作家格非新作《望春风》:像《奥德赛》那样重返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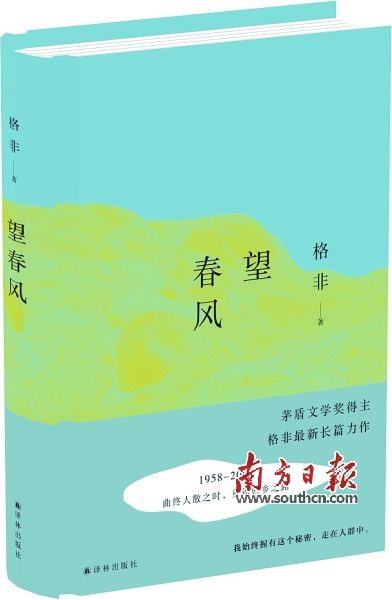

格非在新书发布会上。 王甜 摄
日前,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家格非的最新长篇小说《望春风》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望春风》以中国传统小说和绘画的散点透视手法,对一个村庄的数十个人物群像进行精细刻画,描绘乡土中国的活色生香,展现了乡土文明的人情之美和生存意义。这是格非茅奖获奖作品“江南三部曲”之后的一次全新尝试,也是一次充满艺术冒险的回乡之旅。
“江南三部曲”之后,格非的艺术技巧更臻纯熟,文学和思想视野更加开阔。《望春风》既吸收《金瓶梅》《红楼梦》等明清小说乃至《史记》的复杂技巧,塑造古典诗词与现代汉语交融的语言品质,又展开与荷马、乔伊斯、T·S艾略特、博尔赫斯、福克纳、普鲁斯特、卡夫卡、鲁迅等世界文学大师的对话。作品既探秘过去又预示未来,显示了一个作家民胞物与的使命感,被誉为其30年艺术创作的成熟之作。
近日,南方日报记者独家专访茅奖作家格非。格非说,作为一次艺术尝试,能达到的都达到了,而他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像《奥德赛》那样重返故乡,帮助农村人解释他们的一生,并对乡村的未来寄予希望。
谈作品
重返故乡是诗人的唯一使命
南方日报:《望春风》这部小说创作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写这部反映乡村命运的作品?
格非:现在回想起来,当初之所以决定写这部小说,也许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儿时生活的乡村变成瓦砾之后所受到的震撼。
又过了一些年,我回家探亲时,母亲让我带她去村子里转转。几年不见,乡村变成废墟,草木茂盛,动物出没,枝条上果实累累。我很自然就想起了《诗经》中“黍离”那首诗。想到了鲁迅当年写《故乡》时与故乡告别的心境,也想到了T·S艾略特。那时我才认真决定要写点什么。后来《收获》杂志的李小林老师向我约稿,我就开始了写作。原打算写个七八万字的中篇,但开了头,一种悲悼情绪将我笼罩。写作好像是为了与故乡告别。
南方日报:小说写了儒里赵村的整个群像,我粗略估计刻画了至少50个人,如此大规模的人物刻画是出于什么考虑?
格非:与故乡告别,实际上就是与记忆中的那些人告别,与那些形象、声音、色彩告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我故意要设置这么多的人物,而是人物的形象一个接着一个来到我眼前,让我不忍割舍。所以,在写《望春风》时,我体验到了以前的写作所没有出现过的新情况,就是说,大量的人物来到我跟前,要求在作品中获得一席之地。既然如此,我所要做的,也许就是妥善安置他们,让他们各得其所。
我发现在保存乡村生存记忆方面的作品非常少,我也一直很奇怪,也一直没有下决心写这样的作品。在这部小说里我试图帮助这些人,解释他们自身。我相信他们是很难解释自己的一生的,我觉得有责任帮助他们解释他们失去的时光,这是我的使命。
南方日报:你在上海北京生活那么多年,这些乡村“经验”从何而来?
格非:我以前的作品也常常从故乡取材,但从未想到要认真地或者说正面地描述过它。童年经验是一个人生命中最核心的部分,这对任何作家来说都是如此。这些东西甚至都不能被称作经验,它是流逝岁月中的顽石。时间可以把它打磨得玲珑剔透,它从来不会被真正遗忘。它一直在那儿,是我们所有情感最深邃的内核。
江南对我来说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我恰好生活在江南。我觉得江南也好,江北也好,甚至中原、边疆也好,在写作中并无什么特殊的优势。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值得记述的。但另一方面,一个人的气质和情感方式又不能不受到地域因素的影响。
南方日报:小说的时间跨度长达50年,看似没有直接写历史,却在人物命运的变迁中写出了时代的轨迹,你也像陈忠实、贾平凹那样希望为中国农村立传么?为何在“江南三部曲”之后返回去写乡土?
格非:我渴望重新理解那些平常的人,哪怕看起来是一个“坏人”,也应该尊重,这个是更为重要的。最近我看了意大利物理学家卡洛·罗韦利写的《七堂极简物理课》,书里说时间其实根本不存在,作者认为整个宇宙,村庄会消失,讲得非常残酷。但这就有一个新问题,中国古代的苏东坡、杜甫早就回答了,我在书中也试图回答:活动在这么有限的时间里面,他们抱着怎样的情感,背叛和相爱?这是作家们需要面对和处理的一个“引力场”。
从表面上看,《望春风》确实可以称为一部“乡土小说”,但写一部乡土小说并不是我的初衷,我也无意为中国乡村立传。在我的意念中,《望春风》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小说,或者说是一部重返故乡的小说。记得海德格尔曾说过,重返故乡是诗人的唯一使命(或译“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我相信他是在《奥德赛》的意义上说这句话的。《望春风》的主人公经历了一次重返故乡的历程(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也确实受到《奥德赛》的启发),而我在现实中也经历了一次次重返故乡的旅程。终于有一天,当我发现即便在想象中也没有办法返回故乡时,我才体会到古诗文中所谓“人生如转蓬”这样的伤痛之感。这也许就是我在写完《江南三部曲》之后,再次涉及乡村题材的原因吧。
谈写作
希望与很多前辈作家对话
南方日报:《望春风》在时间线索和人物刻画中采取了古典叙事和绘画的散点透视手法,叙事线索交错穿插,伏笔众多,时隐时显,似乎增加了阅读难度和挑战性,这是受到《金瓶梅》《红楼梦》等明清小说创作手法的影响吗?
格非:明清章回体小说对我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一部作品的写作过程,实际上也是与此前的许多文本展开对话的过程。任何一部作品都与此前的其它作品构成复杂的互文关系。所以我的两个博士生开始帮我打手稿、挑错字,看第四、第五遍时发现里边有很多线索,有的线索埋得比较深一些。这个当然也是《红楼梦》的写法,千里布线,一个线埋在千里之外。
我通过《望春风》和前辈作家对话,当然不只《金瓶梅》或明清小说,还有乔伊斯、艾略特、福克纳、普鲁斯特等非常多的人。有大量小说的技巧可以用进去,可以是司马迁,也可以是《喧哗与骚动》的写法,我可以开一个长长的名单,当然我觉得没必要这么做,因为我对于那些具有很好文学修养的读者怀有牢固的信心。
我确实追求《金瓶梅》式的叙事高度。我在写《望春风》的时候,心里暗暗怀着期望。我希望读者在看第二遍或第三遍的时候,还能读出新东西。不过,在如今这个时代,指望读者将你的作品读上两遍、三遍,显然是过于自恋了。但这个期望本身,因涉及到小说的写作手法,特别是线索和结构,也不能不严肃地加以对待。我以前有的作品有点做作,我希望,当我多少年以后重新看《望春风》的时候,它更自然一些。
在作品中采用什么样的叙事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跟你如何去想象你的读者密不可分。你知道,李商隐和白居易所设想的读者是不一样的,这也导致了他们诗歌语言和形式的不同。我在《望春风》中尽量使用平实的语言,也是希望在阅读上不要人为地设置太大的障碍。但同时,我也会去寻求“知音”读者的认同,甚至与一小部分我称之为“秘密读者”的人展开对话。这样一来,整个作品的手法不得不进行通盘的考虑。
南方日报:你的语言精美、文雅,富有古典气质,诗词古文穿插其间,《望春风》的语言更是简洁凝练,有一股自然的气息。因何而变?
格非:尽管我一直崇拜杜甫,可是直到最近一两年读杜诗,才真正体会到所谓的“沉郁顿挫”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喜欢平实自然的语言,也不排斥精美和典雅。我认为最理想的语言风格是简洁、准确同时有力量。说起来容易,但要真正达到这种境界,需要不懈的努力。你大概知道,杜甫一直到晚年的荆、湘时期,都还在尝试用更新、更有力量的语言写作。
谈思想
文学具有一种超越性的力量
南方日报:小说第一章父亲教导孩子为人处事、察言观色和算命方法的情节,蕴含着一种乡村的哲学观念。“天命靡常”“预卜未来”中的内容,是不是借鉴《红楼梦》中太虚幻境判词的写法?
格非:严格来说,《望春风》中“天命靡常”的“天命”,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天命,并不是一回事。《礼记》中有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样的说法,对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塑造,历来影响很大。《望春风》中的天命,特指预先就被决定的命运,确实带有一点宿命论的色彩。考虑到人物的父亲是一个算命先生,他有这样的观念并不奇怪。事实上,这样一种观念在中国的乡村生活中确实也很普遍。《红楼梦》中的判词,实际上脱胎于《金瓶梅》,从小说的修辞技法来说,是一种“提前叙事”或“预叙”。我在《望春风》中这样设置情节,不光是为了凸显世事无常,同时也要传达父亲在诀别之际对儿子日后命运的担忧,与《红楼梦》并不完全相同。
对于现在的乡村,我认为,原先绵延了几千年的乡村伦理正在衰微。但人们还未充分意识到乡村中代代承袭的是非观、道德伦理观以及人文风俗的重要性。
南方日报:你的小说中常带有诗性气质,对你而言,诗歌和小说是可以在一个文体内互相融合?二者的边界在哪里?
格非:从形式上说,我并不赞同小说的诗歌化,甚至也不赞同小说的散文化。三者各有优长,也有各自的边界。小说要往前发展,应该更多地从小说文体自身去着眼。《春尽江南》中用了一点诗歌,那是因为主人公谭端午恰好是一个诗人。我觉得将沈从文、废名或汪曾祺的小说概括为“诗化小说”或“散文化小说”,是一种偷懒的做法。我并不否认诗歌、散文和小说具有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在我看来,无非是如何共享叙事、抒情和议论。那种认为小说只能叙事,不能涉及抒情和议论的观念,早已被普鲁斯特打破。但你并不能说《追忆似水年华》是诗化小说或散文化小说。如果我们认为在小说中塞进一些蹩脚的诗歌就完成了所谓的“跨文体写作”,显然是可笑的。
南方日报:《望春风》这个书名让我想起陶渊明“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以及“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所蕴含的生机气象。小说有一种回环结构,最后赵伯渝和“婶子”春琴在蛮荒之地上结为夫妻,种地写作,像两个原始人类一样的寓言形式,埋下乡村复活重生的希望,为什么采取这种寓言性结局?
格非:我很喜欢你所说的“原始人类”这个说法。我们在读T·S艾略特《荒原》的时候,往往注意到那被遗弃土地的荒芜,而忽略掉作品真正的主题。在我看来,这一主题恰恰是期望大地复苏。当有人能问卡夫卡,人类还有没有希望时,卡夫卡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当然有希望,只不过这种希望不一定是我们的。同样,鲁迅先生总体上也许是一个悲观的人,但他在寂寞和忧愤之中,也通过《好的故事》暗示了同样的希望。这篇文章多年来一直是我心中的珍爱。我们总是把文学称为一种超越性的力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南方日报记者 陈龙)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推荐阅读
相关新闻
- 评论
- 关注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