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摩崖碑刻的傳世之作"石門十三品":何時再唱石門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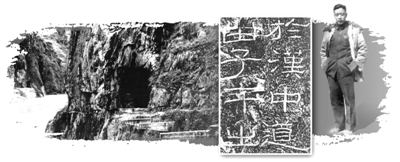 |
|
|
又見“石門十三品”
時隔一年,2015年7月下旬,又一次走進陝西漢中博物館,欣賞摩崖碑刻的傳世之作“石門十三品”。
關於“石門十三品”的介紹如下:
“石門十三品”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褒斜道石門及其摩崖石刻”的重要組成部分。褒斜道是我國古代最早的棧道,因褒斜二谷而得名,全長四百七十華裡。褒斜道南出褒谷穿越七盤山有一段隧道,史稱石門。其開鑿年代距今已有一千九百余年。古時行經棧道的車輛都曾經過石門。古人目睹棧道和石門之偉跡,常感發於懷﹔或為文題記,或題詩留名,相繼鐫於石門內外的崖壁間,遂形成了浩瀚的石門石刻。據一九六○普查中統計,共有摩崖石刻百余方。就中以漢魏刻石為主體的十三種摩崖石刻,最受推崇,世稱“石門十三品”。
按照時代順序,“石門十三品”名錄如下:
漢《鄐君開通褒斜道摩崖》﹔漢《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又以《石門頌》而著稱)﹔漢《右扶丞李君表記》﹔漢《楊淮·楊弼表記》﹔漢隸大字“石虎”摩崖﹔漢隸大字“石門”摩崖﹔漢隸大字“玉盆”摩崖﹔漢隸大字“袞雪”摩崖(為曹操所書)﹔曹魏《李苞通閣道題名》﹔北魏《石門銘》﹔南宋晏袤《鄐君開通褒斜道摩崖釋文》﹔南宋《潘宗伯韓仲元李孝章碑字及晏袤釋文》﹔南宋《山河堰落成記》。
“文革”期間,因修建石門水庫,石門一帶的碑刻挑選出“十三品”將之切割下來,移至漢中博物館的“石門十三品陳列館”集中展出。石門裡其它百塊歷代碑刻,從此淹沒水底,無人再識真面目。
與去年7月的初次見面相比,與“石門十三品”重逢,心裡多了感慨。因為,一天之前,參觀石門棧道風景區,聽人談到一個人與保護石門摩崖石刻的故事。故事一旦聽過,我再也無法忘記他的名字——張佐周,1934年,負責主持修建西(安)漢(中)公路的年輕工程師。
因為張佐周,兩千年前的石門,與今天的我們頓時有了一種直接關聯。此時,站在“石門十三品”前,久久不想離去,多少歷史感嘆,伴隨張佐周的故事一起走來。
臨危受命進秦嶺
決定1934年修建西漢公路,與抗日戰爭有關。
據漢中市檔案館所寫《西漢公路修建始末》一文介紹,1932年淞滬抗戰爆發后,著名軍事家蔣百裡提出建議:中日必有一戰。要警覺日寇模仿八百年前蒙古鐵騎滅南宋的路線,由山西打過潼關,翻越秦嶺,佔領漢中再攻四川與湖北,彼計若成,亡國無疑。必須採取抗戰軍力“深藏腹地”,建立以陝西、四川、貴州三省為核心﹔以甘肅、雲南、新疆為根據地﹔拖住日寇,打持久戰,等候英、美參戰,共同對敵,方能最后勝利。
蔣百裡的這一建議,很快得到採納。於是,雲南修建滇緬路,陝西修建西漢路,全面抗戰爆發之前的公路布局,緊鑼密鼓地在西部地區進行。
西漢公路於1934年開始勘探、修建。西安至寶雞原有可行馬車的大車道可資利用,實際修筑的主要為寶雞到漢中道路,全程二百五十四公裡,除寶雞至益門鎮五公裡與褒谷口至漢中十五公裡為平路外,其余二百三十四公裡均在秦嶺的崇山峻嶺之中,工程之艱巨可以想見。於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撥款修建,這在全國尚屬首次。工程人員由中央經委會公路處處長趙祖康親自挂帥,他從全國數省工程局調集在公路界嶄露頭角、已有名聲的一批人員:吳必治、孫發端、張昌華、張佐周、張鴻逵、鮑必昕、李樹陽、李善梁、劉承先、劉樹升等。
這一年,張佐周剛剛二十四歲,兩年前畢業於天津北洋大學。年輕的張佐周,臨危受命,走進秦嶺,參與勘探、設計、修建這條難度極大的公路。
《西漢公路修建始末》這樣介紹走進秦嶺之前的張佐周:
張佐周出生在河北保定一個書香世家。從小受私塾教育,使張佐周打下古文基礎,引起對古代歷史文化的興趣,使他終身受益匪淺。“五四”運動中,父親受“科技救國,實業救國”的感召,去天津開辦了一個實驗農場,自任場長,並在張佐周十一歲時,把全家由保定接往天津定居。
張佐周從小用功且好勝心強,但凡考試,必為人先。連跳幾級,爭取了時間,年僅十六歲就全部讀完中學課程。並考取北洋大學生,就學土木工程。一九三二年,二十二歲的張佐周從北洋大學畢業,經過考試進入全國經委會公路處。其時,中國公路交通剛剛起步,經委會出台的第一個方案是興辦江蘇、浙江、安徽三省連接的交通干線。
踏出校門的張佐周立即有了用武之地,直接被派往施工第一線,從測量、設計到施工,全方位地接觸實際。從頭至尾參加了從上海至杭州的滬杭公路,從杭州到徽州的杭徽公路的興筑。在此期間,張佐周還作為工程技術人員代表跟著趙祖康去武漢參加了蘇、浙、皖、鄂、贛、豫七省公路會議。
(《西漢公路修建始末》)
走進秦嶺的張佐周,屬於第三測設隊。在第三測設隊負責人張昌華離去之后,留壩至漢中的測量、設計、施工的重任,趙祖康毫不猶豫地交給張佐周。
張佐周臨危受命,挺身而出。
秦嶺的崇山峻嶺,將見証一個年輕人與歷史的銜接。
石門碑刻有幸,將遇到一位喜歡傳統文化、青睞它們的工程師!
保護石門,改道架橋
走進秦嶺,一路勘探,走至臨近漢中盆地的褒水峽谷,千年聞名的石門,出現在張佐周眼前。
張佐周熱愛傳統文化,喜歡古代碑刻。后來他說,石門內外,他看到古代文字石刻多達一百零四塊。宋、明以下者尚且不論,漢魏珍品為我國最集中的石刻寶庫。如《石門頌》刻於東漢建和二年(公元148年),距今一千九百余年。《石門銘》刻於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距今也有一千五百年。二者均為千年珍品。有幸走進石門,目睹千年碑刻,張佐周欣喜若狂,興奮不已。可是,如何保護石門碑刻,這個極為棘手而嚴峻的難題,也擺在他的面前。
《西漢公路修建始末》寫到,寶雞到漢中的這段公路,從留壩施測一直沿著褒水西岸,而石門就在西岸:
石門是漢代開鑿,那時的古道多臨河在山崖鑿孔,下用立柱支撐,再鋪架木板為道。誠如諸葛亮所說:“其梁閣一頭入山腹,一頭立柱於水中。”這種空中閣道,即屢見於史的棧道。由於立於水中的立柱不可能太長,所以棧道距水面常在五至七米之間,石門正在這一高度,而目下興筑的寶漢公路恰與秦漢時期的棧道處於同一水平線。若開山辟路,石門古跡注定被破壞殆盡,蕩然無存。而且,還無法回避,首先不可能讓公路低於石門,那樣易被洪水沖毀﹔也不可能高於石門,此處全為筆立的懸崖,且不說無法使路面驟然升高,即便升高,開山炸石也必然危及石門!
這當然是張佐周絕對不希望出現的事情。他產生的第一個念頭就是:石門絕不能去碰!
那些天,年輕的工程師心裡像墜了塊石頭,煩躁沉悶,坐立不安,他反復查看谷口地形,一個大膽的念頭突然閃過:要保護石門古跡,隻有在上游改道,把公路由河西移至河東。他立即向總工程師孫發端與主持興筑寶漢公路的趙祖康匯報,引起兩人高度重視,同時來到現場考查,使張佐周提出的方案得到許多完善和補充,最后一致同意架橋改線,保護石門。經過雞頭關下“石門”峽谷而達漢中。
於是,公路測設由河西移至河東,完全避開了石門古跡。而且,趙祖康、孫發端也完全採納了張佐周的建議,在石虎、翠雲屏等石峰開鑿通車連環三洞,總長度六十六米,約四倍於古石門。
(《西漢公路修建始末》)
1988年,時隔半個多世紀重返漢中的張佐周,在第三屆褒斜石門研討會上,這樣回憶當年親歷保護石門的往事:
回憶當年受趙老(趙祖康,當時任全國經濟委員會公路處處長)和吳老(吳必治,任西漢公路總工程師)的委命,我代理留漢段測量隊長。當施測到雞頭關下,為了避免破壞古“石門”古跡,在褒姒鋪以下附近建橋(即雞頭關大橋)過褒河,走“石門”對岩“石虎”腳下。又恐有損“石虎”虎形,特在下部開鑿連環三洞,稱為“新石門”。沿河岩石堅硬,山勢險峻,是西漢公路最艱巨的一段,也是最有歷史、文化意義的一段。
在褒城施工時,經常去“石門”。當時從褒城去石門無路可通,沿褒河石壁上開鑿的小槽,上下兩排,上層手攀,下層腳踩,按一定的程度面壁前進到達石門南口。洞長約十五米,寬約四米,高在三點五米左右,可以通過汽車。洞內岩石成橫向片狀,凹凸不平,尺寸也不一律,壁上刻有“石門頌”、“石門銘”珍品。南口石壁上有“山河堰”石刻。在洞口兩端附近有四十厘米見方、深約七十—八十厘米的石孔,孔內表面平整,堪稱巧奪天工,下面岩盤上留有圓形石孔。前者是插入懸臂大梁之處,稱為壁孔。后者是圓木支柱之處,姑稱柱孔。如諸葛亮《與兄謹言趙雲燒赤壁棧道書》所雲:“緣谷百余裡,其閣梁一頭入山腹,一頭立於水中。”當是古棧道的遺跡。
(《三十年代耳聞目睹的石門狀況及其軼事》)
談及這件堪可流傳千古的驚人之舉,張佐周的口氣頗為平淡,但仍可讓人感受到他胸間的歷史豪氣。一位二十四歲的年輕工程師,竟有如此寬闊的歷史眼光,有如此深厚的文化情懷,難道不可以視為英雄?不可以視為保護歷史文化的功臣?在我看來,張佐周保護石門碑刻的舉動,堪可與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抗戰之際的文物勘察與保護之舉相媲美。
1936年5月1日,新石門隧道鑿通,西漢公路由此全線開通。竣工之際,趙祖康專門請當時公路界資深元老葉恭綽,題寫“新石門”鏤刻摩崖之上,隔褒水與對岸石門遙相呼應。
石門碑刻無恙,新石門道路暢通,還有什麼能比這一點更讓張佐周為之欣慰?
一年之后,全面抗戰爆發。戰前的公路戰略布局,開始發揮作用。
遺憾可彌補,石門再觸摸
張佐周是位有心人,在勘探和修建西漢公路之際,他拍攝諸多照片,為我們留下當年的石門景象。張佐周的兒子張熹回憶說:2004年,父親病重期間,我把他拍攝的關於西漢公路和石門的老照片放大后,請他回憶和辨認。他清楚地一一說出地點和場景,我趕緊記錄下來。后來,我們把這些珍貴的照片贈送給漢中博物館。
消失了的景象,因為張佐周而留下陳跡殘影。
在漢中博物館,買到一套《張佐周與漢寶公路》明信片。峭壁上的“石虎”石刻﹔石門隧道北口遺址﹔拓印匠人張老漢拓印《山河堰落成記》現場﹔褒水東岸新石門的連環三洞施工場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褒城縣城牆與城樓……
張佐周真可謂一位充滿浪漫情懷之人。在東岸公路修建之際,他在西岸石門北口棧道遺址上,恢復一段棧道。他回憶說:“我為了恢復一段古棧道的面目,曾在石門北口外依原留孔洞用木材修復了仿古棧道,並在終端一塊峭壁的頂部修筑一亭,毅然臨於褒河溪流之上,面對石虎及公路,景色既秀麗而又奇偉,誠一游覽,憑吊勝地。我當時年輕氣盛,指點河山,俯仰今古,睹‘袞雪’、‘玉盆’遺石,領略大自然之美景,至今思之猶歷歷在目。”他先后拍攝棧道遺址與恢復后的棧道,兩張照片放在一起,恰如張佐周在與悠悠歷史對話,余音裊裊,回蕩於山谷之間……
石門得以保存,實為幸事。1960年,全國進行文物普查,核實石門摩崖石刻有百余方之多,“石門十三品”最受推崇,故將之命名為“褒斜道石門及其摩崖石刻”,成為第一批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69年,距張佐周保護石門改道修橋,正好三十五年。此時,因在褒水山谷修建石門水庫,千年石門從此沉入八十米深的水底。正值“文革”期間,傳統文化早被貶斥和破壞,石門焉能躲過一劫?
自1937年離開石門后,張佐周一直等待了五十一年才重返石門。站在山谷之間的水庫大壩上,滿眼望去,一切,不再是從前。
距大壩百米開外的石門已無蹤影,石門隧道之上的山頂,隻在水面上露出兩塊不大不小的巨石,他所恢復的石門北口的棧道和涼亭,當然也隨石門一起沒入水中。因水位提高,新的西漢公路提高路基重新修建。站在大壩上,俯瞰下方,可以看到東岸廢棄的西漢公路,三個串連的新石門,依稀可見。睹物懷舊,張佐周感慨萬千。他在石門研討會上,傾訴故地重游的情懷:
我在褒城施工歷經三個春秋,自從1937年離開后距今已經五十有一載。久想舊地重游。此次重來漢中,一是應會議之邀,二來也了卻平生之願。所以乘火車一到陝境,頻頻借窗眺望,夜色中僅燈火點點而已。一俟天色初露曙光,見漢江兩岸山山水水依然,遍野花黃柳綠,高樓大廈拔地而起,真是一片春光,一片繁榮景象。換了人間,感慨萬分。下午迫不及待去褒河大壩,隻見高壩背后煙水茫茫,石門已沉淪於水中。昔日之奇偉風光,褒河的激流湍急已成為過去。深感興修水利是件好事,但美中不足將石門淹沒,未免遺憾千古。如果大壩向上游移若干距離,則既興修了水利,又保護了寶貴的文物,豈不兩全其美。雖然耗費較多也是值得的。幸有省、地領導部門關注及有識之士奮不顧身,搶救出來以十三品為主體的部分石刻保存於漢中市博物館中,是不幸中之大幸。
(《三十年代耳聞目睹的石門狀況及其軼事》)
歷史感慨,不需太多表達,一切盡在不言中。他說得不錯,大壩距石門不到百米,當年如有清醒的有識之士,能如張佐周一樣挺身而出,建議把壩址往上方略為挪動,興修水利與文物保護,如同當年修建公路一樣,仍然可以做到兩全其美。
可惜,遺憾已成永遠。
那天,在石門水庫坐上游艇,我們暢游於碧波蕩漾之間。路過西岸,但見水面上露出兩個不大不小的岩石。陪同友人說,這是山頂,水中淹沒部分是山體,兩千年前的石門,就在下面。
凝望石門山頂,我忽發奇想。如今,水下考古已經成熟。石門水庫水深不過八十米,風平浪靜,碧水清澈,顯然非常適合水下考古。石門的岩石堅硬,淹沒水中的近百塊歷代碑刻,想必安然無恙。即便石門裡面有淤泥,以目前的技術將之清淤並非難事。如果先行派潛水員實地考察,做出考古可行性研究。如果難度不大,以電視直播石門碑刻現場考古,一定很有意義。進而,按照修建海洋公園的方法,修建一座水下石門博物館,供人參觀,這並非沒有可能。
遺憾已成永遠,今天的人們卻可以彌補遺憾。用新的方式,讓淹沒已久的千年碑刻,重現在我們面前。希望這一天,不太遙遠。
何時再唱石門頌?
悠悠歷史,可以再銜接,再觸摸……
制圖:張芳曼
《 人民日報 》( 2015年08月21日 24 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推薦閱讀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