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屆香港書展 金庸再次成為話題焦點

7月22日 ●講座嘉賓:內地金庸小說研究評論家陳墨,香港影評人、作家鄭政恆 ●講座題目:金庸的武俠世界 ●推薦書目:香港三聯版《陳墨評說金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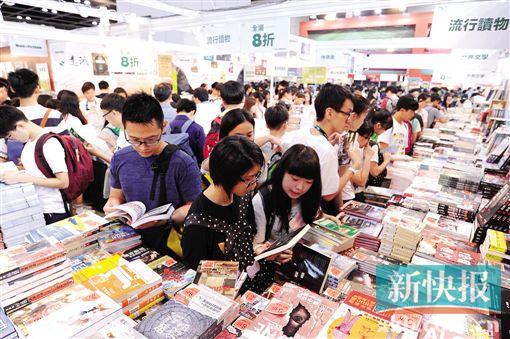
■書展現場書多人多。

■左起楊健思、沈西城、楊興安。 7月23日 ●講座嘉賓:梁羽生關門弟子楊健思、金庸秘書楊興安、《武俠》雜志社長沈西城 ●講座題目:一代風氣開金梁——清談武俠巨人梁羽生、金庸

■金庸與梁羽生。
■新快報記者 王春燕
7月20日-7月26日,由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主辦的第27屆香港書展又如期而至。今屆香港書展吸引了35個國家及地區共640家參展商參展,打破了歷屆紀錄。而來自各地的愛書人,也如這幾日當地的天氣一樣“狂熱”。
今屆書展以“武俠文學”為“年度主題”,為此安排的講座多達十幾場。香港貿發局總裁方舜文在開幕式表示:“今屆香港書展以‘從香港閱讀世界,閱讀江湖·亦狂亦俠亦溫文’點題,一方面配合年度主題,同時亦寄望讀者透過書展培養對閱讀的‘狂’熱,從而成為外在‘溫文’,內在”俠‘義的人生主角,並擁有更精彩的人生,創造更美好的世界。”
金庸,再次成為本次書展中被反復提及的人物。
“他用不同的女朋友配不同的男先生”
陳墨從武功、人物刻畫等方面,講述了自己眼中金庸小說的獨特之處。他認為,首先,金庸把武功文學化,把武功詩化了。“他把中國古典詩詞、典故都化到自己寫的武功中去,比如‘玉女心經’當中有很多中國古代美人畫中畫的名稱,像‘西子捧心’。這跟過去武俠小說和其他武俠小說寫八卦蓮花掌、太極拳等真實的武功名稱不同。在他小說武功的描寫中,中國文化的詩性更強,讀起來味道更濃。”陳墨說。
其次,金庸把武功“個性化”了,他筆下的人物每個人都有一門獨門武功,這差不多也是這個人個性描寫的一部分,像“降龍十八掌”屬於郭靖,韋小寶在《鹿鼎記》中的拿手絕技叫“神形百變”,他改成“神形百逃”,腳底抹油的功夫,打不贏就趕緊逃命去。這是韋小寶市井生活的一種經驗,也是他性格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陳墨還講到了金庸小說裡的教育學,他以《射雕英雄傳》中郭靖學武的過程為例:郭靖的小學老師是“江南七怪”,方法就是滿堂灌,把郭靖折騰得半死,但長進很少;中學老師叫馬鈺,是個代課老師,他偷偷地跑到蒙古去,教郭靖打坐、呼吸、練功,就是把娛樂消閑和教學結合在一起,一邊打坐一邊吃飯,在生活中都在練功。這個“上課”時間很短,但郭靖的長進很巨大。郭靖的大學老師是洪七公,他的教育方法概括起來就是因材施教。除此之外,郭靖的成長道路上還有一個老師,就是黃蓉,她是文化課老師。
所以《射雕英雄傳》這部書寫的是人的一個成長過程,整個教育過程,金庸寫得非常完整。我們在別的武俠小說當中看不到這個。別的武俠小說一般隻有兩招尋常招數,一招就是他的師傅是天下第一高手,所以教出來的徒弟必然都是高手。其實這個是違背教育和成長的真實規律的。天下第一高手,教出來的不見得是天下第一高手。另一招就寫吃藥——遇到一個仙果吃下去,內力大增。金庸也讓郭靖吃藥喝蛇血,但這個對他來說其實完全不是重要的。這是金庸跟那些武俠小說作家的差別,非常之巨大。
金庸更大的貢獻是對人物的理解,他在不斷地尋求變化。“我發現金庸小說有一個規律,后一部小說的主角跟前一部小說的主角(在性格上)基本上是相反的:《書劍恩仇錄》的陳家洛是白面書生,《碧血劍》的主角就黑不溜秋。陳家洛學歷很高,內心優柔寡斷,袁承志學歷相對較低,但內心要堅強得多,非常堅忍和有主見。在《飛狐外傳》中,胡斐就變得非常詼諧開朗,跟袁承志又不太一樣。”
接下來,他就寫了一個郭靖,郭靖就真的很木訥。郭靖寫完了,下一個就是楊過。楊過跟郭靖幾乎各方面都是不一樣的。他聰明、自我、自以為是,缺點和優點跟郭靖相反。然后下一個就是張無忌,張無忌跟楊過又是反的。楊過是處處聰明,而且顯出來聰明,但張無忌這個人內秀,內有靈性,英華內斂,但從來不顯露。楊過是至情至性,實現自我,以自我為中心的發展路線,而張無忌從小學醫,醫者仁心——我不知道他的醫術到底怎樣,但至少他學到了醫生的仁愛慈悲,這是張無忌的一個最突出的性格特點,是他人格的基礎。這跟楊過不一樣。最后寫到韋小寶這麼一個非常好玩的主人公。
金庸是調動一切的藝術手段來描寫他的主要人物,創造個性,有的是用武功,有的是用主角的女朋友——不同的女朋友配不同的男先生,包括黃蓉和郭靖這樣反差極大的性格,那是人間絕配。
“武俠會變成第二種形式,不需要一模一樣”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梁羽生與金庸在《新晚報》創作武俠小說,共同開創了新派武俠小說的先河。梁羽生摒棄了舊派武俠小說一味復仇與打打殺殺的傾向,提出武俠“寧可無武,不可無俠”的理念。金庸則通過武俠小說寫人性,題材多樣,內容深刻,將武俠帶入了文學的殿堂。
但關於兩人之間誰更勝一籌的爭論從未休止過,其中一個說法是“梁羽生的國學功底比金庸好”。對此沈西城說,金庸國學並非不好,“他只是詩詞不精”,但對寫武俠小說來說,詩詞與小說故事關系不大,因為讀小說讀的是故事,是人物性格,以及對江湖社會的描寫是否與現代社會契合。“這幾點,查先生都有做到”,相對而言,梁先生確實詩詞很好,但作為小說,這個是不夠的。
楊興安說,《七劍下天山》開了新派武俠小說的風氣。“梁羽生的寫法是接近文藝小說的,在武俠小說裡加入人情世故和愛情故事,我少年時看是當成愛情小說看的”,而金庸的小說,“若抹去愛情線也是不好看的”。
楊興安認為,兩人的共同點之外,金庸的小說是變化萬千的,他的小說只是披了武俠的外衣。比如,《書劍恩仇錄》、《射雕英雄傳》是歷史小說,《神雕俠侶》是愛情小說,《倚天屠龍記》是偵探小說,《天龍八部》是人性小說,《笑傲江湖》是政治小說。《鹿鼎記》在金庸小說中是娛樂性最強的,但文學性就未必有其他作品好。
楊健思認為,金庸的小說是寫人的,特別是對人性的刻畫非常深刻,也很尖銳。梁羽生也寫人,但他的人物就比較平鋪直敘,比較簡單。為什麼呢?“因為這是他本人的投射,他就像個孩子,很淡泊,很天真,比較老實”。
沈西城也認同楊健思的這個說法,“梁先生是一個老實人,查先生是一個狡猾的人”。“你看韋小寶,這些對白這麼詭譎,如果作家是一個老實木訥的人,如何寫得出呢?楊過、黃蓉都很反叛,令狐沖很有性格,又喜歡個魔女,所以說金庸的作品充滿反叛精神。我們年輕時,就很迷戀這一點,一定有反叛精神才能創新,才能對抗潮流,一板一眼的話,就死定了”。
實際上,梁羽生也對金庸小說裡的人物復雜的個性有過論述。楊興安說,梁羽生之前曾寫文章指出,“金庸有一項特別之處,就是寫壞人寫得好過寫好人,金庸可以鑽入壞人的內心世界,有時你讀來都會同情這個壞人”。
講座最后說到武俠小說的式微,楊健思說,其實金梁兩位先生對於“后繼無人”這件事也是有保留的,“他們覺得這是會變的,會變成第二種東西出來,不需要在他們那種模式下一模一樣寫出來”,他還透露梁羽生將哈利·波特都讀完了,“他覺得可以有另一種突破,轉成第二種形式,但仍然以小說的面貌出現”,至於名稱是武俠小說還是其他,可能這並不重要。
●香港武俠文學代表人物
香港武俠文學始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報章武俠小說連載,因廣受歡迎而獲出版成書,進而擴展至漫畫、電視、網上游戲等領域,影響力遍及整個華人社會,及至海外。其中八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包括: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梁羽生、金庸、古龍、倪匡;1980年代的溫瑞安、黃易;1990年代至2000年代的代表是喬靖夫和鄭豐。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推薦閱讀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