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書記錄26個故事 女作家如何“訪問童年”
中新網客戶端北京1月12日電(記者 上官雲)長大成人后,“童年”似乎是人們願意回憶的。隔著歲月的濾鏡,會覺得有那麼多小小的美好。可前不久,一位作家用一本書和大量的採訪告訴讀者,有些人的童年生活並不快樂。這本書就是殷健靈的《訪問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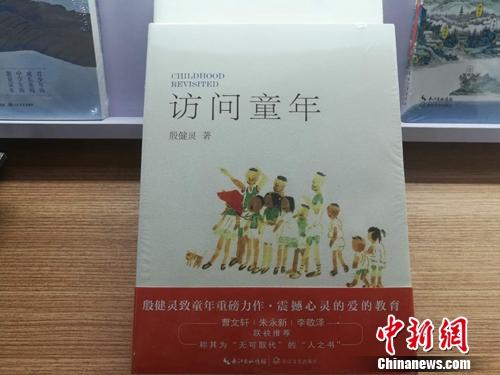
《訪問童年》。上官雲 攝
她告訴記者,請受訪者回望童年,是想用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告訴讀者,太多人需要在童年面對各種痛苦,乃至生離死別,“完滿”並不是童年的常態。但全書基調並不灰暗,在每個人的故事中,又總能找到向上的積極力量。
一個曾無法逃脫自卑的優等生
李妙玉是一位公務員,很小的時候親生母親因病過世了。她和奶奶住在鄉下,總要經受著別人獵奇和憐憫的目光,“這個小孩好可憐哦,沒有媽媽的”。
所以,后來她和繼母初時的相處很愉快,因為意味著有了完整的家。繼母給她帶來漂亮的蝴蝶結,為她梳頭發,跟她和姐姐聊天,家裡總是聽見姐妹倆的笑聲飄來飄去。
可好景不長。由於繼母還有兩個兒子,家裡屬於工薪階層,負擔四個孩子的花費十分吃力。繼母的態度就慢慢變了。
是怎樣陌生起來的呢?有一次早晨,李妙玉沒吃飽,想去廚房再乘一碗飯。繼母斜睨了她一眼,用一種很陌生的口氣說:“你人小,要吃兩碗。哥哥個子那麼高,也吃兩碗。”
她的目光和繼母的眼神輕輕碰了一下,隻覺著繼母的目光冷冷的,和外面的天氣一樣冷。
仿佛從那時開始,她和姐姐連吃飯也要多多留意,燒了排骨,便猶豫著能不能吃第二塊﹔繼母開始數落姐妹倆,也會和父親冷戰。她們越來越害怕和繼母獨處,悶頭吃晚飯、洗好碗,馬上回房間看書。
她不敢反抗繼母,也不敢把委屈告訴父親——因為害怕他們離婚,害怕自己再變成旁人眼中“不同”的那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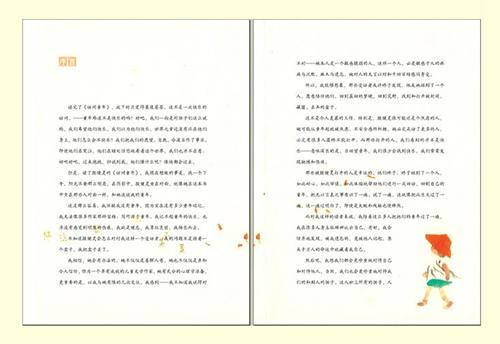
《訪問童年》內頁。長江文藝出版社供圖
盡管她是優等生,但一度逃脫不了自卑。由於一直被繼母取笑“身長腿短,大腿粗,個子矮”,她在打壓中建立著對自己的認知,“我想,我永遠都不可能獲得像別人那樣的自信了”。
遇到那麼多事,仍然相信善良
如果說李妙玉的童年還有一絲溫情的話,沈金珍的童年就似乎灌滿了悲傷。她出生於上世紀50年代,曾是某公司的一名財務。
她的父親是建筑公司的水泥匠,繼母不識字,也沒有工作,但為人很好。父親幾十塊錢的工資難以養活一家八口人,沈金珍從小就學會幫家裡做事,比如出去跟別人借錢。
家裡經濟狀況很糟糕,平時吃的是醬油和鹽拌的籼米飯,冬天棉襖破了,棉花露出來,就用繩子扎緊,這樣可以暖和一些。
常言說,父母在,就有家。但她13歲時,父親患胃癌去世了。不過半年的時間,母親也去世了。同一個殯儀館裡,兄妹們先后參加了父母親的葬禮。
成為孤兒后,沈金珍帶著妹妹們生活。她也只是個孩子,但要去給別人做保姆,尋求一切可以賺錢的機會:納鞋底、翻棉襖……她不覺得苦,也堅決不肯把妹妹送人。
很多年以后,她在接受殷健靈採訪時說起童年這一切,忍不住哭了,“我很平常,也經常受人欺負。碰到那麼多事,但我很堅強,從來沒有絕望過,我還始終堅信一點,良心好,善良,一定有回報”。
“不完滿”童年裡的溫情色彩
上面這樣的童年故事,殷健靈在書裡一共寫了26個。裡面的受訪者有著不同身份,年齡最大的已年近百歲,最小的還在讀小學。經歷中有絕望、孤獨、反抗、倔強……它讓更多人明白,不是每個人的童年都無憂無慮,也不是每個人的童年都過得平靜安詳。
比如,有的受訪者視力有些問題,看不太清楚東西,童年有著不那麼愉快的成長經歷,一度封閉、自卑﹔后來得到老師和同學的幫助,才慢慢建立了自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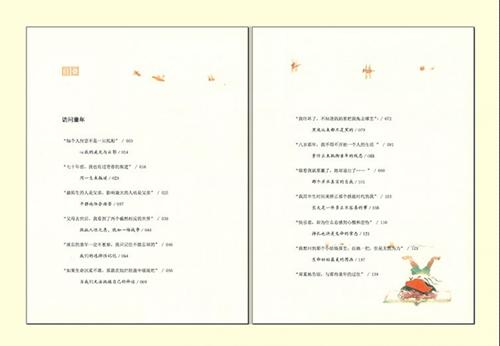
《訪問童年》目錄。長江文藝出版社供圖
在這些故事裡,依然有著溫情的色彩。
一名叫“白茉莉”的教師,小時候被寄放在爺爺奶奶家。雖然從小沒有足夠的父愛母愛,家裡條件比較拮據,但白茉莉的童年依然是彩色的。這種滿滿的幸福感來自於共同生活的老人和叔叔,他們給了白茉莉無盡的關愛。
爺爺喜歡聽書,晚上睡覺前,他會給白茉莉講《西游記》裡的故事﹔奶奶善良能干,十分疼愛她,總是夸她懂事。叔叔給她買了字典,鼓勵她好好讀書……
可能正是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贊揚和關愛,回憶起自己的童年,雖然條件艱苦,但涌上白茉莉心頭的卻是綿延無盡的詩意和爛漫。
她說:“我后來想,一個人的成長是否美好,在於你怎麼看待它”“愛是成長中得到的贊揚,那是最大的動力,激勵我去努力,去追求更好的生活”。
童年更需審慎對待與呵護
曾有人說,殷健靈這本《訪問童年》似乎更多展示了生活中“不那麼完美”的童年,讀起來不夠溫馨、溫暖。
但殷健靈說,她想讓大家知道,童年不僅純真無瑕、混沌無知,童年同樣敏感脆弱、復雜多變、危機四伏。童年獨立生長,可終究敵不過時代洪流、社會文化、家庭環境的裹挾和影響。

殷健靈。長江文藝出版社供圖
倘若人生猶如危崖上的一棵樹,童年便是根,在夾縫中求生存,靠著露水陽光以及自身的力量長成枝繁葉茂。所以,更需要審慎對待與呵護。
“心理學家告訴我們,任何成年后無法解決的困惑和障礙,都可以在童年期找到成因和答案。只是,當我們明白和了解這一切,童年已經無法回返,更難以修正。”殷健靈說。
所以,對孩子而言,從書裡的故事讀到自己,能更珍重地對待自己和對待他人﹔對成人而言,得以“重訪童年”,在記憶、修復和創造中與自己、與生活和解。
德國作家黑塞說過,每個人的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人人都在奔向自己的目的地,試圖躍出深淵。我們可以彼此理解,然而能解讀自己的人隻有自己。
殷健靈說,願把《訪問童年》獻給每一個曾經的孩子以及正在成長著的孩子,“我們將從別人的故事裡讀到自己,那裡有人生的源頭,那裡也有重新出發的路標”。(完)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推薦閱讀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