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副刊丨讀《揚子江文萃》
我曾多次聽說江蘇泰州“揚子江文萃”公眾號很火爆,每天收到全國各地像雪花一樣飛來的稿子達一千余件,而每天實際用稿隻有一篇,可謂是:千裡挑一,披沙揀金。有人感嘆,在“揚子江文萃”上發稿真難啊。該公眾號聚集的粉絲達十萬人之多,這些“鐵杆粉絲”每天早晨七點像迎接日出一樣,早早地就打開各自的手機,等著新稿的推出。而每當一篇稿件推出后,在揚子江文萃評論群中讀者寫的評論近千條。如果一個作者在“文萃”上一“炮”打響,便被網友紛紛傳誦,立馬走紅,成為雖未曾謀面卻人人想見的“名人”。更讓人贊嘆的是,那麼多的稿子,隻有“揚子江文萃”掌門人翟明一人審讀,而且每稿必看,這是一個多麼巨大的工作量啊!他選稿時,重點看稿件能否“打動人心”。
翟明何許人也?他是《泰州晚報》原總編輯。在報社工作期間,翟總親自主編“坡子街”副刊,堅持“老百姓寫,寫老百姓,老百姓看”的編輯方針,僅用三年時間就使“坡子街”成為一個獨領晚報風騷、飛入尋常百姓家的品牌。從報社退休后,在揚子江藥業公司的大力支持下,他辦起了“揚子江文萃”公眾號,僅一年多時間,就讓這個新媒介文學平台成為泰州乃至全國的一道獨特的新大眾文學景觀,還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揚子江文萃2024》(三卷本)。與此同時,在網絡平台上出現了多家專為“揚子江文萃”開辦的評論、綜述、交流的平台,如南京的陳捷勇先生開辦的“揚子江文萃評論”公眾號,每天對文萃作品推發后的上千條評論整理成一篇“綜述”文章,包括“首席評論、優秀評論、金句摘登”,為“揚子江文萃”推波助瀾,珠聯璧合,相得益彰,一時氣象萬千,好評如潮。人們不禁要問:“揚子江文萃”是怎樣一步一步地活起來、動起來、紅起來、火起來的?
今年4月中旬,我應邀赴泰州參加了揚子江文萃文友見面會,聽到了生活大地上春草生長的聲音,親眼目睹了“揚子江文萃”這一文學新媒介、新平台因為直面生活、直通一線、直擊心靈而蓬勃發展的壯麗景象,它全面體現了人民性、時代性的新審美特征,使創作、傳播、欣賞、評價各環節的參與者都能各擅勝場、各美其美,開啟了全新的大眾文學的模式,充分激發了新大眾文藝發展的創造活力。其成功的奧秘或許就在於:
──來自於文萃公眾號的精准定位。“揚子江文萃”公眾號堅持“非虛構、接地氣、抒真情”,在“為何寫、為誰寫、寫什麼、如何寫”上精准定位,以文傳薪,以人為本,匠心獨運,啟智潤心,抱朴含真,引人入勝。就像當年艾思奇先生倡導“大眾哲學”一樣,翟明正用心用情用力地推動“大眾文學”。正如艾思奇先生以最通俗的筆法,日常談話的體裁融化專門的理論,使大眾的讀者不必費很大氣力就能夠接受哲學那樣,翟明先生認為我們的文學也可以大眾化,思考在全媒體時代如何寫好生活的故事,必須將筆觸伸向民間,把目光聚焦大眾,做新大眾文藝的創造者,動員更多的人“我手寫我心”,用大眾喜聞樂見的語言,深入淺出地講好新時代故事,“我”及身邊人現實生活與奮斗的故事,為新大眾文藝如何扎根現實、反映大眾生活樹立了典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短短一年時間,“揚子江文萃”的文章,以及所匯集的三本皇皇巨著,在文友之間不脛而走,競相傳誦,一時傳為文壇佳話。
──來自於品牌傳播的全攻略。翟明先生建立了“寫—讀—評—談”一體化的作品創作與傳播矩陣,推動作者、評論者、讀者實現良性互動,靈犀相通,把成千上萬個“粉絲”召集於同一個“屋檐”下,包括今年先后召開的專家座談會和“文萃”作者線下見面會,大家對文本進行深入細致的分享、對話與交流,見仁見智,相互啟發。著名作家王慧騏一起有力助陣,慧騏老師近年出版了《青色馬文存》(三卷本)、《江南素描》、《安靜做最慢的事就好》等散文隨筆集,為揚子江文萃作者通過寫作向大眾傳遞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精神力量提供了優秀的范本。翟總不愧為宣傳策劃與傳播的高手,他善於培育文化品牌,發揮文化的品牌效應,堅持網刊的特色發展,建構作者、評論者與讀者之間理性、健康的對話關系,使揚子江文萃從線上到線下、從天邊到身邊,愈益變得可愛、可親、可敬。功夫不負有心人,如今揚子江文萃擁有了像王慧騏、徐循華、劉茁鬆、趙光琦、張淑霞、林蕾、王軍樂、常玫瑰和被譽為“女版趙樹理”的王玉蘭等一大批優秀作者群,以及葉櫓、王干、周旭、王正宇、周法鳴、王永峰、陳捷勇等一大批實力評論者隊伍,越來越多的新秀也如雨后春筍般茁壯成長。
──來自於適應大眾心理的新期待。翟明先生奉行“大眾書寫、大眾閱讀、大眾評論、大眾分享”的辦刊理念,“揚子江文萃”公眾號好比是一面鏡子,按別林斯基的話說,既然是鏡子,就要反映富有特征的客觀生活,必須始終保持與現實生活之間親密的血肉聯系﹔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論述,就是要“尊重現實生活”、“說明生活”﹔或者如杜勃羅留波夫提出的“人民性”的問題,他尤其強調文學應反映生活的主要動向,回應時代命題,描寫生活的本來面目,指出作家的主要價值在於描寫的“真實”﹔抑或像皮薩列夫的“現實主義者”,應當知道和了解他的時代和他的人民。“揚子江文萃”正是適應大眾心理新期待,要求作者持守有根的寫作,接地氣的寫作,為時代立言、為大眾立命、為凡人立傳、為文化立魂。數十萬粉絲每天翹首以盼新作的推出,那是他們心中執著的牽念。
──來自於直擊人心的感染力。讀“揚子江文萃”所刊的文章,仿佛是一次次觸及靈魂的相遇,它使我們抱有更多的熱忱與激情,真想成為“文萃”大家庭中親愛的、真正的、讓人信賴的一員。其所推出的散文隨筆,甚至如評論家徐循華先生所說的“能不能別太像散文”,但都能表露真心,流露真情,述說真事,傳達真思,給我們以深摯的心理治愈與審美慰藉,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讓人讀后不禁為之動容,這才是沾泥土、帶露珠、接地氣、通人脈的“人間煙火”啊!
“非虛構、接地氣、抒真情”,不僅“揚子江文萃”的用稿標准,也是作者需要把握寫作的關鍵妙招,它關乎“為何寫、寫什麼、如何寫”的大問題。
一是“非虛構”,彰顯現實的本色。真實是藝術的生命,“非虛構”是最老實的寫法,偷不得一點懶,摻不得半點假,也容不得耍花槍、玩花樣,“減去不必要的藝術描寫筆墨,騰出篇幅讓讀者知道各式各樣的人物和他們各自不同的活法,而且它們所呈現的民情、民風、民俗和民心,既有文學觀賞價值,又有不可多得的信息和史料的價值”(張韌語)。如葉櫓的《往事的魅力》、王干的《南京知青》、周旭的《尋常日子的生命敘事》《關於吃的記憶》、徐循華《丈母娘家的那些事》、王玉蘭的《神奇的針灸》《血壓二百六》《心動不如行動》、張潔的《我的“小店”夢》、常玫瑰的《玫瑰有約》、王正宇的《乘坐郵輪去旅游》等,寫的都是真人真事,都是定格在時光裡的歷歷往事,縱使歲月已換了容顏,有些事有些人從不曾忘卻,他們寫下的都是非虛構的生活“紀念冊”。揚子江文萃所提倡的“非虛構”,就是要真實地反映客觀的人、事、景、物,准確地表達真情實感,真實再現“我”的神韻,多寫富有表現力、啟悟力、感染力的細節,於平常瑣碎中發現妙處,在世間萬象中感悟人生,寫出平凡中的溫暖,平淡中的真情,平易中的深意,體現所寫題材的親歷性、紀實性與真實性,原汁原味,有滋有味,淡而有至味。揚子江文萃期待我們的不是造假虛構的寫作,而是一種動真格的建構,一種充分彰顯現實本色的寫作。
二是“接地氣”,呈現生活的底色。為揚子江文萃寫作,就要把握那些接地氣的東西、有底氣的內容。作者不能把自己閉鎖在象牙塔裡,也不可游離於栩栩如生的、真善美的、接近本真的、千變萬化的生活圖景之外,不能像某些西洋文學個別現代派作家,好像生活在雲端裡,似乎是精神貴族,那與人民距離太遠了,與當下現實生活太隔了,“揚子江文萃”可不喜歡這樣的東西。它希望作者由雲端回到大地,由渺遠回到身邊,由仰視回到俯瞰,由轟轟烈烈的人物場景回到“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的小家小戶過日子的景象,那種敦厚朴實、真淳自然、素面朝天的“質朴的氣韻”,那種與靈魂“裡應”兼與現實“外合”的藝術筆墨,那種傾力以赴現實生活氣勢宏大的“第一現場”而能夠如穆木天先生所曾說過的“捉住現實”的美學承襲。如周旭的《上河工》、王軍樂《長成一棵草》《野菜的味道》、張淑霞《探望》《下鄉種菜》、張篤德《我和我的工廠》等,這些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的尋常生活場景,很接地氣,有的甚至還帶有泥土的味道、大地的溫度、人間的煙火。揚子江文萃提倡作者要聚焦“客觀現實”,聚焦“社會動向”,讓散文在“接地氣”中添“底氣”,在“聚人氣”中增“大氣”,寫出“平凡的世界”中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悟,充滿對大眾的深摯厚愛,滲透人道主義精神﹔要關注“大地上的事情”,正因為有了這種溫暖與力量,我們下筆時才真正做到接地氣、有底氣,才能直面現實,干預生活,聚焦人生,不做時代精神的“睜眼瞎”,才能突現揚子江文萃倡導的以人為本和以“人的文學”為基點的寫作。
三是“抒真情”,守護心靈的原色。為揚子江文萃寫作,是“抒真情”的需要。有話要說,有情要言,正如宋人魏泰說:“述事以寄情,事貴詳,情貴隱,及乎感會於心,則情見於詞,此所以入人深也。”有深摯情感的文章,往往能彰顯其動人的魅力。如王慧騏的《那個給了我早期精神塑造的人》《昨日少年》、劉茁鬆的《萬家憂樂在筆端》、庄曉明的《爺爺是個孩子王》、周旭的《長生舅舅》、劉香河的《為母親梳頭》、林蕾《謝謝你,老張》《我娘要回養老院了》、王軍樂的《岳父》《你認識王軍樂不一定認識我》、趙光琦的《外祖瑣記》《家父》、申賦漁《看青的爺爺》、李貞琴的《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看你》等,情意綿綿,有情有義,感人至深。閱讀“揚子江文萃”,我時常感受到其文中的動情力,生活瑣事、人情風俗、所經所歷、所思所感等皆成文章,皆見性情。而情美又在於心靈的真實,著名散文家吳伯簫說:“說真話,敘事實,寫實物,實情,這仿佛是散文的傳統”,余光中說:“散文家無所依憑,隻有憑自己的本色”,這本色就是性情之真,也是揚子江文萃恪守的選稿准則,它要求作者抒真情,寫“真我”,守護心靈的原色,這是散文最為必需的基石所在。
《揚子江文萃》在新大眾文藝發展的大好態勢下應運而生。不久前我讀到了《延河》編輯部的署名文章《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一文,我非常贊同這樣一段話:新大眾文藝,“貼近社會,貼近現實,貼近大眾”“樹正氣,接地氣,有煙火氣”“讓大眾讀得懂,喜歡看,有收獲,能共鳴”“真正回到大眾,大眾寫,寫大眾,大眾享用,鼓舞大眾!”其實在此之前,“揚子江文萃”就是這樣做的,它把文藝從神壇上請下來,摒棄那些裝腔作勢、無病呻吟、為賦新詞強說愁的空文虛藝,大力倡導“人民大眾的自我書寫”。“文萃”發表的作品,也是變“少數人創作”為“多數人書寫”,變“少數人孤芳自賞”為“大多數人爭相傳看”,變評語的“隔靴搔痒”為論點的“切中肯綮”。它求真、向善、臻美,更在意平台發表的作品讀者認不認可,大眾買不買賬,網民點不點贊。文學創作不再是“你說我聽,你寫我讀,你文我賞”,而是堅持“美在生活,匠在民間”,大眾共寫共賞共建共享。幸得乎此,則“揚子江文萃”引起了廣泛共鳴、產生了深遠影響,相信“文萃”會越辦越好,越辦越紅火,越辦越出色出彩出新矣。(崔國發)
(來源:學習強國)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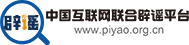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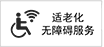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