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文物的重生:修復背后的記憶打撈
 222
222
點擊播報本文,約


馬耀南烈士的筆記及其在多光譜紅外頻段下的成像情況。受訪者供圖

一九四四年,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簽發的聘林邁可為無線電通訊顧問的聘書。受訪者供圖

1943年岱崮戰役中喝水的茶缸 受訪者供圖

《前奏》第十二期樂譜集修復前后對比圖(右為修復后)受訪者供圖

劉劍輝工作照 受訪者供圖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八十年后的今天,硝煙早已散盡,但那段用鮮血與生命鑄就的民族記憶,沉澱於一件件文物之中,並未隨歲月褪色。是血跡斑斑的軍裝、彈孔累累的紅旗、卷了刃的砍刀,也是鏽蝕的茶缸、泛黃的日記,還是記錄歷史的報紙、折痕疊加的地圖……這些沉默的見証者,歷經歲月。修復它們,不僅是為了留住一段記憶,更是為了銘記文物背后的英雄壯舉、家國情懷。
量身定制修復處方
抗戰烽火遠去,一件件抗戰時期的文物,將一段段血與淚交織的歷史封存。其中,記錄日軍暴行的報紙、烈士的日記手稿、珍貴書籍等紙質文物,因紙張的脆弱性而飽受“傷病”困擾:殘缺斷裂、霉變污染、虫蛀或老鼠啃食,還有折痕、變色、污漬水漬等“頑疾”。
那些曾被小心折疊存放的地圖、信件或手書,折疊處往往成為紙張加速老化的“重災區”,最終導致斷裂。山東博物館文物保護部副研究館員魯元良對此深有體會:“我們修復過長兩米、寬一米的地圖,因為長期折疊存放,折痕處幾乎全部斷裂。”
紙質文物破損后,修復師在修補時,需要選擇與文物在顏色、厚度、質地、紋路等方面接近的紙張。由於抗戰文物的紙張多與書畫古籍用紙差異顯著,修復師常需化身“造紙匠人”:他們先用儀器分析紙張的纖維成分,再精心配比紙漿,使用傳統造紙術的“抄紙”技術制出修復用紙。“抄出來的紙,厚度、顏色必須均勻”,江蘇文博文化遺產保護有限公司文保部主任趙丹丹強調,“我們可能要抄幾十張,才能選出一張最接近的”。之后,還要用色度儀和厚度儀檢測,修補用紙要與文物顏色和厚度無限接近,才算成功。
抗戰文物的修復保護,除了“修補”,還包括對文物進行復制,以滿足各種展覽的需求。中國國家博物館文保院書畫文獻修復研究所文物修復師劉劍輝告訴記者,國博的文物復制是“復原性復制”。“不同時期的文獻,紙張、工藝等都帶有那個時代的烙印。如果只是通過原色打印來復制文物,會丟掉很多歷史信息。”因此,復原性復制要遵循“原材料、原型制、原工藝工序”的原則,最大限度還原文物原件的歷史信息。以原材料為例,抗戰時期的文獻用紙,可謂五花八門,有傳統的手工紙,有近代從西方傳入的“洋紙”,有老區自制的“土紙”……不同的紙張,其造紙材料、紙張紋理都不一樣,如果找到材質、紋理接近的紙張,復制工作就成功了一半。
復原性復制還有一道重要的工序:將復制出的“完好”品做殘做舊,將文物原件的殘損樣貌與舊氣還原出來,再現其歷史流轉中形成的滄桑感。“經過這樣復原性復制的文獻,不光具有史料價值,還具有工藝價值。”劉劍輝說。
弱不禁風的不僅僅是紙質文物,也包括那些飽經風霜的歷史建筑。重慶大學內,那座融合歐式風格與中式小青瓦屋面、紅雕花門窗的“七七抗戰”禮堂,不僅是重慶抗戰歷史的重要見証,也銘記著抗戰時期國立中央大學遷渝辦學的往事。
然而時光無情,這位“高齡老人”已危在旦夕:外牆滋生菌藻,屋頂木構件開裂腐朽,飽受白蟻侵擾……面對這些“病灶”,“重慶大學‘七七抗戰’禮堂修繕項目”的文物建筑責任設計師陳蔚、項目主持設計師胡斌團隊在動工前,先用無人機和三維激光掃描等儀器對大禮堂的各個部分進行精確測繪,然后再對症下藥。例如,禮堂頂部原本的木屋架糟朽不堪,他們匠心獨運地採用了新舊屋架並置方案:按原樣式、尺寸制作鋼架,外裹鬆木,安裝在原有木橫梁旁邊,既加固承重,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珍貴的歷史原貌和信息,讓這座建筑得以繼續訴說往事。
多學科合力照亮修復之路
文物修復,“科技”含量不斷增加。修復前用儀器為文物做“全面體檢”已成常態:金屬文物用X射線熒光分析其材質和元素,掃描電鏡觀察局部病害﹔紙質文物則分析酸鹼度(pH值),鑒定墨跡是鬆煙墨還是油煙墨,還要取樣化驗,追溯其成分。
“酸化”是加速紙質文物老化的元凶,而“脫酸”往往需要浸泡或噴涂脫酸液,但近現代機制紙卻“怕水”。趙丹丹解釋:“宣紙是用細竹帘將紙漿從水中‘抄’出來的,不怕水,所以一般修復古代書畫時,工序中都是可以用水的。”而近現代紙上的紅藍鋼筆字,遇水即洇染。所以,脫酸成了大問題。不過從去年起,趙丹丹已經用上了南京博物院自主研制的無水脫酸溶劑,讓脆弱的機制紙也能安全“洗澡”。
面對新材料新設備,修復師們極其審慎。魯元良強調:“我們會先用舊書報反復實驗、分析研判,確認安全有效,才用於文物。”
科技之光,更能穿透時光迷霧,還原歷史細節。多光譜成像技術的運用,讓馬耀南烈士(1902-1939)的筆記內容完整面世。馬耀南是八路軍山東抗日武裝的重要領導人之一,被譽為“清河平原抗日的一面旗幟”。魯元良介紹,在修復馬耀南的筆記時,有幾頁上出現了字體暈墨、被透明膠帶遮蔽的現象,於是他們用多光譜成像技術還原文字。比如有一頁馬耀南的讀書筆記:“月亮懸在遠遠的一株鬆樹上。”“樹”字原被污漬遮蔽,在紅外光下拍攝的照片,則將其清晰顯現。
AI技術也加入了守護文物的行列。面對被水泡爛、撕裂又夾在玻璃板間的烈士照片,魯元良坦言,傳統修復技術已經很難施展。他選擇先加固本體、除塵清理、更換無酸紙,然后對其進行高清掃描,借助AI技術還原影像,再重新沖洗,讓模糊的烈士面容重煥光彩。
修復中覺醒的守護使命
每一次修復,都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
趙丹丹告訴記者,1941年創刊的《江海報》,記載了抗戰時期許多珍貴史料。南通博物苑收藏有《江海報》合訂本,但因其破損糟朽嚴重,已經無法翻閱。這也讓她意識到自己工作的價值和意義——讓革命先烈的遺存和那段烽煙記憶,更長久地保存下去。新四軍紀念館藏品部負責人潘麟之也深有同感:“有病害的抗戰文物要抓緊修復,否則文物的狀態會越來越差,就像生病的人,你不去治,他就會病得越來越重。”
在日復一日的修復中,抗戰文物背后的故事,一次又一次觸動修復師的心。魯元良修復過一個鏽殘嚴重的灰綠色搪瓷茶缸,這是1943年岱崮戰役中八路軍戰士喝水的茶缸。茶缸帶有很多標簽,有的是用小細繩拴了一個硬紙片,有的直接貼在缸子底。時間長了,膠質腐蝕了金屬,貼標簽的地方鏽蝕相當嚴重,甚至把搪瓷的琺琅體都破壞了。
魯元良在修復時,腦海中浮現了這樣的畫面:在萬余名日軍及飛機、重炮及毒氣彈的圍攻下,山上斷水斷糧,一茶缸水在戰士們手中傳遞,誰都不舍得多喝一口。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八連的93名戰士堅守陣地十余個晝夜,以傷7人、亡2人的代價,殲敵300余人,創造了以少勝多的奇跡。“文物是歷史的記錄者和見証者,把它們修復好,是我對革命先烈表達敬意的方式。”
劉劍輝在修復或復制文物前,必先深入了解其歷史背景,讓自己進入歷史場景中去。無論是想象烽火連天的戰場,還是先烈書寫家書時的柔情,都讓修復過程充滿溫度。“修復或復制的程序或許差不多,但對我來說每一件都不一樣。”他在復制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簽發的聘林邁可為無線電通訊顧問的聘書時,讀了許多關於林邁可的事跡。他了解到這位國際友人積極參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幫助中共改進無線電通訊設備,使世界聽到“延安之聲”,對這件殘破的証書也肅然起敬。“和平是這些仁人志士拋頭顱洒熱血換來的,保護好這些革命先輩留下來的文物,我們責無旁貸。”
從脆弱的紙張到飽經風霜的建筑,從先進儀器到修復師的巧手,抗戰文物的修復之路,是今人與歷史的對話,是傳承一段不該被忘記的民族記憶,延續革命先烈不朽的精神。這些歷經劫波的文物,提醒著我們:今天的歲月靜好,那是先烈替我們擋住了腥風血雨。(記者 李韻 王笑妃)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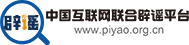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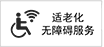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