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不是“重返”文学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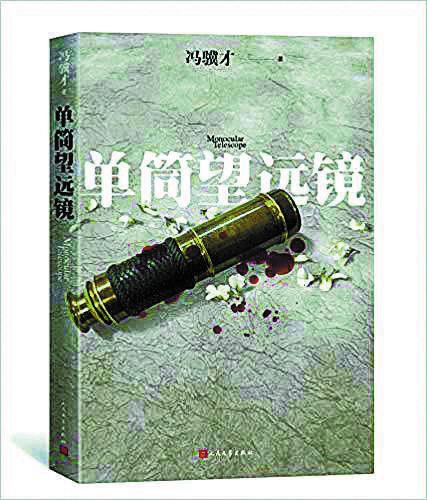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12月

邓勃 摄

黄天骥(左)为冯骥才颁发奖杯证书 周巍 摄
年度长篇小说
致敬词
冯骥才 《单筒望远镜》
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代表性作家,冯骥才先生的创作涉及多种体裁,小说、散文、诗歌、纪实……在虚构与非虚构的不同文体空间里,他左右腾挪,游刃有余。同时,他能反思传统,也反思现实,绝不自限于“文学”的层面,将美术创作、非遗保护、民间艺术也纳入他的文学空间。
他最新推出的这部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可视为回归之作,延续了文化反思的主题。从一段跨国恋情开始,以古朴精致的语言,行云流水的叙事,为我们展开了一卷真实、生动、厚重的历史画卷,在一百多年前的天津一隅,中西文化的碰撞跃然纸上。
一位会为自己笔下人物落泪的作家,一个藏在心里三十年才写出来的故事,仅凭这两点,《单筒望远镜》就值得我们致敬。
冯骥才和老伴闲聊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等我岁数大了……”这时候老伴会马上回话:“怎么你还没老啊?”
这位忘记自己年龄的老先生,今年春天凭一个奖,证明自己宝刀未老——他时隔30年推出的最新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获得2019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奖,而77岁高龄的他也不远万里从天津来到广州,和一波又一波的读者分享他的写作生活。
近30年来,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叱咤风云的冯骥才,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如今他带着《单筒望远镜》“重返”小说,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惊喜——
小说一般要改七遍
从未停止写作
卅年不断酝酿
羊城晚报:《单筒望远镜》是您时隔30年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力作,熟悉您的读者都为您“重返”小说欢呼雀跃,不知道您本人是否认同“重返”这样的说法?
冯骥才: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虽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进行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的保护,但我并没有停止写作,文学方面像散文、随笔都有,量不大,但针对文化遗产保护写作的档案、田野调查等文章量很大,绝对超过我的小说。我做文化遗产抢救前后20多年时间,如果两年写一部长篇的话,至少有10部长篇,相当于我放弃了10部长篇。谁也不知道,我把内心多么热爱的东西放下了,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所以大家现在说我“重返”小说,我是认同的,但我想说的是,我不是“重返”文学,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文学,包括《单筒望远镜》中的很多人物和故事情节,其实一直都在我的脑子里“写”。
羊城晚报:是什么机缘让您开始《单筒望远镜》的写作?写这个长篇花费了您多长时间?
冯骥才:这部小说在我脑海里已经酝酿了30年了。小说还没开始写的时候,先在脑子里写。对于里边的人物,不断地想,他们在我心里活起来,有性格了,有脾气了,跑来跑去了,最后想从我脑子里跳出来,跳到纸上去。但在2018年之前,我都一直没有时间去写,因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占用了太多时间,也没有这个奢望。
到真正动笔写这部小说时,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去年9月中旬,中国非虚构写作协会在甘肃张掖召开非虚构文学研讨会,研讨会当天上午我给1000多位观众做了一场演讲,比较疲劳,下午年轻人都跑去马蹄寺玩去了,我留在酒店休息,但靠在床头上也没睡着,靠着靠着忽然脑子里蹦出了几句话,就是《单筒望远镜》开头的那几句,它们就好像一个精灵,钻出来了,特别有感觉。我就用手头的iPad开始写,等他们回来时敲门,一看已经写了2000多字了。
从此就停不下来了,每天都在写,高铁、飞机途中都不放过,整个人被想象力主宰了,50天后,初稿就完成了。我写小说一般都要改七遍,这部小说也是,后来改了七遍才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
不只是复制生活
续写怪世奇谈
延续文化反思
羊城晚报:据说这部小说中不少荒诞离奇的情节源自您的亲身见闻,而您也一直擅长以民间传奇为脚本进行创作,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部小说中的真实和虚拟?
冯骥才:故事的原型是朦朦胧胧的,曾经听人家说起,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天津有个银行的职员和一外国女孩恋爱,语言不通,这个事当时闹得很厉害,外国人非要杀了他不可。放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一个很离奇、很荒诞的故事。但是这个悲剧爱情故事本身并不是我写作的目的,我是想通过这样的“情爱遭遇”去表现我想表现的“文化撞击”——在近代中西最初接触的时候,这对异国男女稀里糊涂地坠入爱河,却因为文化的隔阂、时代背景的悲剧性,注定不会长久。
羊城晚报:小说中涉及历史叙事的部分是完全真实的吗?
冯骥才:这些材料必须是真实的,是从生活里来的。写历史小说,材料就是从历史生活里来的。这需要大量的积累。比如我写天津老城,我在天津生活了几十年,对这个城市太了解了,我做过老城的抢救,曾经带着我的团队,将近100人,把整个天津的历史文化捋了一遍,重要的东西一一拍摄记录,对天津的每一条街巷,都有地图刻在心中。落到小说里,我的人物从什么地方来,去什么地方,都在我脑子里一目了然。对于那个年代的历史、生活、经济、社会、文化,拥有很多的细节记忆,但我都没有铺开来写,单单说纸局吧,我要不节制的话都能写几万字,因为我对这个太了解了,从小画画,围着纸局转,这一行里的各种规则,我太熟悉了。再比如说文人的书房,是什么样的,我跟老一代的文人接触多了,文人用的文房四宝、纸笔墨砚,书房是什么样的气息,都在我脑子里。我想给小说里的人物一个什么样的书斋,很自然就想出来了。
比如我写欧阳觉一家是从宁波来到天津,因为我自己就是宁波人啊。写宁波来的人物,我容易找到感觉。他们会从宁波带很多细节来,带来他的仆人,宁波人的吃饭、穿衣都有他们一套,宁波人都瞧不上外地的裁缝,我现在穿的外套都是宁波裁缝做的。
其实就是生活中很多零碎的细节,最终成为写作的素材。托尔斯泰的《复活》,里边写到有个女孩马斯洛娃眼睛有点斜视,我想他一定在现实生活中看过别的女孩眼睛斜视,跟这样的女孩目光接触时,会有一种特异的感觉,搁在小说人物身上,读者就会有相当真实的感受。这是小说家必须具备的素质,将万千的生活感受融会贯通,但到出手时绝不只是对生活进行简单复制。
羊城晚报:《单筒望远镜》的故事背景设置在1900年,而之前出现在您长篇《神鞭》《三寸金莲》中的“辫子”“小脚”也是那个年代的关键词,您为什么会那么在意那个时间点?
冯骥才:1900年是中华民族最贫穷、最愚昧的时期,我们在全封闭的情况下,眼光狭窄,对世界不了解,而且也受西方列强的欺负,这时候最容易看出我们民族自己的问题,包括鲁迅说的国民性的问题,也包括后来说的落后挨打的问题。中国的种种问题,在这个时代看得最清楚。我希望通过这个时间节点的小说创作,启发人们从历史上更深层次地去反思中西文化的交流,该如何去选择今天和未来的道路。
羊城晚报:选择单筒望远镜作为小说的一个重要意象,是基于偶然的灵感还是苦心酝酿的结果?它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
冯骥才:单筒望远镜在天津的古玩店里很常见,多是外国人留下来的。有一回我在古玩店看到它时,正好我在想这个小说,觉得特别适合。单筒望远镜有一个特点,必须一只眼看,有选择地看。在爱情的立场上,单筒望远镜一定是选择对方美好的视角。在文化的角度来看,单筒望远镜又一定会选择自己好奇的东西。小说中,欧阳觉和莎娜互相吸引,同时莎娜很好奇中国人的小脚,欧阳觉则看到外国人奇形怪状的头发、服装等,这都是单筒望远镜带来的选择。
用单筒望远镜作为交流媒介,当两种文明对立的时候,就会把对方的负面看得比较大。大量的误解,构成了那个时代的背景。选择对抗还是交流,决定了人物命运和历史的走向。这对现在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启示。
“我是一个失败者”
放下写作转型
卖画保护村落
羊城晚报:上世纪九十年代,您为何会暂别挚爱的文学,跳进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保护的“漩涡里”?
冯骥才:与其说是我的选择,不如说是时代对我的选择。我们赶上了一个社会转型期,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急速转型。这个转型当然是人类历史的必然,但转型的时候一定要将前面的文明成就瓦解、毁灭吗?当然不是这样,过去的文明中存在许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去传承,这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可是在中国人急于想富起来的时代,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人人都在追求物质。知识界站在文化的立场,总会比较早地发现这个问题,就应该有一批人先站出来,大声呼吁社会关注这个问题。最初,我喊出保护文化遗产时,人们还不理解,当时,我就是抱着一种舍我其谁的想法,只能先把写小说这支笔放下,做出牺牲。虽然说这样的牺牲对个人大了点,但我想回馈给社会的,应该是比小说意义更重大的东西。
羊城晚报:您觉得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成就感大过写作?
冯骥才:其实也不全然是,我其实是一个失败者,我想保护的东西,大部分没有保护下来。但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做,很多文化遗产再不去抢救,就全没了。像中国的古村落,已经进入一个消亡的加速期。经常是发现一个开发一个,实际就是开发一个破坏一个。要不就是根本不遵从文化规律,而是从眼前的功利出发,改造得面目全非,把真的古村落搞成了假的古村落。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有多少老村子,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村子的历史,在不知道的时候这村子已经没了。
后来国家意识到,村落的保护应该成为城镇化的一部分。2012年发动立档调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与认定,对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村落加以保护,在全国选择5000个极具历史价值的传统村落命名保护。
羊城晚报:您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光是为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保护出版的书籍数量就很可观,是怎么克服各种困难,坚持下来的?
冯骥才: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组织了几次画展卖画,将卖画的收入作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资金。有一年在苏州画展,我把心爱的画全卖了,一时觉得家徒四壁。当天展览落幕时,画作都有了买主,我让摄影师帮我拍了一张照片,从那一刻开始,就跟这些画作说再见了。不像书,画的原作卖出去了,就永远也看不见了。我还是很伤感的。
过去20多年,我白天往各地跑,做大量的调查,很多时间的写作是做文化档案、做普查提纲。没有人劝我这么做,但我觉得必须做,我想这是知识分子的天性,要让人们了解自己的文化是什么,了解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家底,才能真正催生对文化的热爱、对民族的自信。
非虚构也有魅力
应该放缓脚步
关注严肃文学
羊城晚报:虽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让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暂别小说,但最近几年您接连出版了《凌汛》《无路可逃》《炼狱·天堂》《激流中》等多部非虚构作品,非虚构写作近年来也很热门。在您看来,非虚构写作的魅力是什么?
冯骥才:非虚构的东西大家之所以比较喜欢,应该是虚构文学衰弱的表现。如果虚构文学能反映生活的本质,反映时代特有的魅力,就像19世纪那样不断有伟大作品诞生,那么我想它的空间不会被非虚构侵吞得这么多。但是说到底,非虚构也有非虚构的魅力,它凭着事实说话,它是历史的本身,也是现实的本身。只能说,我们的现实生活太精彩了,变化太快,太有吸引力,造就了非虚构文学的旺盛。
不过,事实的东西、现实的东西,是不是写出来就是文学,也不一定。记者也可以通过采访把事实写出来,写出来也是很好的作品,在新闻上也有很大的价值,但是它不是文学。非虚构文学是什么?是在现实中拿出有写作价值的东西,拿出来写的时候,它得是文学。文学的第一位是思想。人人都能写作,但不是人人都能创造。
我两种都爱,两种都写。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用了近十年采访调查,写了一本反映“文革”记忆的书,叫《一百个人的十年》,应该算是最早一批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吧。
羊城晚报:您说虚构文学在衰退,但是人们对文学的热爱却在升温。尤其是在广州这样的大都市,高质量的文学活动总是能吸引很多人参与。
冯骥才:这绝对是好事!人们关注文学,特别是关注严肃文学,说明人们对自身的精神生活要求越来越高了。严肃文学属于文化中深层次的东西,是更本源的文化,也更具精神性。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社会太物质了,人们应该放缓一下脚步,眼光不能只盯着现在,也要关切历史和未来。
冯骥才
祖籍浙江宁波,1942年生于天津。现任国务院参事、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定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等职。他是“伤痕文学”代表作家,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已出版各种作品集两百余种。代表作《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一百个人的十年》《俗世奇人》等。作品被译成十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四十余种。他倡导与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传统村落保护等文化行为对当代人文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吕楠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推荐阅读
相关新闻
- 评论
- 关注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