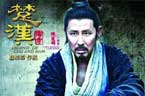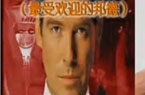也斯 本名梁秉鈞,1949年3月12日出生,祖籍廣東新會,1949年到香港,香港浸會大學外文系畢業,1984年獲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比較文學博士學位,曾任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主任。著有散文集《神話午餐》、《山水人物》,詩集《雷聲與蟬鳴》、《游離的詩》,小說集《島與大陸》、《剪紙》等。是香港最重要文化人之一。
在成為香港書展年度作家后半年,香港作家也斯便與世長辭。本月5日早9時,也斯在香港沙田的仁安醫院去世,享年63歲。而他的臨別遺願是,冀望香港文學能得到本地乃至世界的廣泛關注。
去世前3月還在做講座
也斯是香港戰后本土出生的第一代重要作家之一,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創作,多次獲得香港文學獎項。也斯2009年前被確診身患肺癌,並接受化療。
香港詩人廖偉棠說,兩個月前也斯的病已經很重,但還在去年10月和他一起做過一場講座,當時詩人阿多尼斯赴港,也斯和廖偉棠一起與阿多尼斯見面。“他在生命最后時刻一直都在努力,為文化推廣做事情。”廖偉棠說,這兩年,也斯意識到自己的時間無多,所以更加勤奮,“我們有時見到他都很心疼,越來越瘦,他得病以后沒有停下寫作,一直在寫,上一次我見到他,他還說要把生病治療的一些體會寫成詩,寫成文章。”
也斯還一直主持嶺南大學的研究工作,過去兩年主持出版了幾本香港文學梳理的圖書。“他一直都很強調一點,不要讓香港文學在全球的話語中消失,他很想盡自己的力量把香港文學推出去。”廖偉棠說。
為人和藹謙遜
廖偉棠說自己來香港定居后認識的也斯,開始覺得也斯德高望重,自己不太敢與他親近,接觸后發現也斯是非常和藹謙遜的一個人,所以二人很快成了忘年交。每次有外國或內地詩人、作家來到香港,廖偉棠和也斯都會一起帶著對方去一些很特別的地方吃飯,因為也斯也很懂得飲食。
華文世界最早用魔幻現實寫作的人
談到也斯的詩歌,廖偉棠認為和同時代的現代詩相比,也斯的詩歌不朦朧也不晦澀,在簡潔外表下有很大深意。同時也斯也很關注日常生活、關注香港的當下。“他有一本詩集叫《東西》,其中寫的是很平凡的事物,但這很平凡的事物都折射出在某一個特定的時代下,在香港或者作為一個華人對這個世界的反應。”
而對於也斯的小說,廖偉棠認為非常有實驗性,是整個華語世界最早一批受魔幻現實主義影響的小說。“像莫言都是80年代的事情了,也斯和西西在五六十年代已經開始實驗用魔幻現實主義來寫作,幾乎是緊跟著拉丁美洲的文學潮流的。”
廖偉棠認為,也斯、西西的一代,曾經代表了香港的文化精英直接和西方文化接軌。“你看也斯當時寫的影評都是世界上最前衛的電影,就算放到英美去,也是最前端、最前衛的。也斯他們所做的東西真的可以說是開拓性的,就是在一片荒野中,開拓出一些東西來。”而這些成果,廖偉棠認為在97之后真正成為香港年輕一代的精神遺產。
在嶺南大學發布的公告中顯示,也斯遺願是希望香港文學能得到更多關注,因為多年來香港文學處於邊緣地位,所以也斯希望香港本地優秀作家能夠受到關注,希望香港文學地位在將來得到平反。
■ 文學圈追憶
許迪鏘
也斯努力推廣香港文學
我認識也斯大概有30多年了,他是最初鼓勵我寫作的朋友之一。也斯在寫作上很努力嘗試不同文體,詩歌、小說、散文、評論,內容很廣泛。近年來他把生活上,譬如說飲食寫進小說,通過飲食探討不同地方的文化的相同和差異,這是大家都很喜歡的,也是大家比較重視的一點。他也很注意文字和不同媒體融合,比如他和很多不同媒體的創作者合作,攝影、舞蹈、裝置藝術等等。
我最喜歡的就是他的詩集《雷聲與蟬鳴》,他的詩歌很平實,生活感很強,但也有一些變化,比如他有一首詩寫新年,他說還有幾裡路就到新年,把時間化作空間,給我們一個新的對時間的看法。
也斯這幾十年來一直努力把香港文學推廣到香港以外的地方,他的遺願據說是希望香港文學會被世界上更多的人認識。
馬家輝
看他的散文,我覺得很溫暖
我在芝加哥大學時,有一個冬天下了很大的雪,我在圖書館翻到也斯在台灣出的一本散文集,印象非常深刻。看到他的散文,我就覺得特別的溫暖,好像碰到一個同鄉,一個故鄉來的人。1989年的冬天,我們開始書面交往。1997年,我回香港報社工作,開始有機會見面,一般都是在文學場合。
最后一次見他,是2012年的6月,我帶他去廣州演講,那時候他的病情已經控制住了,一般的說法是這樣。但我心裡不這樣想,因為我好多朋友、長輩得肺癌都是這樣子,肺癌是一種很令人討厭的病,通常你剛開始治療效果非常好的,突然控制住,好像沒事一樣,但一眨眼它突然又來了,所以我當時就有某種預感,果然就發生了。
也斯積極替香港文學平反,他覺得香港文學被文學界低估了,詩、小說甚至專欄都被低估了,他一直在做這樣的事情。 (記者姜妍 見習記者江楠)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