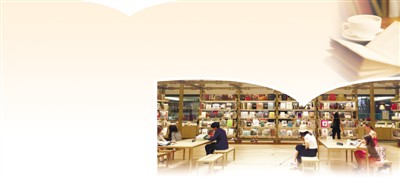 |
東京蔦屋銀座店的公共空間。 |
 |
布宜諾斯艾利斯雅典人書店一角,顧客正在書架旁安靜讀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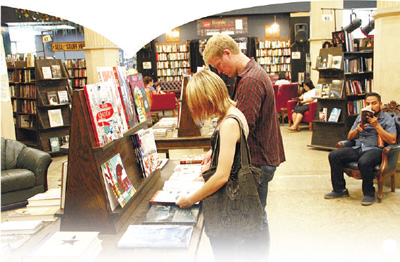 |
洛杉磯“最后一家書店”圖書展區。 |
 |
巴黎莎士比亞書店內的顧客。 |
 |
網絡大潮洶涌,實體書店式微。然而,世界上仍有一些特色書店業績興旺,甚至成為城市的文化標志,讀者的精神家園。秘訣在哪裡?歷史的涵養,創意的勃發,人文的關懷……
劇院變身最美書店
本報駐阿根廷記者 張衛中
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雅典人書店以華麗精美著稱,作為該市名片之一,外國游客甚至專門尋覓這處特色書店。
這裡原是大精彩劇院,建於1919年,能容納500名觀眾。4排包廂均衡排列在劇院舞台兩側中心位置,裝飾精美。拱頂繪畫主題為和平,和平女神在一片花簇中起舞,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變身書店后,地面層設為銷售和閱讀區,地下一層為兒童專用售書區和音像作品展銷區。內設扶梯,書店兩側拾階而上,可以預覽新書目錄,全球新書介紹等。書店內保留了古典歌劇院風格,舞台絨幕甚至是原配的。
書店市場開發負責人布魯諾非常樂意向記者介紹書店的早期歷史——這裡曾演出芭蕾、歌劇等,還被當作電影院。阿根廷數代探戈表演家在此演出,並將阿根廷探戈帶向世界。這裡也曾是阿根廷國內首次播放有聲電影的地方。
雅典人書店是一個連鎖店。2000年,雅典人書店租用了原來的大劇院作為售書場所之一。除這家書店外,其他分店所租用的地方也多為古典建筑。布魯諾說,所售書籍內容包羅萬象,從文學到科技,從兒童到企業管理,一應俱全,每年售書70萬本。由於書店的特色吸引人,每年到此參觀的人數就達80萬。
這是南美洲最大的書店,營業面積2000平方米。平日每天上午9點開門,晚上10點謝客。周末營業時間延長至午夜。
雅典人書店成功之處在於與時俱進。隨著數字化程度越來越高,雅典人書店也早就開始經營音像產品,但這家店從不經營電子書籍。書店內還開了一家咖啡廳。進入書店,讀者可以隨意挑書,選擇自己最喜歡的區域看書,並不一定購買。一架古式鋼琴,不時有人演奏古典樂章。記者在採訪時還發現一個現象,到書店購書或閱讀者兩極分化,尤以老年人居多,兒童則在父母的陪伴下讀書,接受環境熏陶。
布魯諾說,實體書店確實面臨網絡書店的巨大挑戰,隻有在保持傳統的基礎上,不斷發掘新的圖書銷售形式,才有可能繼續生存下去。阿根廷書店的普遍做法是,採用實體書店與網絡書店共同經營,滿足不同消費形式的需求。單純的實體書店危機已經存在多年,但最終沒有完全被電子書擊垮,是因為人們仍有傳統閱讀方式的需求,有著不同的消費感受。看什麼書,在什麼地方看書,仍有不同的消費心理。紙質書的好處仍是電子書所無法替代的。人們仍享受看書時的從容,與其他書一道放在書架上,可隨時閱讀,不用電,不用程序,有感處還可以做標記,或寫上幾句備注。紙質書也方便共享,並且還是文化傳承載體。不同版本的書,不同時代出版的書,有時甚至是舊書,其價值常常與年齡成正比,越老越值錢。
記者見到幾個學生模樣的讀者還帶了拉杆箱進店。他們告訴記者,學校開始放假,返鄉前他們到這裡替朋友購書,因為這裡的書最齊全。雅典人連鎖書店旗下還擁有一個出版社,一個網上圖書公司和一個印刷廠。
阿根廷《當代》雜志主編古斯塔沃告訴記者,實體書店面臨的挑戰不僅來自電子書,還有日益發達但有時很粗制濫造的多媒體、自媒體等的沖擊。實體書店與電子書並不是對抗關系,而是相互補充。實體書店目前還有其一席之地。
品味“最后一家書店”
本報駐美國記者 王如君
走進洛杉磯市中心的“最后一家書店”,扑面而來的是一股濃濃的“老味道”。書架是老式的,書桌是老式的,還有老書籍、老唱片、老鐘表、老收音機、老電扇等等,甚至那個用一本本舊書壘成的收銀台,都讓人感受到書籍的厚重和歷史的年輪。
一樓大廳分為書展區和唱片區,書展區全是書,新書和二手書都有。唱片區則是黑膠唱片天地,自黑膠唱片問世以來的產品,分門別類,應有盡有。不少顧客置身其間,有的手捧一本書,靜靜閱讀﹔有的則在一排排老書架間溜達,看能否淘到自己鐘愛的寶貝。一位來自西班牙的中年男子高興地對記者說:“你看看,這張黑膠唱片多棒!這是上世紀60年代‘貓王’的作品,我花了1個多小時才找到,回家后放到唱機上聽聽,那聲音、那質感,美極了!”
書店二樓處處洋溢著“藝術范兒”。走在嘎吱嘎吱的木質地板上,可以看到老式打字機吐出了“飛翔”的書稿懸浮於空中﹔用各種書籍裝飾的牆壁無疑是精妙的書雕﹔還有別出心裁的書洞和拱門式的書廊。二樓絕大多數是二手書,從政治、文化到宗教、歷史,分類很細。同時也有布置家居用的擺飾書籍,按書皮顏色分類。除了新書價格貴一點,二手書大多是一兩美元一本。二樓另一個區域則有很多手工小店,銷售手工制品與一些復古的擺飾。
多樣性也是書店的鮮明特色。書店除了售書、賣唱片外,還回收顧客的舊書,顧客也可來換書或贈書。此外,書店還提供座談、表演和簽名售書會的活動空間,時不時也舉辦作者演講、時裝秀等。書店不隻向愛書的人敞開懷抱,更向社會各界敞開大門。
據介紹,“最后一家書店”的創辦人喬希·斯賓塞曾做過十幾年的貿易,開過實體店也開過網店,最后決定將全部心思傾注到自己喜愛的書籍上來。書店於2005年誕生於洛杉磯市中心的一間小閣樓,隨著業務擴大,才搬進目前的地址。取名“最后一家書店”,多少體現了斯賓塞心中的無奈。眾所周知,隨著網上書店和電子書的風行,實體書店日益衰落。斯賓塞正是以其厚重的文化情懷和奇妙的創新設計讓“最后一家書店”散發出異樣光彩,吸引了大量顧客。
如今“最后一家書店”已成為加利福尼亞州最大的集二手書、新書及唱片為一體的書店,被評為洛杉磯最好的書店和全球最美的20家書店之一。隨著美名遠揚,“最后一家書店”已成為洛杉磯的名勝,不隻吸引著愛書之人,更吸引著觀景的游客。書店經理凱蒂·奧芬對記者說:“我們書店買賣的25萬冊圖書中85%是二手書。雖說面臨網上書店的競爭壓力很大,但我們有自己的風格和優勢。目前書店運轉正常、盈利良好,希望將來發展得更好,能夠吸引更多顧客和游人。”
生活方式的提案者
本報駐日本記者 田 泓
在眾多實體書店收縮規模甚至關閉時,日本蔦屋書店卻於今年4月在寸土寸金的東京銀座某商廈內開出了總面積達2300平方米的新店。短短幾個月,就實現日均到店顧客2萬人次的佳績,成為該商廈內集客力最高的商鋪。店長山下和樹自信地告訴本報記者:“書店贏利不成問題。”
其實,伴隨少子老齡化和閱讀無紙化,日本書店業不斷萎縮。僅2016年一年,日本全國有735家書店歇業,平均每天關門兩家,甚至出現全城沒有一家書店的現象。蔦屋何以能逆勢上揚?
據山下店長介紹,銀座店主打“藝術”概念,目標顧客為50歲以上“有閑有錢有品位”的日本人和對日本文化有興趣的海外客。書店以100位各個歷史階段有代表性的藝術家為主軸,展示來自全世界的6萬冊藝術書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巨書角”,陳列著50本50×70厘米的大書。要知道,這種大部頭在其他書店有一本就很稀奇了。
“藝術”的另一層含義是藝術詮釋手段的多樣化。書店不吝空間,採用日本傳統建筑樣式“櫓”搭建起6米書架,形成一個敞亮的公共區域。這裡是顧客的休息閱覽區,也可作為新書發布和商業營銷活動場地。
蔦屋書店必備的星巴克,在這裡也有了升級,是少有的可以品嘗到手磨咖啡的地方。配有高腳凳的長條桌上,放著雜志、畫冊和提示紙條——“請在喝咖啡時享受閱讀的樂趣”,完全不同於通常書店禁止帶入食品的規定。
蔦屋書店母公司是日本規模最大、擁有1400家店面的圖書和音像制品零售出租連鎖店。從1983年在大阪開出第一家蔦屋書店,創始人增田宗昭從未滿足於既有成功,不斷嘗試拓展。2003年在六本木書店引進星巴克,打造咖啡讀書廳概念﹔2011年在代官山開設集商場、餐廳於一體的生活提案型書店﹔2013年接手改造武雄市圖書館,讓一個人口僅5萬的小城鎮創下每年吸引游客人數超百萬的奇跡﹔2015年推出新型家電賣場“蔦屋家電”……每一次創新都引發商業和文化界的熱點話題。
“蔦屋不光賣書,還要做生活方式的提案者。”蔦屋書店母公司CCC公司公關負責人元永純代告訴記者,蔦屋書店摒棄了傳統書店按照書的形態(旅游指南、參考書、漫畫等)進行分類的方式,而是按照書的內容、生活場景進行分類,重構書店空間。同樣是賣烹飪書,蔦屋會在周邊布置相關的食材和廚具,讓消費者一下進入“理想廚房”的情境。
增田宗昭在《解謎蔦屋》等書中,闡述了辦書店30多年的心得,對實體書店業頗有啟發——
“若要以量取勝,顧客隻要在網上購物就好。人們前往實體店,就是為了逛得津津有味才去的。”
“對顧客來說,有價值的部分不是書本身,而是書裡的提案。”
巴黎的文學“烏托邦”
本報駐法國記者 王 遠
在巴黎,恐怕每一位文學愛好者都繞不開莎士比亞書店。
從外面看,書店門面並不大。招牌中央擺放著一幅莎士比亞肖像畫。一扇門的門框上,寫著這樣一行字:“不要對陌生人冷漠,他們也許是偽裝的天使。”這種待人的善意與慷慨,讓書店成為不少文人作家棲居創作的庇護所。
書店建筑原址是一處始建於17世紀的修道院。1951年創辦書店的喬治·懷特曼曾說:“中世紀時,每個修道院都有一個掌燈者,專門負責夜幕降臨時點燈。我就是這裡的點燈人,扮演一個不起眼的角色。”他說,自己創建這所書店,就像寫小說的人,把每個房間都當做一個章節來構建。“我希望人們推開書店的門,就像翻開一本書一樣,這本書把他們引向一個想象中的奇妙世界”。
書店最初名為“密斯托拉”,1964年莎士比亞誕辰400周年時更名為“莎士比亞書店”——不隻寄托了喬治對在巴黎首創莎士比亞書店的書商雪維兒·畢奇的敬意,更是延續了老牌同名書店溫暖好客、支持無名作家的精神。
上世紀20年代,畢奇的莎士比亞書店不僅是供人借閱、購買圖書的地方,而且出於支持作家文人的初衷,為他們提供創作的港灣——海明威、喬伊斯、斯泰因、菲茨杰拉德等知名作家旅居巴黎時,都曾在這家書店棲居過。但不幸的是,畢奇因為在二戰期間拒絕向德國軍官提供詹姆斯·喬伊斯作品《芬尼根的守靈夜》最后一份副本而被捕,身心受到打擊的她最終選擇了徹底關閉莎士比亞書店。
時光流轉,畢奇和喬治都已經離世,現存的莎士比亞書店卻依然是文人墨客的避風港。書店二層的沙發、座椅、行軍床、打字機見証著幾十年來在此停留的不知名作家。書店為他們提供食物和臨時床鋪,讓他們在此度過一晚上、一星期甚至數月。據粗略估計,這家書店前后收留過約3萬名需要幫助的作家。在這裡住下隻要做三件事:每天讀一本書、給書店幫忙幾小時、留下一頁紙自傳。如今,這些數以萬計的自傳已成為幾代作家、旅行家與夢想家故事的珍貴檔案。
現在,莎士比亞書店擁有近5萬本新書和2.5萬本二手圖書,每天接待顧客超過400人次。在實體書店紛紛迫於壓力關門的時代,反而煥發出歷久彌新的光彩。
據書店目前的主人西爾維婭·懷特曼介紹,在租金飛漲的時代,作為業主不用交租金無疑為書店省下一筆可觀的開支。此外,書店管理團隊的經營方式也十分重要。除了每周至少組織一場讀詩會或閱讀交流會,莎士比亞書店也會評選自己的圖書獎,吸引了世界各地未發表的中篇小說作家參與競選。為了跟上互聯網的大潮,書店也有專門的團隊運營官方網站,讀者即使不親臨書店也能在網上完成購買。當然,真正支撐這家傳奇書店受歡迎至今的最重要原因,恐怕還是書店本身作為一種符號,所象征的對於不知名作家開放而友好的人文關懷。
版式設計:蔡華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