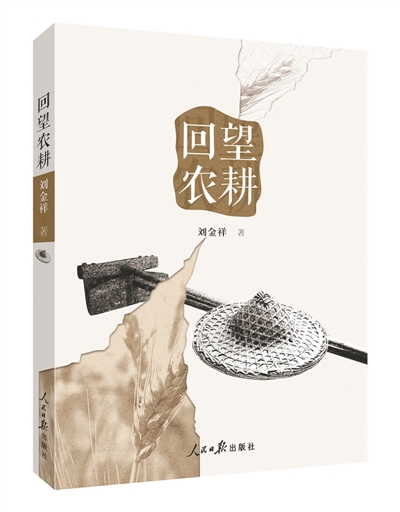 |
在中央宣傳部、人民日報社工作時間較長,接觸農耕文化方面的文章和書籍相對少了,最近讀了劉金祥同志寫的20世紀江蘇裡下河地區農民耕種農具的書稿《回望農耕》,迅即勾起我對過去深深的眷戀,讀后倍感親切,耐人尋味。
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的國家,農耕文明佔據了很長的歷史時段,它熠熠生輝於世界文明史。由田、牛、犁、人構成的畫面,是農耕文明時期最常見的生動場面,而農具更是農耕文明的重要結晶。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古代哲人確立的命題,集中體現了中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世世代代依賴並運用的農具,已然成為順應自然、利用自然、保護自然和維持生存、延續后代、生生不息的活化石,映射著先祖們的聰明智慧,映射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天人合一的動人情境。
上古時期,大禹治水分置天下為九州,揚州為九州之一。我的家鄉在今天揚州、泰州所轄的裡下河地區,裡下河地區依江蘇省江北裡運河(江淮之間的運河曾被稱為裡運河或裡河)與“下河”(串場河)而得名。“下河”最早始於宋代,明代稱東下河,清代稱為下河,民國時期稱裡下河,流經泰縣(今泰州市姜堰區)、興化、江都、高郵、寶應、東台、鹽都、建湖、淮安等九縣。裡下河地區現在范圍是,西起裡運河,東至串場河,北自蘇北灌溉總渠,南抵通揚運河,包含揚州、泰州、南通、鹽城、淮安五個地級市的十多個縣市區。裡下河地區地勢低窪,水網密布,河港交錯,湖泊眾多,盛產稻米、小麥、魚蝦、螃蟹,是名副其實的魚米之鄉。這裡的農民更具有勤勞、勇敢、智慧的優秀品質,這裡的農耕文化更是源遠流長、內涵豐富,這都成為江淮文化和中國精神的寶貴財富!
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土壤結構、氣候特點不一,適合生長何種農作物雖有地區差別,但從古到今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農具是類似的。那些農具一直使用到21世紀初,有的如今仍在使用。現在的農具先進了,逐步實現機械化,不少已是高科技了。那些已被或將被新型機械、高科技取代的農具卻是人類生產生活歷史長河中寶貴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如同發現了幾千年前的一把已沒有了鋒刃的鏽刀、已經破損的石器那樣,雖已無實際用處,但對研究人類歷史進程有著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這就是我們要保存這份遺產的真正動因。
每個中國人幾乎都是念著“鋤禾日當午……粒粒皆辛苦”的詩句長大的,但現在許多人已不知曉農民多麼艱辛。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天及將來高科技的耕種方式,都不可能“天種人收”,總得靠人們用手中的農具(機具)去完成播種、管理、收割、揚晒、儲運等工作。盡管人們對過去農具的知曉程度不一,或是生長在大城市裡的人,或是學生和還沒懂事的孩子,但他們遲早會有機會去接觸它,甚至將來會有不少人成為運用農具的行家裡手或研究農具的專家學者。
我是1977年參加高考后離開泰縣沈高人民公社河橫大隊的,在這之前一直參加隊裡的農業生產勞動,許多農具我都使用過並且非常熟悉。比如,灌水要有踏車、風車﹔割麥割稻要有鐮刀、草腰子﹔挑把運把要有把叉、農船、竹篙﹔挑糞挑桶兒泥要有扁擔、糞桶、舀子﹔挑渣要有泥拉兒、釘耙﹔挑河要有大鍬、擔子﹔碾場、摜把、壓麥苗要有碌碡,等等。當年,農民天天有活干,從大年初一“開門紅”到年三十上午收工再迎新年。我們大隊每年種“三熟”(兩熟稻子、一熟麥子),年年都有“雙搶”(搶收、搶種),勞動強度大,勞動周期長。那時我與家鄉人民從事農業勞動,與天地相伴,與農具為伍,腳踏實地,送走太陽迎來月亮,至今想起那時的勞動場景仍歷歷在目。
金祥同志寫農耕文化的出發點在於他生長在農村,並在多個鄉鎮工作過,在農村的時間長達二十余年,從一般干部到領導干部,都是與農民打交道,對“三農”問題情有獨鐘。在此之前他曾寫過一本書叫《根戀》,我也看了,敘述詳實,感情細膩,語言豐富,文字流暢。他的寫作特點與風格較為特別,寫農具也是如此。把握不同農具的特點,以一個個真實、精彩、鮮活的勞動人民的故事,謳歌了在農業生產一線勞作、心地善良的“泥腿子”。每件農具都在他的筆下變“活”了,有“動感”了,件件有靈性,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一年四季,農活有若干種,耕作、播種、管理、收獲、運儲等,農具在農民手中所承擔的作用,由他勾畫出來,儼然就是一幅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圖”。
說實話,對“三農”情況能夠深入了解,把農具“連起來”並寫出來是有相當難度的。因為不僅要懂得我國農耕文化的歷史演變過程,還要懂得農具的結構、用途,實踐過、研究過它。正如金祥同志所說,如今地道的農民已不多見了,更何況,改革開放這麼多年,從收、種、管到裝、運、儲,當年那些農民愛不釋手的農具在哪裡?那些已經“隱身”幾十年失去“聯系”的農具,想找到它,說出它在何時用、用途如何談何容易?可喜的是,經過較長時間調查整理,東奔西跑許多地方,金祥同志這份不可多得的收獲終於使他如願以償。
在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信息社會的今天,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人多了,不忘初心、砥礪前行的人多了,但毋庸諱言,數典忘祖、不識東西的人也多了,好高騖遠、不願吃苦的人也多了,這當然可以從社會急劇轉型中得到解釋。在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價值多元化、文化多樣化的時代背景下,每個國家、每個社會都有學習互鑒的機會,每個家庭、每個人都有學習選擇的機會。但應當明白,價值再多元,總有一元為主導﹔文化再多樣,總有一樣為主流,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一直以為,泥土出芬芳,堪比桂花香。農具今猶在,田間耕耘忙。這些年來,劉金祥同志以農具為對象,深入田埂地頭,進入農家庭院,出入採訪調研,專心寫成該書,實在令人感佩。我相信,該書的出版定能給農耕文化留存難得的珍貴資料。
(作者為人民日報社原副總編輯。本文為人民日報出版社《回望農耕》一書序言,本報編發時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