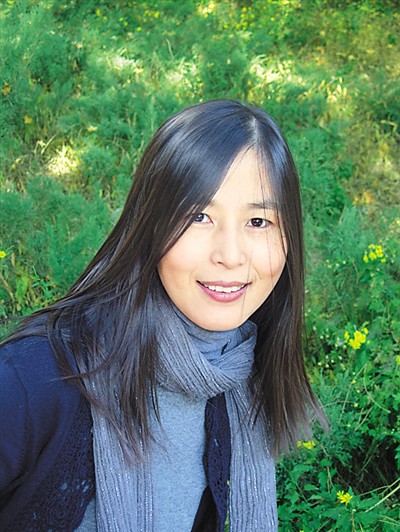 |
●女作家,也不止女作家,一生迷戀紙上世界,大約無非就是尋覓那個知己吧
●女性命運,大約從來都同其個人情感境遇有著纏繞不清的關聯
最近,性別意識、女性寫作、女性經驗、女性主義等話題常常被提起、談及。我也經常被讀者問到,作為女作家,你覺得優勢和難處是什麼,你如何看待?老實說,我一點兒都不覺得被稱為女作家是一種冒犯,或者是評判標准的暗中降低,是男性中心話語陰影的遮蔽或者覆蓋。我也不認為,女作家就一定沒有作家那麼響亮、正大、高級。女作家就是女性作家,不必過於敏感和糾結。
自然了,因為性別差異,到底是男女有別。女性好像更細膩、更柔軟,心思幽微,一腔柔腸,千回百轉。兩個女人見面的問候,往往是,“你這裙子真好看”。這是女人之間的禮節,也不必當真。就像一個女人哭訴她先生的種種不是,最好的態度,大約是幫那可憐的先生說話。梁實秋在《論女人》中說,假如女人所捏造的故事都能抽取版稅,便很容易致富。奧斯卡·王爾德也說過,藝術即是說謊。在這個意義上,女人或許是天生的小說家。打著虛構的幌子,一本正經地說謊話,隻不過,兜兜轉轉,她總有本事自圓其說。小說是什麼呢,其實就是小聲說說。這是汪曾祺先生的話。一個女子,她的生活或者圓滿,或者有缺憾,她內心裡總不免孤獨。心有郁郁,無以遣之,遂一發而為筆墨。她本是自言自語,說給自己聽的﹔倘若無意中被人家聽到了,心有戚戚者,便是知音了。女作家,也不止女作家,一生迷戀紙上世界,大約無非就是尋覓那個知己吧。
多年來,我一直寫故鄉“芳村”,寫鄉土中國。“芳村”一直是我文學創作的精神根據地,長篇《陌上》更是“芳村”這一文學版圖的集中呈現。以物理時間計,我的城市生活比鄉村生活更長,與我耳鬢厮磨、日夜相對的其實不是“芳村”,是城市。作為小說家,我遲早要把我置身其中的城市寫出來,即將出版的新長篇就是我積累多年之后的一次嘗試。
小說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書寫一個女性的精神成長和命運遭際:從鄉村到城市,從芳村到京城,那道射向精神的隱秘的微光,不斷照耀,不斷閃爍。內心世界的千回百轉,情感生活的顛沛流離,心靈的動蕩難安,人性的撕裂和掙扎,價值的顛覆和重建,精神的蛻變和新生,所有這一切,都成為深刻的痛楚的烙印,影響並重新塑造著人物的精神面目和心靈世界。人生困境中的不屈和不甘,對人性尊嚴的捍衛和珍惜,暗夜中的彷徨歧路,內心力量的生發、積累以及壯大,女主人公在生活的激流中沉浮輾轉,在命運的壁壘面前跌跌撞撞,傷痕滿懷,最終獲得了內心的巨大安寧。
這部長篇書寫城市,但我的芳村始終在遠離城市的地方默默佇立,暗中相助。一個芳村女子對於城市的想象和期待,在現實的強大碾壓之下,如何破碎,如何百般縫合而不得?千瘡百孔之后,如何在生活的烈焰中艱難重生?如果把這部長篇視為“我”的自敘傳,那麼,這部小說大約也可以看作是一個女性的個人史。個人的,私密的,曖昧、復雜、豐富、幽深,一言難盡,有著強烈的女性色彩和個性氣質。
女性命運,大約從來都同其個人情感境遇有著纏繞不清的關聯。在某種意義上,女性的情感深刻影響甚至決定著女性命運的走向。小說以人物情感為脈絡,跨越近40年,書寫了一個女性從少年、青年到中年的成長歷程,從天真稚嫩到飽經滄桑,再到純淨如水﹔從內心動蕩到內心安寧﹔從單純到復雜,再到重歸單純。城鄉文化的碰撞交鋒,異鄉人的新鄉愁,殘酷的城市生存法則,北京新移民的中國故事……小說以巨大的敘事耐心,仔細勾勒出一代人的精神地形圖,寫出了社會轉型期新的中國經驗。小說在現實和回憶之間自由往返,有時間的縱深感和蒼茫的命運感。看似日常的敘事背后,有大的時代背景若隱若現。個人命運和時代生活之間的關系纏繞糾結,有一些意味深長的東西在裡面。
在結構形式上,小說的主體部分之外,還插入了七個短篇小說。插入部分和主體不斷對話、對峙、反駁或者爭辯,構成一種巨大的內在張力,從而有一種多聲部的敘事效果。現實和回憶不斷交錯、閃回、纏繞,敘述上更自由更從容。
夢裡不知身是客,且把他鄉作故鄉。這部新長篇裡的疼痛、創傷、蒼涼、孤寂,最終都獲得了撫慰和安放。理解和體恤這世上人心的苦難,諒解並且熱愛這世上的一切,這是地母般的遼闊、溫厚、包容和悲憫。雖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