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王鬆長篇小說《煙火》:“津味小說”的新標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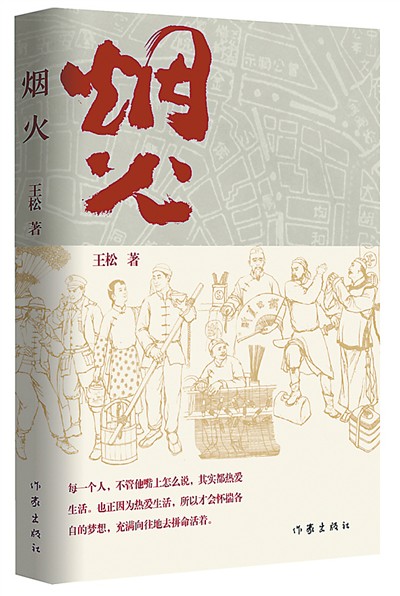
王鬆的《煙火》寫的是天津,卻從一條胡同寫起,故事也主要圍繞胡同裡的人和事展開,這不能不讓人想起老舍的《四世同堂》。《四世同堂》被認為是“京味小說”的代表作,“京味小說”的名號早已叫響,“津味小說”的說法卻少有人提。王鬆在小說后記裡說,他也是因為這部小說才聽說這個詞兒,還覺得挺新鮮。不過以后如果要追溯“津味小說”的歷史,《煙火》會是一部繞不過去的佳作。
《煙火》裡的“蠟頭兒胡同”,原本叫“海山胡同”,一條窄窄的胡同,卻能夠連著山、接著海,簡直可以通達天下,這正是《煙火》所寫出的天津城與天津人的宏大氣魄。小說講述的故事的確未曾遠離這條胡同,最多不過延伸到租界和武清﹔但在小說人物的命運背后,卻始終映現著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起伏。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歷史事件,不時穿插在市井味道濃郁的胡同故事裡,足以讓讀者明白這座城、這條胡同,終究也是宏大歷史的一處小小舞台。這樣一種重影般的敘事效果,難免讓人想起《四世同堂》:老舍讓抗戰的硝煙,始終彌漫在小羊圈胡同的上空,而《煙火》所涉及的歷史更長,從1840年“白河投書”一直寫到21世紀。
以一個人、一個家族、一條胡同,乃至一座城市來折射歷史的作品可以說是汗牛充棟,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稍微有些歷史感的長篇小說大都採用了這種我稱之為“重影式敘述”的寫作技術。在小說中,宏大的歷史進程一定需要充沛的生活細節來填充,抽象的歷史邏輯必須依靠生動的文學形象來演繹。只是生活細節、文學形象和它們背后的歷史與邏輯各自佔多大比重、彼此之間又構成怎樣的關系,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作品的可讀性與藝術性,甚至也決定了小說的歷史洞察力。
《煙火》中,王鬆始終小心翼翼地控制著筆墨,盡量不讓胡同之外的歷史風雲過多地、過於直接地卷到胡同裡來。王鬆更關心的是如何從這條胡同和這座城的角度去看待歷史、感受歷史、與歷史發生關系。作為小說家,王鬆非常清楚,自己的責任在於立足“小”,而非妄言“大”,因此他不厭其煩地講述天津的空間形制、沿革掌故和民風民俗。但是不要誤會,《煙火》並不是一座關於天津的紙上博物館,所有的知識都被他編織成了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從而不再是單純的知識——蠟頭兒胡同裡的住戶,大多是手工業者,他們所經營的行當涉及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們吃穿住行,他們走街串巷,他們喜怒哀樂,這裡面天然就有老天津的日常生活、城市景觀與市民性格,也有推動這部小說前進與轉折的動力。《煙火》因此不至於像很多重影式小說那樣,淪為宏大歷史的乏味圖解或可憐注腳。王鬆的關注焦點在歷史,但更在天津,他沒有把一部小說寫成史傳,也無意繪制歷史圖卷,而是要畫一張風俗畫。但是好的風俗畫不正是格外生動的歷史圖卷嗎?
了解一部重影式小說的重心與目的,隻需要判斷台前與幕后的兩幅影像哪個是影,哪個是身。以此為據,我們可以更加明確,王鬆的《煙火》究竟是要為歷史作注,還是要為城市寫心。很多重影式小說裡,情節與人物背后的龐大歷史就像是木偶的提線,總是緊緊攫住故事的走向與命運的周折,小說就像一隻瑟瑟發抖的兔子,在歷史巨獸面前毫無還手之力﹔而在《煙火》裡,情況卻有所不同。
小說通過洋人下令拆天津城牆和“天津教案”等歷史事件中,石鐵匠、老疙瘩、劉大頭等人物的表現,刻畫出天津人的嫉惡如仇、家國情懷以及一點就著卻又深謀遠慮的性格特點。王鬆筆下的這類人物和那些在歷史巨獸的爪牙下無可如何的小說人物相比,精神格外張揚,力量格外驚人。給人的感覺是,天津這座城和城裡的人們在拽著歷史往前走,而非任由歷史擺布。
那麼這座城市的獨特氣質,與天津人的特殊性格,究竟是從哪裡來的?我們似乎可以從主人公來子(牛全來)身上找到答案。老天津的文化涵養了他,使他具有大氣穩重的性格,處事干練機敏,是天津人的優秀代表。“狗不理包子鋪”的高掌櫃曾經琢磨過來子的性格,認為他結合了父親的迂和母親的暴,這恰恰分別代表了天津男人和女人的典型性格,兩相中和,便讓來子既寬仁厚道又綿裡藏針。不過這對素來不能和睦共處的夫妻早早離散,對於來子的影響終歸有限,倒是借用高掌櫃這番互補對沖的理論,可以找到另外兩個人,構成來子性格更為重要的來源:其中一個正是高掌櫃本人,而另一個則是那位出身書香門第的尚先生。
高掌櫃是買賣人,《煙火》裡反復強調,買賣人做生意是白刀子進白刀子出,打開店門迎接八方來客,沒有手腕是不行的。但王鬆並未過多渲染高掌櫃的生意手腕,他收留流離失所的小閨女兒,照應失去父母的來子,幫襯街坊鄰居的喪事……高掌櫃與其說是商人,不如說是地方鄉紳。事實上,王鬆筆下的天津有著中國傳統城市那種濃郁的鄉土氣息和人情味兒——這座城裡看似八竿子打不著的人,轉幾個彎就認識了,這樣錯綜復雜的人際網絡簡直令人疑心這不是城市,而是鄉村。
更重要的人物是尚先生。小說從尚先生搬來胡同講起,又基本終結於尚先生去世,這位老先生是這條胡同乃至整部小說的定盤星。尚先生出身知識精英階層,家道中落才搬到這條胡同,靠看相、行醫和代寫書信為生,進了臘月二十,也會在胡同口兒擺個賣香燭神祃兒的小攤兒。尚先生的經歷在某種程度上演繹了中國傳統的精英知識是如何下沉並演化成民間的是非觀念的過程。千百年來,政府自上而下的教化固然重要,但落魄知識分子隱入民間,卻能夠更為身體力行地影響鄰裡風化。因此在這條胡同裡,尚先生扮演著評斷是非的角色﹔也因此,尚先生自刻自印的神祃兒,不僅是地方民俗,更是文化傳統的象征。
理解了《煙火》中天津這座城市的歷史能動性、天津人的性格特征,以及它們的由來,我們或許能更為准確地把握王鬆對這部小說和這條胡同命名的用意——“煙火”指向的當然是市井與民間,在王鬆看來,正是在嘈雜而豐厚的民間市井生活裡,才埋藏著這座城市乃至於這個民族最為重要的力量﹔而人們之所以更願意管這條胡同叫“蠟頭兒胡同”而非“海山胡同”,或許在他們看來,重要的不僅是廣闊空間裡一時的風雲變化,更在於歷史與日常生活深處那綿延不絕的文化力量。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推薦閱讀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