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月》创刊号。

《十月》2013年第五期(9月10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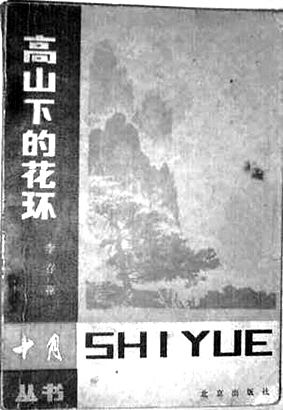
《高山下的花环》

《北京人在纽约》

《黑骏马》
36年前,出版社编辑张守仁和王世敏、章仲锷,在一次会议间隙,到宾馆外的花园里聊天。那次关于文学潮流的闲谈,孕育了一年后创刊的《十月》。《十月》一创刊便声名鹊起,1981年最高印数已达58万5千册。“那时印《十月》十趟车拉的纸都不够”。之后刊发《高山下的花环》在全国引起的震动,至今依然罕见。不过,潮起潮落,那个文学爆发的黄金年代已然成为历史,众多文学期刊今天都面临发行量下降的困境。尽管如此,《十月》依然在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前行,“我们依然可以做出有价值的作品。”
《十月》杂志是一本创办于1978年的大型文学杂志,主要登载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剧本、诗歌等文学作品。发行周期为双月一期。单月10日出版。现任主编曲仲,常务副主编陈东捷,副主编宁肯、赵兰振。2004年起,十月编辑部同时编辑、发行另外一本原创长篇小说杂志《十月·长篇小说》,每年6期,双月10日出版。
酝酿 聊天聊出来的文学杂志
1977年夏,山东,天气炎热。张守仁、王世敏和章仲锷在一个文联会议的间隙,跑到会场外的树阴下纳凉、聊天。闲谈中,三人都预感到一个文学的潮流正在逼近。十年动乱中历经曲折的作家开始纷纷从下放的农村返回城市,他们一定迫切想把积累多年的生活感受用文学的方式宣泄出来,因此需要一个平台让他们的作品得以发表。于是三人一拍即合,决定创办一份文学杂志,他们站在树下商量刊名,从《东风》、《首都文学》一路聊开去,最终敲定了名字——《十月》。
“因为十月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都是有意义的日子,十月革命在十月,中国的红军长征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打倒四人帮也是在1976年10月,同时十月也是收获的季节,人们经过一年的辛勤劳动,到了秋天便会收获。”多年后,回忆起起名缘由,张守仁如此说。
从1978年8月《十月》创刊,到如今已有35年的时间。作为“文化大革命”后创刊的第一家大型文学期刊,它见证了一个时期文学之于社会的作用。
2004年谢冕曾为《十月》创作一篇文章,题目即为《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
创刊 《爱情的位置》第一次冲破禁区
距离三人决定办刊有一年时间,《十月》才得以问世。“因为当时很多作家没能马上回到城市,很多稿子没有出来,我们筹备了一年时间,才凑齐稿子,得以发表。”张守仁说。《十月》第一期刊发的文章有茅盾的《驳斥“四人帮”在文艺创作上的谬论并揭露其罪恶阴谋》、陆柱国的中篇小说《吐尔逊的故事》、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郑万隆的短篇小说《铁石老汉》以及李凖的《的创作札记》,此外还有介绍中文文学名著的“学习与借鉴”栏目。而在“编者的话”中编辑部用这样的句子表达自己的文学旨趣:“我们希望在这一园地上,能够不断涌现出一批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的、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好作品。”
其实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十月》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并非分量十足,但却不妨碍它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创刊号上影响最大的作品当属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这篇被誉为“文革”结束后最早在文学中恢复爱情记忆的作品,因为第一次冲破爱情的禁区,一经发表《十月》编辑部便收到5000多封读者来信。由此全国各地都知道北京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学刊物《十月》。
“我们当时就好像一枝报春花或报春鸟,预示文艺春天的到来”张守仁说。《十月》创刊之后半年,上海的《收获》复刊,一年后北京的《当代》创刊,之后广州的《花城》、江苏的《钟山》纷纷涌现,许多大型文学刊物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国各地生长。“那时人们都把文学当做一个窗口,而《十月》恰恰又是文学和思想的窗口”张守仁说。
一个阅读文学作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心的时代降临了。
辉煌 《高山下的花环》引发轰动
《十月》处于这个时代的中心。《十月》从创刊伊始便发行10万册,1981年,最高印数已达58万5千册。“那时印《十月》十趟车拉的纸都不够”张守仁回忆道,“后来在北京都印不过来了,我们不得不在成都、西安、武汉同时印刷”。作家方方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拿到《十月》的情形,“那时我读大学,忘了是写诗歌得了奖,还是写文章得了奖,反正奖品就是《十月》,当时真是很兴奋,当时像这种大型的文学刊物,《十月》是第一本,我觉得真划得来。”
而在张守仁看来,《十月》之所以能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广泛的轰动,是因为他们刊发的作品冲破了意识形态的禁区,让文学开始真正反映现实生活。1982年发表的《高山下的花环》正是如此。“我当时向李存葆约稿的时候就说,你务必要写军队内部的矛盾冲突,不要只说好话,如果你不能反映军队内部的矛盾,不能揭露军队的黑暗面,写得很肤浅的话我是肯定不发的。”
李存葆在后来做了“超水平”发挥。《高山下的花环》于全国引起的震动,至今罕见。小说在《十月》上发表后,有8家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累计印数达1100多万册,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被60多家剧团改编成话剧、歌剧、舞剧、京剧、评剧……“我收到的读者来信就有一万多封,一麻袋一麻袋的”张守仁说他编稿子的时候没有哭,但看到读者来信却哭了。“我收到佳木斯读者的来信,信里写到他们在零下二十度的天气里,围着电线杆,哈着白气,跺着脚,听喇叭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广播《高山下的花环》,我真感动!”张守仁觉得正是因为文学第一次真正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反映人民的心声,才引起读者如此共鸣。
为了约到好稿,《十月》的编辑也煞费苦心。张守仁常常会和作者彻夜长谈,“我问他们,如果明天就死了,一生中最感动的事情是什么?他们告诉我之后,我会说就写这个,别的我不要。”当代文学史上有名的作家基本都曾与《十月》有过关联,汪曾祺、丁玲、艾青、宗璞、王蒙、铁凝、张贤亮、王安忆、贾平凹……方方至今仍对其中很多作品如数家珍,“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宗璞的《三生石》、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张贤亮的《绿化树》,太多了,这些都是我们熟得不得了的作品。”
那时,张守仁经常在火车上听到人们讨论由他组稿、编辑的作品所改编的电影。听到这些,他就越发觉得自己的工作意义重大,因为它们影响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创新 现实主义中的现代文学
2009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曾对《十月》有过这样的定义:“刊物关注现实,关注读者的阅读需求,提倡审美趣味和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形成了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具有包容气度的编辑风格。”现实主义是《十月》的主要文学旨趣,但《十月》也曾刊发过不少现代派作品。
1980年《十月》发表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该小说在创作中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在西方现代派的文学资源尚未完全进入中国作家视野的时候,《蝴蝶》连同王蒙其他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新时期文学的先河。
1982年到1985年,《十月》发表了高行健的四部戏剧:《绝对信号》、《车站》、《野人》、《彼岸》,让当代先锋戏剧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车站》当年发表时曾因其内容而引起巨大争议,以致一度不能公演。为此《十月》也承受不小压力,“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冲破约定俗成的文学形态”张守仁说。
海子也是在《十月》上得以成名。1984年诗人骆一禾到《十月》工作,主持诗歌专栏。骆一禾在《十月》工作了近六年时间,他像磁铁一样吸引大批诗人给刊物投稿,也正是在骆一禾的推荐下,海子的诗作得以在《十月》上发表。1987年《十月》刊登海子的《农耕之眼(十二首)》,1989年刊登《太阳(诗剧选幕)》和《太阳(诗剧选幕·续完)》。海子在1989年3月辞世,他将遗稿全部托付给骆一禾。骆一禾为海子的丧事奔波,整理、抄写、编辑海子的遗稿,却在海子去世第49天的凌晨因脑淤血而昏倒,并在昏睡了18天之后去世。诗人陈东东曾如此形容骆一禾与海子的关系,“我把一禾看成了一个倾听者,一只为诗歌而存在的耳朵。而海子则是嗓子,海子的声音是北方的声音,原质的、急促的,火焰和钻石,黄金和泥土”。
坚守 我们还可以做出有价值的作品
《十月》的常务副主编陈东捷1991年来到杂志社工作。其时文学的热潮已经大大降低,各种媒体包括电视、报纸的普及,也让文学期刊很难再处于中心地位。张守仁说常常有人问我怎么你们那时就可以这么光彩,“我的回答是天时地利人和,是时代成全了我们,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十月》是中篇小说的主要阵营,在方方看来这正是《十月》这样的文学期刊在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用,“中国现在最好的就是中篇小说,而这和文学刊物的兴起是分不开的,中国中篇小说的繁荣就是大型文学刊物带动起来的”不过随着中国文学创作的情况发生变化,《十月》也在慢慢调整自己的定位。陈东捷说因为原创长篇小说越来越多,2004年《十月》由双月刊变为月刊,单月还是以原杂志为主,双月便推出《十月·长篇小说》,专门刊登长篇。早期《十月·长篇小说》便发表了莫言的《生死疲劳》。1999年《十月》还设立了一个新的栏目“小说新干线”。“我们希望关注那些不太有影响但有实力的青年作家”陈东捷说,目前这个栏目已经有近80多位年轻作家,他们都逐渐成为在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
虽然做出种种改变,但《十月》仍难避免文学期刊面临的普遍压力。《十月》现在的发行量保持在每月5、6万册,“所有期刊的发行量都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了,杂志发行量小了,但各种成本却都在上涨,稿酬也在上涨,经济方面一直都有一些困境”,陈东捷说。2011年《十月》获得北京市委宣传部每年100万的财政拨款,这使得他们可以把稿酬大幅提高,“可仍不乐观,其实我们还算好的,依靠发行本身可以盈利,不过一加上人员等种种成本还是比较紧张。”
即便如此,《十月》还会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前行。陈东捷说未来的《十月》会继续做文学精品,刊登既关注现实人生,又具有成熟叙事技巧的作品,“比如我们今年发表了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因为它切中了一个社会话题、一种人群的生活方式,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也许我们的影响和上世纪80年代没法比了,但我们依然可以做出有价值的作品。”
而老编辑张守仁对于《十月》的未来,则仍保有上世纪80年代那种理想主义的热情与期望,“你看那些长在石头上的松树,只有很小的空间,很少的营养,它们一样长得挺拔,所以有想法的编辑也总能找到金点子来让刊物生存下来,我觉得一个文学刊物在目前的生存状态下也还是可以活下去。”
■ 《十月》名篇
《“牛棚”小品》(三章) 丁玲 刊发于1979年第3期,真实生动地记录了丁玲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和智慧探索。
《追赶队伍的女兵们》 邓友梅 刊发于《十月》1979年第1期的中篇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女兵》。
《公开的情书》 靳凡 1980年第1期
《晚霞消失的时候》 礼平 刊发于《十月》1981年第1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手抄本小说”之一,作品以其浓重的思辨色彩与对人生价值的探索性,而在当时引起强烈争论。
《爬满青藤的木屋》 古华 刊发于《十月》1979年第2期,改编成电影《爬满青藤的木屋》。
《鬈毛》 陈建功 1986年第3期
《小镇上的将军》 陈世旭 刊发于《十月》1986年第3期的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荣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南方的岸》 孔捷生 刊发于《十月》1982年第2期中篇《南方的岸》,和《十月》刊发的孔捷生另一重要中篇小说《大林莽》,风格厚重,内涵丰富,在当代文坛有重要影响。
《绝对信号》 高行健 刘会远 1982年第5期
《北京人在纽约》 曹桂林(美) 刊发于《十月》1991年第4期的中篇小说《北京人在纽约》,经冯小刚、郑晓龙执导改编成电视剧,由姜文和王姬主演,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美国热”。电视剧荣获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第十四届“飞天奖”、第十二届大众电视“金鹰奖”。
《巴山夜雨》 叶楠 刊发于《十月》1979年第4期的剧本《巴山夜雨》被改编成电影,1981年第一届金鸡奖获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女配角奖、最佳编剧奖等奖项。
《张铁匠的罗曼史》 张一弓 刊发于《十月》1982年第1期中篇小说,是著名作家张一弓中篇力作,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被改编成电影。
《向上的台阶》 周大新 刊发于《十月》1994年第1期的中篇小说《向上的台阶》,是著名作家周大新代表性作品。
《大平原》 高建群 刊发于《十月·长篇小说》2009年第1期长篇小说,是《最后一个匈奴》作者高建群另一力作,2012年荣获“五个一”工程奖。
《天下第一楼》 何冀平 刊发于《十月》1988年第3期的话剧剧本《天下第一楼》,被认为是继《茶馆》之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的代表作,演出超过400场,并场场爆满,成为“人艺”的保留剧目。
《天行者》 刘醒龙 刊发于《十月·长篇小说》2009年第4期的长篇小说,是著名作家刘醒龙至今最重要的作品,2011年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空镜子》 万方 刊发于《十月》2000年第1期的中篇小说《空镜子》,改编成同名电视剧,自2002年起热播荧屏数年,好评如潮。
《开拓者》 蒋子龙 刊发于《十月》1980年第6期的中篇小说《开拓者》,在著名作家蒋子龙的工业改革题材的小说中占有显著地位,1981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高山下的花环》 李存葆 1982年第6期
《黑骏马》 张承志 1982年第6期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铁凝 1983年第2期
《永远有多远》 铁凝 1999年第1期
《花园街五号》 李国文 1983年第4期
《来来往往》 池莉 1997年第4期
《生活秀》 池莉 2000年第5期
《狼毒花》 权延赤 1990年第3期
《锄奸》 石钟山 2007年《十月·长篇小说》第4卷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张洁 1994年第1期
《神木》 刘庆邦 2000年第3期
采写/新京报记者 江楠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