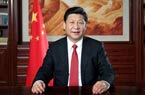|
|
圖為《韓熙載夜宴圖》(局部)。 |
聞弦歌而知雅意。
與詩三百、楚辭、古詩十九首、南北朝樂府詩以至唐詩宋詞元曲等古典文學華彩篇章一脈相承的,是中國文人歌詠綿延千年的藝術格調和審美情趣。文人之歌詠唱和,蘊藉著別具一格的中國文脈與文化精神。這種傳承在“五四”時期,在與西方文化、西方音樂的碰撞交融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今天的我們,當以何種方式實現中國文人歌詠的現代轉型?
(一)
我享受過一次真正的中國“好聲音”,是在維也納音樂之友協會大樓內的“勃拉姆斯音樂廳”。男高音歌唱家范競馬全球首演“中國雅歌”(Chinese YAGE)室內聲樂音樂會,上半場是中國當代“藝術歌曲”,即趙元任、黃自、蕭友梅、劉雪庵、廖尚果等人在20世紀上半葉創作的“文人”歌曲﹔下半場在中國作品《良宵》和《二泉映月》之外,范競馬和女高音歌唱家李晶晶演唱了德國民歌二首及舒伯特的藝術歌曲《極樂》與《鱒魚》。即便在挑剔的維也納觀眾眼中,這也是一台品位高雅又氣氛輕鬆的音樂會。
雅歌(YAGE),是范競馬為中國藝術歌曲起的“洋名”,此“雅歌”之“雅”乃上溯至“詩三百”“風雅頌”之“雅”。“雅歌”所代表的是中國文人或知識分子綿延千年的藝術格調和審美情趣。從“詩三百”到楚辭,從古詩十九首到南北朝樂府詩以及唐詩宋詞元曲等皆為中國文人雅士的擅長,它們無不與音樂形影不離甚或水乳交融,即所謂詩詞琴曲皆為一體。此文人之歌詠唱和,是為“聞弦歌而知雅意”之“雅歌”,然其以何樣聲音唱出、以怎樣的方式傳播,如遺珠散落,湮不可考。
綿延兩千多年的中國文人雅趣,在上個世紀初葉的中國,機緣巧合地披上西洋樂歌的外衣。自晚清開始的西學東漸至民國年間既成氣候,一大批專攻語言及音樂的知識分子(他們亦是現代中國音樂的先行者)於西方學成歸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他們身上的表現,便是以漢語入詞、以西方調式配歌,其佼佼者及代表人物有趙元任、黃自、蕭友梅、廖尚果等。為他們作詞的往往是易韋齋、韋瀚章、龍榆生、劉天華、劉雪庵、徐志摩、潘孑農、周無若這樣的詩詞大家。其歌與詞所凝聚洋溢的真情實感及風雅趣味,一反傳統的工整精巧而變得自由奔放,特別是在樂思上豐沛寫意、不拘一格,其膾炙人口者如“叫我如何不想她”“聽雨”“思鄉”“紅豆詞”“玫瑰三願”“踏雪尋梅”“花非花”“相思曲”“海韻”等。它們或譜寫於書齋、首唱於沙龍,或起意於即興、聞播於唱和,其歌樂形態既不同於古曲新調,亦有別於民歌俗曲。它們是新時代的產物,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它們雖披著“洋歌”的外衣,卻自內向外散發著文人的雅趣——既感時傷懷,又積極奮進,有愛的致意、愛的表達,還不失含蓄比興、幽默風趣。它們於民國年間流行一時,最近幾年在大陸樂壇亦頗有復興之勢,先后有優秀聲樂家開過專場音樂會。2012年,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辦“紀念趙元任誕辰120周年”音樂會,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思考引入音樂創作,推動了對中國文人歌詠獨特唱法的探尋。且不說那個時代,國學大師趙元任等發乎性情、直抒胸臆譜寫的數百首歌曲其實大多已經湮沒,那些在華人世界廣為傳唱的“歷史歌曲”,又有幾人能夠認識其歷史價值和學術內蘊,以及渴望融入西洋主流聲樂體系的“偉大雄心”?
(二)
在中國聲樂領域開創“中國雅歌”的事業,便是源於一個全新的藝術命題——建立一種以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為基礎、能與西方音樂藝術融通與對話、兼具原創性和深度表現力的中國歌唱藝術。這是在對中國文人歌詠歷史傳承基礎上,再一次現代轉型。
在這一次的發現、傳承、轉型、實驗中,作曲家鄒野為“中國雅歌”的配樂尤其值得稱道。他力圖接近德奧19世紀晚期的風格,體現作為歌曲伴奏的音樂交響性、對應性和技術含量,凸顯了趙元任、蕭友梅、黃自等所追求的“洋味兒”。在維也納、林茨、巴德伊舍爾和布拉迪斯拉法的音樂廳,當“雅歌”與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或者德奧民歌出現在同一場音樂會時,它帶給異國聽眾的突出印象便是一個同等境界、同等水平和同等品味,但又來自不同地域與民族的“藝術歌曲”的集聚。在這樣的集聚中,語言獲得了最高級別的尊重,它被成熟的音樂規范了發音。詩,成就了音樂﹔音樂,賦予詩聲韻的穿透力。漢語,在音樂中顯現了它的美妙、它的音韻的魅力。
“雅歌”希望能夠做到德國20世紀偉大的男中音歌唱家迪特裡希·菲舍—迪斯考那樣,通過考究的語言和詩意的吟唱,提升到熔高貴語言和典雅歌唱於一爐的圓融境界。這種訴求,既是對詩歌和精神深處理性的探索,也是一種現代心靈的詩意表達。
每個中國人或者具有一定漢語基礎的人都可以輕鬆學唱“中國雅歌”。范競馬與合作者研究並確立一種近乎標准化的演唱方法,它既不同於西洋“美聲”,又有別於“通俗”或“民歌”,它不以追求歌唱的技巧和難度為目的,尤重於詞與音在對應精准的前提下達到唯美的和諧。通過文人內在世界和返朴歸真的詠唱,在詩性的歌唱中,把對漢語的審美提升到音樂美學的高度。在服從漢語的語音規則與特性的前提下,以科學、統一、規范的發聲方法為支撐,把中國歌唱藝術以既高貴又通俗、既考究又自然的形態呈現於音樂舞台,希求超越東西方“詩”與“歌”的審美差異與偏見,取得精神境界層面的和諧統一。
器樂部分,是“中國雅歌”一個極為顯著的特征。除了鄒野的精湛配器,中國愛樂樂團的鋼琴與弦樂五重奏組呈現了高水平的室內樂之聲,完美而自然地連接了“玫瑰三願”和“鱒魚”之間的美聲意境。在這種高品質聲音的鋪陳及唱和中,“雅歌”藝術得到富有情懷和意蘊的發揮。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劉東教授聲情並茂地朗誦徐志摩的敘事詩《海韻》之后,趙元任譜寫的謠唱曲將故事的敘述層層深入,飽滿的情感跌宕起伏,營造出動人心魄的戲劇效果。此刻,恍如置身19世紀末維也納的藝術沙龍,聆賞配器大師馬克斯·裡格爾為舒伯特藝術歌曲而改編的樂隊伴奏。
(三)
在奧地利和斯洛伐克的每一場“中國雅歌”音樂會之后,我聽到最多的聽眾評價便是——這些來自中國的歌曲非常熟悉,它們和舒伯特、勃拉姆斯一樣美,是能夠聽得懂的音樂。甚至有一位音樂學院的教授疑惑地問我:你確定這些歌曲都是中國人在幾十年前譜寫的?它們太令人感動了!
中國人演唱中國人創作的歌,竟然令舒伯特和勃拉姆斯的聽眾產生如此強烈的認同感。是不是可以說,近百年前中國歌曲的世界之夢,如今可通過“中國雅歌”而抵達夢圓之時?
在當下全球化的時代,以相同的層面與高度,尋找具有國際審美尺度的藝術實體和表達方式,既可以含蓄而真實地體現中華民族內心深處高貴而驕傲的文化品位,又能自然地被世界所容納所接受。這是“雅歌”誕生的願望基礎,也是中國傳統歌樂在全新背景下“走出去”的有益嘗試。
我們深知,“中國雅歌”發展之路仍很漫長,曲目的積累、歌詞的選擢、表現形式的豐富多樣性、規律的探尋、標准的確立、傳播的廣度與深度,這些需要更多音樂人的參與,需要聲樂家和器樂家的身體力行。當我在2013年底的一場“雅歌”音樂會上,聽到年逾七旬的作曲家高為杰為三首元曲譜寫的“雅歌”,聽到抒情花腔女高音張怡以款款深情唱出“玫瑰三願”和“春思曲”時,我看到了“中國雅歌”在這片土地上的萌芽。
“雅歌”,作為連接中國歌唱藝術傳統與現代的紐帶,既代表了高速發展的中國所需的精神高度和藝術情懷,又承續傳統文化在新時期的新狀貌新內容。它是真正的“中國好聲音”,是中國的歌聲,也必然是世界的歌聲。
《 人民日報 》( 2014年01月09日 24 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