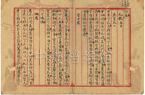原標題:少些功利心,別讓遺產成遺憾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華代表辛格 李謐歐 攝
近日,有著“中國第五大發明”之稱的珠算,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了最新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至此,我國已成為全世界擁有世界級“非遺”最多的國家。
在我們為之歡呼雀躍、文化自豪感隨之升騰的時候,也需冷靜思考:“申遺”的目的究竟是什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華代表處代表辛格先生在接受《解放周末》獨家專訪時說,“發自內心的尊重和切實的保護,比獲得‘非遺’這個稱號更重要。”
雖然被命名為 “遺產”,但並不意味著那都是些“將死”或“已死”的東西
■我們希望人們對“非遺”的關注能夠更為持久,不能看完奧斯卡頒獎,大家就再也不進電影院了。
■無論全球化的趨勢如何蔓延,每個人身上都留著先人傳遞下來的文化烙印,這是丟不掉、也不能丟的。
解放周末:上周,中國珠算“申遺”成功,人們的“非遺”熱情又被點燃了,但不知道您注意到沒有,這種對“非遺”的關注,似乎總像一陣風?
辛格:在公布“申遺”結果的前后一段時間,確實會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我覺得這是好事。就像奧斯卡搞頒獎典禮一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每兩年舉辦一次這樣的評選,就是想喚起人們對“非遺”更加持續的關注,激發人們對“非遺”的熱情。當然,我們希望人們對“非遺”的關注能夠更為持久,不能看完奧斯卡頒獎,大家就再也不進電影院了,那肯定不行。
解放周末:對普通人來說,一提到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會很自然地聯想到一些已經逝去的文化。
辛格:非物質文化遺產雖然被命名為“遺產”,但並不意味著那都是些“將死”或“已死”的東西。相反,它們是人類的根,一個民族的文化與生活都是從那裡走出來的。無論全球化的趨勢如何蔓延,每個人身上都留著先人傳遞下來的文化烙印,這是丟不掉、也不能丟的。
解放周末:即使丟不掉、不能丟,但也有人總會把“非遺”和“老古董”聯系在一起,覺得這些東西離人們的生活太遙遠了,甚至是個負擔。您怎麼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對於當下生活的意義?
辛格:“非遺”確實是老的、舊的東西,但它們是時間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是人類進化過程中留下的最精彩的標記和符號,這些成果不只是藝術方面的,它們往往還見証著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發展路徑。對於現代人來說,這些歷史的饋贈仍然具有現實的啟發意義,仍然產生著持續的影響。
解放周末:您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華代表已經5年了,在這5年裡,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給您留下了怎樣的印象?
辛格:說說我所熟悉的昆曲和古琴吧,這兩項非物質文化遺產讓我印象最為深刻。我第一次看昆曲表演的時候感到非常震撼,舞台上演員們精致的妝容、奇特的服飾,深深地吸引了我。我雖然是印度人,中文不太好,但這並不妨礙我喜愛這門藝術,我甚至產生了了解她的歷史的興趣。昆曲在中國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在上海、蘇州、南京等城市,以及在北方的一些地方,演變出多種風格流派,她承載著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和文化內涵,非常厚重、靈動、豐富,我把她看成是了解中國文化的一把鑰匙。
解放周末:文化遺產是可以超越國界、跨越語言鴻溝的,您即使不能完全聽明白,但也不妨礙您感受她的獨特魅力。
辛格:這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魅力所在,那就是讓全人類共享。
我還喜歡中國的古琴。每當聽到她流淌出來的旋律,我都會心醉。古琴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曾經扮演過很重要的角色,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她的了解越來越少了,但我很高興地看到,現在有不少人正在重新找回對她的興趣,特別是一些年輕人不僅欣賞,還在認真學習彈奏古琴。相信在琴聲中,他們能夠捕獲到傳統文化傳遞給他們的訊息,也能夠在這種文化的滋養中獲取力量。
發自內心地認同本民族的文化,為這種獨特文化的存在而自豪,這是“非遺”生存的土壤和空氣
■讓“非遺”活在當下,關鍵是讓她成為我們的一種生活方式。
■要增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自豪感,應該給予他們認同。
解放周末:您認為怎樣才能讓古老的“非遺”活在當下?
辛格:讓“非遺”活在當下,關鍵是讓她成為我們的一種生活方式,讓我們能夠不斷使用她、發展她、完善她。
這點我自己就很有體會。比如中醫中藥,我吃過中藥,還嘗試過拔火罐、扎針灸。我還建議我的家人進行針灸治療,效果很好。我記得自己第一次體驗針灸的時候,非常放鬆,還睡著了。醒來之后,醫生告訴我,他很驚訝一個外國人第一次做針灸竟然能夠這麼放鬆,而且還打呼呢。(笑)我還向我的印度朋友們極力推薦過針灸。
解放周末:結果如何?
辛格:在他們看來,要把二三十根針插進自己的身體裡,包括后背、腦袋和嘴巴,“實在太痛苦、太令人恐懼了”。雖然我努力向他們解釋,這是一種很細的針,隻要醫生的技術好,就不會有任何疼痛的感覺,而且這些針不會向人的身體裡注射任何藥物,但是要讓他們建立對這種治療的信任,確實需要點時間。
解放周末:謝謝您對中國“非遺”的推廣。
辛格:我在中國工作的這幾年裡,中國被世界認可的“非遺”數量顯著增加,我很高興。作為教科文組織駐華代表,我很樂於把在中國接觸到的文化習俗和藝術成就,把這些交集和體驗,告訴給更多人。
這些年,我們也很欣喜地看到中國一些地區的中小學做了很好的探索,他們將民歌、民樂納入音樂課,將剪紙、年畫納入美術課,將傳統技藝納入手工課,讓那些仍具有生命力的“非遺”逐漸融入到人們的生活中去。
解放周末:融入生活,能夠讓非物質文化遺產“活”起來,那麼怎麼才能讓它們更具有持續的生命力呢?
辛格:首先要增強一種文化認同感。人們應當發自內心地認同本民族的文化,為這種獨特文化的存在而自豪,這是“非遺”在新時代生存發展的土壤和空氣。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致力於呼吁年輕一代增強對自己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並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把更多的時間、資源投入到對文化的回饋、復興和推廣中。
除此之外,還要增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自豪感,應該給予他們認同,讓他們認識到自己所從事的“非遺”工作是非常有價值的。
如果把所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束之高閣、藏於深閨,那他們就無法順應時代的變化,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非遺”是活著的文化,怎麼能用固化思維來保護呢?
■不能為創新而創新,丟了靈魂可不行。
解放周末:有些人認為“非遺”既然是遺產,那保護“非遺”就應該小心翼翼,把它們供在博物館裡、罩在玻璃蓋子下。對於這種做法,您怎麼看?
辛格:對於某些有形的物質文化遺產,應當提倡博物館式的保護,講求原封不動、修舊如舊﹔但無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存在於特定人群中、仍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傳統,保護的最終目的是促進它的傳承和發展,而不是擺在博物館裡供人觀賞。
比如人們都熟悉的剪紙藝術,它之所以被世界認可,不僅僅是因為它最終剪出來的那些美麗圖案,而是整個剪紙的過程,包括它的創意、藝術家靈活的刀法以及圖案背后傳遞的文化內涵。如果只是把剪紙完好地擺在博物館裡展示,那樣根本不可能促進這門技藝的發展和傳承。
解放周末:保護的目的不只是讓遺產留下來,更重要的是傳下去。
辛格:對,“非遺”是活著的文化,怎麼能用固化思維來保護呢?
就像昆曲,在昆曲誕生之初,當時的中國沒有很多的娛樂方式,聽戲就是許多人最大的樂子,所以一出戲常常要唱上好幾天。經過幾百年的發展,昆曲在不同的地方衍生出了不同的流派,唱的時間也越來越短了,現在人們看一場昆曲一般隻要3個小時左右,這就是昆曲隨著人們的生活自然進化的結果。如果把所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束之高閣、藏於深閨,那它們就無法順應時代的變化,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解放周末:作為保護者要做的,就是為“非遺”的延續和發展提供支持和保障,讓這些遺產自然地進化,自然地傳承。
辛格:說得對。我留意到中國現在有不少民間力量在進行古建筑的保護,他們在修復古建筑的基礎上又把它們開發成展館或者畫廊,而不僅僅作為一處文化遺跡供人參觀。我覺得,賦予這些古老建筑以新的生存方式,就是讓它們活起來的好方法,這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一種好思路。
解放周末:中國作家莫言不久前提出了這樣一種觀點,他認為,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既要保護,更要大膽創新。對此,您怎麼看?
辛格:我主張在一定程度上進行創新,這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適應時代變化的需要,但創新必須是在繼承傳統的前提下進行的。不能為創新而創新,丟了靈魂可不行。
解放周末:剛才您廓清了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上的誤區,那麼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能為保護“非遺”做點什麼呢?
辛格: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關注,絕不僅僅是聯合國的事、政府的事、傳承者個人的事,更是全社會都可以參與其中的。每個人都可以發揮自己的作用,比如聽一場昆曲,學一學剪紙,甚至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去定制一套手工服裝,這也是對這種傳統技藝的支持。
在對待文化遺產的問題上,應該消除功利心
■發自內心的尊重和切實的保護,比獲得“非遺”這個稱號更重要。
■假如把“非遺”的招牌當作吸金的法寶、賺錢的工具,把“申遺”當成買賣,那就是在禍害、糟蹋這些遺產。
解放周末: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華代表,您怎麼評價中國這些年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面所做的工作?
辛格:十年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國是最早加入這一公約的國家之一。這些年來,中國建立起了一個從地方到國家,再到世界的“非遺”申報、管理系統。無論在“非遺”的數量上還是保護的質量上,都發展得很快。
解放周末:現在中國成為了擁有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最多的國家,但在“申遺”的過程中,一些地方也存在一定的認識誤區。比如,有的人覺得“申遺”比保護“非遺”更重要。
辛格: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注不能隻停留在“申遺”上,不能成功了就不管了,不成功就不理了。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期把最需要保護的遺產列入名錄,但並不意味著那些暫時沒有被列入名錄的候選項目就不珍貴,就沒有保護和傳承的價值。
許多人或許不知道,貴州從江縣的苗寨裡,至今傳承著一種非常古老的斗牛活動,這種斗牛既不暴力,也不血腥,而是當地獨特的祭祀文化的一部分﹔但是隨著高速公路的修建,那個村子的面積正在縮小,斗牛的傳統也瀕臨消亡。我們在做“文化地圖”這個項目的過程中,發現了這一獨特的文化,並且通過很多渠道幫助他們。現在,每年有超過兩萬名的游客會到那個寨子去參觀他們的斗牛表演,這一文化傳統就活下來了。雖然它沒有被官方認定為任何一個級別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但這樣的保護也是有意義的。
解放周末:重要的是保護的行動,而不是“非遺”稱號的獲取。
辛格:對,在對待文化遺產的問題上,應該少些功利心。“非遺”對於我們的意義絕不僅僅是擁有一個稱號,更重要的是如何運用這份令人驕傲的文化財富,為人類的生活增添魅力和價值。所以,發自內心的尊重和切實的保護,比獲得“非遺”稱號更重要。申報的項目再多、申報的級別再高,如果不以一顆珍視之心去對待那些遺產,就失去了申報的意義。
解放周末:這種功利心還表現在有些地方把成功“申遺”視作一種政績。
辛格:我也留意到了這種心態,比如有些地方的“非遺”項目得到了省一級的認可,而別人的項目得到了國家一級的認可,那這個地方就要千方百計地投入財力、物力、人力,爭取得到更高級別的認可。“申遺”本身是公益性的,目的也應該單純一些,不該變成一項政績指標。
解放周末:政績指標的背后,往往也是錢在作祟。
辛格:確實,由於追逐經濟利益導致過度開發的現象,已經出現在一些世界自然遺產的保護過程中。大多數世界自然遺產都是人們熱衷游覽的景點,這些遺產確實需要經營,但經營的最終目的並不是賺錢,而是運用這些資金更好地對遺產進行維護和保護。為了謀取經濟利益而過度開發甚至破壞遺產的現象是所有人都不願意看到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也是如此,假如把“非遺”的招牌當作吸金的法寶、賺錢的工具,把“申遺”當成買賣,那就是在禍害、糟蹋這些遺產。

(來源:解放日報)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