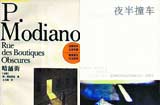書市上,諾貝爾文學獎的熱潮慢慢發酵,這位來自法國的新主帕特裡克·莫迪亞諾,讓存在主義再次受到大眾的關注。
熒屏上,七大最佳男主角合作的電視劇《北平無戰事》正在熱播,柏林影帝廖凡一臉深沉地念著台詞:“既然我選擇了不能再選擇,就不可能再有別的選擇。”擊中文藝范的心。
其實這都和一個人有關,他存在很多人的心底。
1964年拒領諾獎的讓·保羅·薩特,即將“來”杭。這是身處江南的你,距離他最近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劇贊·國家話劇院2014杭州演出季”第一出大戲,就是話劇界的神劇——《死無葬身之地》,10月24日、25日登陸杭州劇院,這是大神薩特的戲劇首次亮相杭州。
要說說薩特的故事
不能不說波伏娃
薩特和其他板起臉說大道理的哲學家不同的是,他不但會板起臉寫哲學著作,也會很有親和力地寫小說和戲劇,更重要的是,他寫的故事都很好看。
這當然和他的經歷有關。
1905年,薩特出生於巴黎,他是標准的“富二代”,但卻不是“高帥富”,因為他的右眼從小就斜視,個子還很矮,這讓他顯得有點“丑”。他的那些流傳於世的肖像照都用厚厚的眼鏡和巧妙的角度來修飾,他也可以說是美顏界的鼻祖。
薩特父親在他1歲的時候就過世了,母親帶他回娘家,投奔做德文教師的外祖父。薩特在書香門第的外祖父家裡接受良好的教育。據說,他看的第一本書是《一個中國人在中國的苦難》。
薩特的傲嬌估計遺傳了外祖父的基因。外祖父把他送到蒙田公立學校,要求校長直接給天才的外孫上8年級,但是校方很快以薩特“基礎太差”為理由,要求他從1年級開始學。外祖父竟然一怒之下讓孩子退學,請了家庭教師在家裡上課。
薩特的確是學霸,而且情商也極高,他在大學期間遇到了后來的“終生情侶”西蒙娜·德·波伏娃。
薩特和波伏娃之間的感情可以寫成一本傳世小說。他們在世界舞台上出雙入對,還曾經一起到過中國,上過天安門城樓。光是那女高男矮的形象就足以引起圍觀。
而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們相守半生,卻一直沒結婚,並且開創出一個著名的短語:契約式愛情——精確詮釋“婚姻只是一張廢紙”。
薩特喜歡對西蒙娜說:“我們的結合是一種本質上的愛。”這句話意味著,他們都可以體驗偶然的風流韻事。
薩特的名言
經常上微博當“心靈雞湯”
薩特是典型的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二戰爆發以后,他應征入伍,很快於1940年被俘。他在德國的戰俘營裡研讀海德格爾,然后,他以眼睛有疾病不能打仗為由,使德軍軍官相信他不是士兵而逃出戰俘營。
戰爭期間是薩特創作的黃金期,他不但寫出了存在主義哲學的專著《存在與虛無》,還有大量文學作品問世。這其中最著名的要屬獨幕劇《隔離審訊》,整部劇隻有三個演員,每個人都需要其中另一個人,而每一個人又都妨礙另外兩個人彼此依靠,最后終於沒有任何一個人達到自己的願望——是不是很拗口很混亂,很殘酷卻又讓人很好奇想看?那就是他的特色。
這部劇的結尾讓人難以忘懷,“我萬萬沒有想到,你們的印象中,地獄裡應該有硫磺,有熊熊的火堆,有用來烙人的鐵條。啊!真是天大的笑話!用不著鐵條,他人就是地獄!”
“他人就是地獄”成為薩特最著名的名言。
戰爭也讓薩特改變了對文學的態度。他的口號是:我們必須為我們的時代而寫作!他把這種態度稱之為“介入”,他認為作家須通過作品對當代社會、政治事件表態,從而保衛日常生活中的自由。
正是這樣的態度,讓他的文學作品擁有深入人心的力量。作為一個杰出的文學家,薩特1964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但他卻拒領了,理由是“不接受來自官方的任何榮譽”。
薩特被諸多人惦記,就是因為他堅持維護自己的獨立人格與自由精神——一切是非善惡都可以由人自己選擇。但也因為絕對自由,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在現實世界中,人們感到焦慮,恰恰是因為有選擇的自由。用流行的話講,這是“選擇恐懼症”。例如大三學生要面臨考研還是就業的選擇,有人面臨移民還是繼續留在國內發展的選擇,這些抉擇沒有任何因素可以依靠,隻能靠自己,於是就產生了“焦慮”。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自由時代,薩特所倡導的“自由選擇”在生活裡已經蔚然成風。許多人奉行這個原則,並不是因為看過薩特的書。
就像王朔說的,“以前我不知道薩特、尼採什麼的,后來我看了, 才發現他們說的我都已經知道了。”
(來源:錢江晚報)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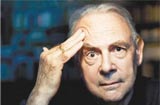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