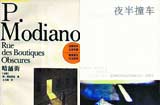小仲馬

電影、歌劇、小說……不同形式的《茶花女》風靡於世。
提起《茶花女》,不少人想到其同名小說、話劇,甚至會哼唱起同名歌劇裡那首著名的《飲酒歌》。然而,這不僅是一部被改編為多種題材的文學名著,更是開啟了中國現代話劇之門的鑰匙,也是中國文藝吸收外國文藝精華、滋養自身的見証。
今年,是《茶花女》作者、法國著名作家小仲馬誕辰190周年。盡管時光流逝,但浸染著歲月之光的《茶花女》,卻歷久彌新,芬芳依舊……
“讓我們高舉起歡樂的酒杯,杯中的美酒使人心醉。這樣歡樂的時刻雖然美好,但誠摯的愛情更寶貴。”
當《飲酒歌》的旋律響起,帶來的是歡樂與陶醉。這首人們耳熟能詳的名曲,就是來自歌劇《茶花女》。問世以來,它被翻譯成數種語言,流傳於世,至今仍是人們最樂於演繹的經典藝術作品之一。
“這是中國人最熟悉的一部西洋歌劇,很多中國歌唱家就是通過《茶花女》走上歌劇道路,把歌劇作為摯愛一生的事業的。”今年4月,國家大劇院推出了“老帶新”版本的歌劇《茶花女》,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劇中女主角薇奧萊塔的扮演者張立萍如是說。而這,已是國家大劇院版歌劇《茶花女》迎來5年內的第3輪演出了。
但《茶花女》獻給世人的,卻遠不止歡樂與陶醉——小說《茶花女》脫胎於小仲馬的親身經歷,描寫了一段真摯、曲折而淒婉的愛情,1848年出版后,便成為轟動一時的名作。
歌劇《茶花女》問世時,小仲馬曾表示,即使自己的小說被忘記,歌劇也將永垂不朽。但令他沒有想到的是,漂洋過海的《茶花女》,在大洋彼岸的中國土地上,開出了更加絢爛的花朵。
以情動人的暢銷書
“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浪子魂”
小說《茶花女》與中國的邂逅,像極了一場淒美的偶遇。
1897年的暮春三月,晚清著名翻譯家林紓喪偶,整日郁郁寡歡。為了排解愁緒,他接受朋友王壽昌的提議,開始翻譯《茶花女》。機緣巧合之下,《茶花女》成為了最早被譯介到中國的外國小說之一。
兩年后,《茶花女》被譯作《巴黎茶花女遺事》出版,其膾炙人口的故事一時之間風靡街頭巷尾,人們紛紛爭相購買。在這些狂熱的“粉絲”當中,甚至還包括了魯迅和周作人!魯迅在南京求學時就購買了《巴黎茶花女遺事》,周作人在《魯迅的青年時代》一文中回憶得更加細致:“我們對於林譯小說那麼的熱心,隻要他印出一部來,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國書林把它買來﹔看過之后,魯迅還拿到訂書店去改裝硬紙版封面。”
除了周家兄弟外,作家葉靈鳳也是林譯《茶花女》的忠實讀者。由於反復閱讀《巴黎茶花女遺事》,他已經有些“入戲”,常常感到自己“擠在人群中也仿佛是小說中的阿蒙(即今譯《茶花女》中的阿芒)”,可見小說的魅力之深。
《巴黎茶花女遺事》的暢銷,出乎林紓意料。但當時的讀者們為之傾倒,已是不爭的事實。晚清思想家嚴復有詩雲:“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浪子魂。”道盡了《巴黎茶花女遺事》暢銷大江南北的情狀。
中國現代話劇的起點
“這一回的表演可說是中國人演話劇最初的一次”
如果說小說《茶花女》掀起了翻譯外國小說在中國最初的熱潮,那麼由中國最早的話劇團體春柳社所演繹的話劇《茶花女》,則為中國現代話劇史寫下了濃墨重彩的第一筆。
有趣的是,話劇《茶花女》的誕生,延續了小說翻譯的偶然意味——那本來是一場為江蘇水災賑災募捐而舉行的演出,排練時間隻用了20多天。
1907年早春的一天,日本東京中華基督教青年禮堂裡座無虛席,一場旨在賑災募捐的游藝會上,春柳社演繹的話劇《茶花女》正在初試鋒芒。台上,在一間布置精美的房間裡,一位披著卷發、身穿洋裝、身材纖細的白衣美人正忍痛與愛人告別。台下,2000多名來自中國、日本、歐美等國的觀眾屏息觀看,時而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
后來,上海的報紙這樣形容這次演出:“此誠學界中僅有之盛會,且亦吾輩向未經見之事也。”而那位讓觀眾們深深著迷的白衣美人,正是由著名藝術家李叔同(即弘一大師)扮演的茶花女。他的演出,被日本評論家鬆居鬆翁譽為“優美、婉麗,絕非本國的演員所能比擬。”他還稱贊此舉“在中國放了新劇的烽火”。
誠然,話劇《茶花女》的成功,離不開小說在中國暢銷10年的基礎。但更令人激動的是,這次演出改變了中國傳統戲曲以歌唱為主、抽象的舞台背景的演出樣式,它以對白和動作為主要表現形式,還原真實的舞台藝術,促成了中國現代話劇的誕生。春柳社最早的成員之一、著名戲劇藝術家歐陽予倩認為,“這一回的表演可說是中國人演話劇最初的一次”。
深刻影響中國文藝
文化土壤中綻放出他鄉之花
嚴格說來,《茶花女》其實是一部有些離經叛道的作品——它是法國文學史上,第一部以妓女作為主角的文學作品,卻也是世界文學史上,對尊嚴和愛情描寫最為深刻和動人的作品之一。有研究者認為,《茶花女》中,對妓女瑪格麗特的塑造,跳出了以身份論人的窠臼,充分凸顯了人性的高貴。而這一點,迅速地被中國文學所吸收,化為自身的養分。
回顧中國現代文學史,不難發現,女作家廬隱在1930年問世的兩部長篇小說《歸雁》和《象牙戒指》中女主人公身上都融有茶花女瑪格麗特的影子。直到20世紀40年代,茶花女的這種魅力還時常浮現在小說中,如端木蕻良的《新都花絮》。
不僅在文學創作上,在藝術舞台上,著名劇作家曹禺的名作《日出》,也被認為深受《茶花女》影響。《日出》主角陳白露與《茶花女》中的瑪格麗特不無相似之處。前者深刻地譴責了20世紀30年代“損不足以補有余”的黑暗的社會現實。
對此,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崗在接受本報記者電話採訪時認為,自晚清以來,西方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既形成了沖擊,也產生了推進,如魯迅的《狂人日記》等白話小說、“五四”時期誕生的白話新詩等,都是受西方文藝思潮影響而產生的。
時至今日,這種影響更多地體現在融合與創新上。對此, “三度梅”得主、重慶市川劇院院長沈鐵梅體會深刻。
沈鐵梅告訴記者,有人說在川劇裡採用以《茶花女》為代表的西洋歌劇的配樂、舞美、化妝等元素,會讓川劇“走味兒”。
“其實不然!這種東西方文藝的融合,實際上是用西方藝術的語言,把中國傳統藝術介紹給全世界的觀眾。但作品的精髓和靈魂,還是地地道道的中國味。東西方藝術各自發揮所長,讓作品跨越語言和文化的門檻,才能真正實現‘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事實亦如此。近年來,沈鐵梅將西方的交響樂和歌劇元素引入川劇表演,打造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李亞仙》、《鳳儀亭》等川劇劇目,在歐美等地大受歡迎。
“這是正在蓬勃生長的中國文藝,對外國文藝精髓的吸收與化用。”西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王本朝表示,中華民族是一個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文藝的發展受到了外國文藝的極大影響,期間的不斷學習、融合與創新,為我們的文藝百花園提供了大量養分。
或許,這就是以《茶花女》為代表的一大批優秀的西方經典能夠扎根在中國的文化土壤裡,綻放出絢爛的花朵的原因吧。
《茶花女》有哪些版本
小說《茶花女》由法國作家小仲馬創作,出版於1848年,講述了法國鄉下姑娘瑪格麗特令人同情的一生。她還是個少女時便來到巴黎賣笑,后來成為貴族們追逐的交際花。因為喜愛白色茶花,人稱“茶花女”。她遇到真摯的青年阿芒·杜瓦后,二人產生愛情,卻終因為阿芒的父親阻撓和種種誤會,不得不分離。
歌劇《茶花女》首演於1853年,由意大利歌劇大師威爾第創作,一共三幕,是世界上演出次數最多的歌劇之一。譯林出版社版本的小說《茶花女》譯者鄭克魯在該書序中指出:“《茶花女》從小說到劇本再到歌劇,三者都有不朽的藝術價值,這恐怕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文藝現象。”
另外,《茶花女》還數度被改編為電影,其中以1936年美國米高梅公司拍攝、葛麗泰·嘉寶主演的版本最為著名,而2001年上映的歌舞電影大作《紅磨坊》中的愛情故事也來源於《茶花女》。
1978年,德國漢堡芭蕾舞團把《茶花女》搬上了芭蕾舞的舞台。芭蕾舞劇《茶花女》由舞團藝術總監約翰·諾伊梅爾操刀改編,被稱為“戲劇芭蕾”的經典之作。2010年,芭蕾舞劇《茶花女》舞進了國家大劇院,讓中國觀眾大飽眼福。
(本報記者 申曉佳 實習生 李海嵐 整理)
《茶花女》趣事一二
著名作家王蒙的名字來自於《茶花女》
當代著名作家王蒙的夫人方蕤在《我的先生王蒙》一書中提到,王蒙的名字是著名詩人、文學評論家何其芳起的。何其芳是王蒙父親王錦第的北大同學,王蒙出生時,何其芳正在研究法國文學,便建議以《茶花女》中男主人公的名字“阿蒙”(阿芒的另一種譯法)為他命名。王錦第大為稱贊,但“阿”字叫起來不順口,便簡化為單名“蒙”。王蒙在自傳《半生多事》中也提到了這件趣事。
在沙漠上唱《茶花女》
歌劇《茶花女》自問世以來,曾唱響眾多歌劇藝術殿堂。然而,今年6月,第四屆以色列歌劇節來了一次別出心裁的創新,主創人員把舞台搬到了以色列南部城市馬薩達的沙漠上。主演們在炎熱的沙漠上,頂著風沙為5萬多名觀眾完整地演繹了三幕歌劇《茶花女》。憑著這部歌劇的魅力,當地酒店的數千間客房全部客滿,並且還多出了1000個歌劇節的臨時就業崗位。
(本報記者 申曉佳 實習生 李海嵐 整理)
(來源:重慶日報)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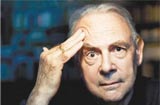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