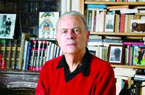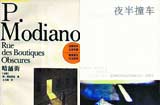在現代散文的園地裡,充滿智性的還有一類散文家,他們在出道之時閱讀的是革命的文學和西方的文學,在這兩種資源的雙重召喚下,開始追求一種新的智性寫作。這類作家既不能納入言志傳統,也無法歸入載道傳統,他們另辟蹊徑,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汪曾祺、王小波、史鐵生、周國平、趙園等人,他們的寫作影響著當代散文的發展。
汪曾祺的散文是當代散文的一座高峰。汪曾祺是沈從文的學生,文章中自然少不了沖淡的色彩,但他早期受到現代派繪畫和現代派小說的影響,所以也有一些非理性,有一種像繆哲所講的那種“非詩非文”的“匪氣”蘊藉在文章裡。他深諳文章之道,不是從魯迅和周作人那裡簡單移植,而是追根溯源,從宋人筆記和晚明小品出發,再吸收一些周作人、廢名和沈從文的文學因子,從而筑建了漂亮有趣的散文格局,超過了張中行、呂叔湘、舒蕪、鄧雲鄉等人。我們有時能夠在汪曾祺的文字裡,讀到一種清爽、明快和溫潤之氣,仿佛有一種幽思在腦際暗暗流動。他的散文銜接了中國士大夫的傳統,兼具濃烈的現代意識,自成一派,稱得上一個奇跡。
在自成一派的散文家中,他們或者從神學層面進入到個體幽深的精神領域,或者從德國近代哲學裡汲取精神養分,打開精神窗戶進行寫作。從神學裡受到暗示的代表是史鐵生,從哲學裡吸收精神養分的代表是周國平。
史鐵生的《務虛筆記》和《病隙碎筆》都帶有神學韻味。他從宗教、心理學、婦女研究、兒童研究等方面汲取了很多營養,最后形成了獨語體的文本。他完全顛覆了“五四”以來的小品文寫法,直接地與神學、思想家在文本中對話、交流,他經常思考的是存在的有無問題,成了一個思想的“叛逆者”。在史鐵生看來,我們的語言、敘事邏輯都出現了問題,其症結在於國人在表達思想和審美情調之時,話語方式已被世俗化了,都是世俗的語言,不能生長出思想和智慧來,或者說不能夠拷問存在的實有和虛無。史鐵生不斷瞭望時空,欣賞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超越世俗層面進行寫作,並最終找到一種思想者才擁有的話語方法。他的語言,很值得深入探究。
周國平研究尼採、古典哲學和近代哲學,加上他自己的生活經驗,也熔鑄成了獨具特色的文本。周國平的散文不斷被贊譽,原因就在於他是一位思想者和學者。他早年喜愛閱讀魯迅,后來走向尼採,受到了尼採強力意志和對自由意志態度的影響,末了又從尼採的世界裡走出來,創造了屬於自己的散文話語方式,一種自言自語的獨語體。
王小波的散文也非常受歡迎,他的散文可稱為當代智性散文的一個標志。王小波的思想源頭應當說是拉伯雷的《巨人傳》,哲學上是英國哲學家羅素的哲學,包括愛因斯坦的一些理念,在小說上他特別喜歡尤瑟納爾、卡爾維諾以及博爾赫斯等作家。王小波的小說和隨筆,使用一種非常規的方法,即狂歡的話語表達來解構傳統,顛覆流行的文化語法,形成一套獨特的智慧表達方式。
王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園》一書中說:“我反對愚蠢,不是反對天生就笨的人……在這個世界上,大多數愚蠢裡都含有假裝和弄假成真的成分。而且我討厭裝傻,渴望變聰明。”通過他的代表作《一隻特立獨行的豬》,我們可以看出王小波的寫作,其實就是反對裝假、裝傻般書寫的文化語境,他用自己的狂歡式寫作,用看似很簡單的語言,表達了一種聖潔的思想。他是用笑的方式、用癲狂的方式在寫文章,這也是他的審美方式,是我們這一代文壇所稀缺的。
木心是一個帶有趣味和智性的散文家。他最喜歡的文字是六朝的,他對法國詩人蘭波情有獨鐘,對波德萊爾、畢加索都很喜歡,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德烈·紀德的小說也頗為喜愛。他在文章裡表現出博覽群書之后的達到的有選擇的有比較的智慧,他在自己的散文隨筆裡形成一個豐富的世界,一會兒在古希臘,一會兒在波斯,一會兒在中國的六朝,一會寫紐約的感受,一會兒寫埃及的感受……他是一個游蕩在東西方文化中的自由人。
日本文學中優美的俳句眾所周知,但漢俳在如今卻是稀有的存在,木心卻是能寫漢俳的高手。一個句子,十幾個字,就疊出無數意象。木心有本散文集叫《哥倫比亞的倒影》,其詞語的豐富讓人驚嘆。就像錢鍾書在《管錐編》裡面打通中西,出現一種畫境一樣,木心也試圖做到這樣,但並非處處成功,他的有些作品過於追求辭章之美,有點做作,比如《上海賦》。
木心的古文非常好,他對漢賦的語言非常敏感,把先秦到兩漢之間語言最精妙的部分都吸收到自己的腦子裡來。木心背負著東西方文明,出現在我們面前,而他的寫作又從漢語的藩籬裡飛出來了,增添了另一種可能性。
白話文寫作不到100年,在這100年裡我們的寫作經歷了很痛苦的過程,有豐收年也有荒蕪年。但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65年,尤其是最近30余年的寫作過程中,散文寫作由單一的文化形態變得更加多元,出現了不同的作家群。在“五四”大的傳統之下,這30余年又形成了新的傳統,像汪曾祺、史鐵生、王小波等一大批人的散文或多或少地帶有一種智性,使漢語從模式化的語言,從單一的道德化語言裡,衍生出了種種新的文本。他們的文章回到了自身,回到了本源,豐富了當下的生活。
對於青年人的寫作而言,不一定必須在哪裡依傍。開始可能受某些人的影響,但最終一定要回到自身、成為自己。如果能發掘出自身內在的潛能,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一個獨特的存在,都能夠與東西方對話,與現實對話,與自己對話。
(本文由李琦、張鑫磊整理)
“讀書論世”欄目開辟的“漫談當代智性散文”系列通過孫郁老師的三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詮釋了智性散文的特點、發展及相關代表人物,讓我們對於散文的“智慧”有了更清晰的認識。這一話題已經結束,今后我們將定期約請名家就更多的話題進行探討。
——編 者
《 人民日報 》( 2014年10月14日 24 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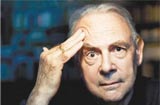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