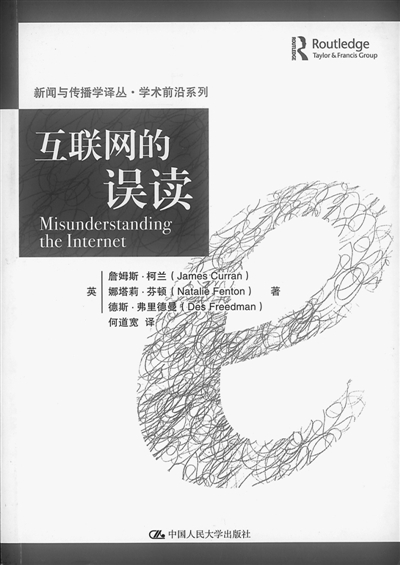 |
|
《互聯網的誤讀》,詹姆斯·柯蘭等著,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
對互聯網,從來不缺乏誤讀。
比如,互聯網是使我們更加聰明了,還是更加愚蠢了?這是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根據答案,可以分成“聰明派”和“愚蠢派”。
尼古拉斯·卡爾是后一派的領頭羊。他認為互聯網把我們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變得更愚蠢了。他在自己的《淺薄》一書開頭便指出,2007年,他意識到他自己的認知過程因網絡發生了改變,但並非是朝好的方向。“我失去了我原來的大腦”,其原因在於網絡那些閃爍的鏈接、嘈雜喧嘩的多樣性使人類變得愚蠢。卡爾認為,網絡正在重塑我們的大腦,“網絡弱化了我們對信息進行‘深加工’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正是支撐我們專注性地獲取知識、歸納推理、批判思考、想象以及沉思的關鍵”。他引用了一系列關於大腦和行為的研究成果,借此証明互聯網不但讓我們能夠進行不同的思考,同時也讓我們的思考能力變得更差了。
另一場大爭論的中心人物是《紐約客》作者、暢銷書作家馬爾科姆·格萊德威爾,他認為,社會化媒體作為社會變革工具的作用被高估了,因為社會化媒體激發的是人們之間的“弱聯系”,而不是活動家們需要的、能夠讓人們為之去冒險的“強聯系”。格萊德威爾的觀點對那些認為社會化媒體是變革的唯一原因,甚至將這些變革直接稱為“推特革命”的人是一種矯正。
雖然格萊德威爾也不認同那些主張社會化媒體根本沒有發揮任何作用的觀點,但批評者認為,他忽略了社會化媒體快速傳播另類信息和觀點的能力,而這些信息和觀點本來是難以達到如此廣大的受眾的。即便不能在社交媒體傳播同直接行動之間建立起強有力的聯系,那也無法否認社交媒體在影響公眾輿論方面的重大影響。
僅僅舉這兩個例子就可以看出,從互聯網誕生之初,人們就對這種橫掃一切的技術到底對我們這個世界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眾說紛紜。在這個意義上,詹姆斯·柯蘭等人所寫的這本《互聯網的誤讀》,不過是人文知識分子再次對互聯網發展中或許是內嵌的技術樂觀主義表示反對的一種回響。這種技術樂觀主義始於上個世紀90年代中葉,那時互聯網到處都引起敬畏和奇跡感,堪稱互聯網的“純真年代”。
歸根結蒂,互聯網的誤讀實際上是來自於當初互聯網的一些倡導者的信念,在那個“純真年代”,互聯網總是和這樣一些美好的“大詞”相聯系——開放,自由,民主,平等,不一而足。然而今天互聯網已經碎裂了,像柯蘭等人在書中寫的那樣,它現在是一片矛盾的海洋。起初的軍方試驗田被一群奉行自由至上主義的大學教授和技術“極客”改造為精英保留地,然后隨著商業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介入,互聯網已然成為新自由主義分子、開源軟件工程師、大媒體、大商業、民族國家的政府以及其他各種相互競爭的利益的斗爭場域。不過就在如此復雜的情況下,大多數用戶可能還愉快地以為,自己是在風平浪靜的海上航行,相信網絡的訪問是一種不知從何而降的慈善禮物。
憂心忡忡的柯蘭們試圖為不識廬山真面目的網絡用戶提供一部指南。這本書遵循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路徑,用勞動與剩余價值理論分析我們的在線生存。在網絡的葡萄園裡,我們都是辛苦勞作的工人﹔很多人以為類似“臉書”這樣的公司在提供服務,而實際上它們所鋪開的是一張無邊無際的監控之網。除了揭穿“服務即奴役”,《互聯網的誤讀》還花費大量篇幅解構互聯網具有內在的民主特質的神話,這主要是通過對大媒體和大商業的抨擊來完成的。全書有關互聯網經濟和監管的分析非常有力,給上一代的自由主義啦啦隊的不切實際的鼓噪潑了冷水、降了溫。
《互聯網的誤讀》試圖通過還原互聯網應用的社會語境,解構互聯網的各種神話,不僅包括天使化的神話,也包括妖魔化的神話。它的中心主題可以概括為:權力是至關重要的,互聯網既可以用來加強權力,也可以消解權力或是繞開它。所以,互聯網的內在本質既非民主也非專制,而是極大地——如果不是完全地——依賴於部署這一技術的語境。從來就沒有什麼技術的前定主義,一切都是路徑依賴。
該書最后對如何實現一個更公平和更包容的數字化社會提出了解決之道。遺憾的是,就像大多數批評互聯網的書一樣,作者的診斷能力高於開處方能力。他們所談論的有關互聯網的規制與其他人談論的對其他媒體的規制並無太大的不同,他們並沒有形成自己的觀點。換言之,作者對互聯網這種新媒體與此前的廣播報紙等媒體的區別認識不足。這實際上是批評新媒體的人最易犯的錯誤。
作者暗示,互聯網並沒有創造出什麼新的社會現象或社會變革,所有問題都潛藏於社會之中。但新媒體,無論它有多少不足,相對傳統媒體而言,仍然構成了一場量子躍遷。
《 人民日報 》( 2014年10月14日 24 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