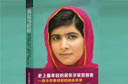李樯,河南安阳人,著名编剧。代表作品《孔雀》《立春》《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致青春》《黄金时代》。曾获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编剧奖以及金鸡奖、百花奖、金像奖、金马奖最佳编剧奖。

李樯与许鞍华
印 象
文艺气质
与生俱来
今年10月,由李樯编剧、许鞍华导演,众多明星加盟的电影《黄金时代》上映,实验性的拍摄手法,由演员出戏念台词的间离效果,3个小时的片长,都给观众带来很大挑战。票房并没有想象中的理想,但与同档期上映的其他国产片相比,这部电影还是受到了最多的关注。10月1日,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公布入围名单,《黄金时代》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女主角及最佳女配角五项提名。这部影片还将代表香港地区角逐2015年奥斯卡外语片奖。
7月21日,《黄金时代》沙龙在北京单向街书店举行,许鞍华和李樯同时出现,众多文艺青年挤爆了活动现场。这是记者第二次见到李樯。上一次是2013年5月,《孔雀》《立春》《致青春》三部剧本成书出版,李樯走进北京大学“未名讲坛”,与学生们交流剧本创作的心得。
李樯喜欢穿素色宽松的衣服,说话轻声细语,笑起来温文尔雅,举手投足都体现出一个写作者应有的状态。如他所讲,写作对于他,就像农民下地种粮食、工人上班,是很日常的劳作生活。如果说他的“劳作”与他人有何不同,那么最明显的标签,就是他那种似乎与生俱来的浓郁的文艺气质。“只要你想拥有精神和心灵生活,你就是文艺青年。”李樯这样解释“文艺青年”这个称呼,“只要曾被一首歌打动想去学吉他,或者突然看了一部电影想成为那个主人公,任何对于自己身份的假定和想象都是创造,这种虚构的能力就是文艺的表现。”
年轻的岁月,李樯过得算不上顺利。19岁高中毕业后入伍当兵,两年后进入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学习,毕业后进入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做编剧。工作两年后,他转业回老家安阳市文化局,写“自己一点儿都不懂”的豫剧。不久后,他重回北京,做了“北漂”。2000年,颗粒未收的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他又回到安阳老家。
“所有编剧经历的一切困扰我都经历过。不给署名,当枪手,写完不给钱,用了你还不承认,全都碰见过。”聊起那段日子,李樯觉得那就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他甚至有些感谢那些坎坷和由此带来的痛苦,“为什么人要避免痛苦?很多所得明明是在痛苦中锻炼出来的啊!那为什么人人都要抗拒痛苦而去追求幸福呢?”
2005年,顾长卫把李樯编剧的《孔雀》搬上银幕。那时候,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尚未形成。2013年,李樯根据辛夷坞小说改编的《致青春》由赵薇担任导演,上映后票房超过7亿元。金牌文艺编剧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让他有底气拿出《黄金时代》的剧本,这是他第一次聚焦真实人物,第一次让故事离开当下,进入那个充满理想又充斥战乱的民国年代。
如今,国内薪酬超过100万的编剧只有三个人,刘恒、芦苇、李樯。而李樯每天的生活依然简单得像白开水,一般情况下,他会在写作和阅读中度过,有时上网看微博,他会发现时代变化得太快了,“大家都没有耐心去认真思考、讨论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对李樯来说,现在大概就是他的“黄金时代”,当然这也是一个快得让他困惑到无所适从的时代。他希望能保持从容的状态,“我在某个阶段只能写我当时的能力和思想能够表达的东西。我觉得我就像是一个手艺人,为我的客人定做出他所满意的东西,同时这个东西里面也包含了我的匠心。我就是去写作,仅此而已。”
李樯口述 我眼中的萧红
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接触萧红的作品。那时只是对她文学作品的认知,零零星星对她的身世有了一定了解。那时候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拍她的传记片。
萧红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你越走近她的时候,你发现她离你越远;当你觉得她很远的时候,似乎那种亲近的感情又产生了。萧红是一个特别独特的作家,我叫她“源头性作家”,之前没有这样的作家,之后也没有这样的。她的原创性在某种程度上比张爱玲还高,她没有师承于谁,她是天地造化的一种文笔,更大刀阔斧,更印象主义,更现代。她认为文学没有什么规律,没有一定要遵循的东西。张爱玲还能看出受《红楼梦》这种中国章回体小说的影响,受弗洛伊德、毛姆的影响,还能看出她的师承,当然她是一个集大成者,但是她是有迹可循的。
很多作家的身世和作品是不能合二为一的,毕竟一个是虚构的东西,一个是真实的经历。但是萧红的作品跟她真实经历是重合的,她写的东西,也是她经历过的事情,在她的作品与人生之间的界限已经融合了。
《黄金时代》有一场戏,萧红在香港,弥留之际跟骆宾基的一段谈话,这当然不是萧红写的,是我写的,我托萧红之口说了一段话。她说:“骆宾基,我在想,我们每个人都是隐姓埋名的人,并没有人能知道我们的真相,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真相。若干年后我不知道我的那些作品还有没有人会翻开,但是我知道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隐姓埋名的,别人或者知道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但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全部,连他自己都只知道自己的一部分。我能感受到萧红的气场,但她有限的照片只是她某些瞬间的状态,很难代表她整个人所有的时间段。在萧红的人生里,爱情占了很大比重,这可能耗损了她很多东西,但同时也馈赠给她很多。我对萧红没有哀其不幸。让我觉得动感情的,是她很短寿,她经历了这么多,人生尽头写出《呼兰河传》,作为一个写作者,她已经赚了。所以我觉得,一个作家的一生是和他的创作紧密相连的,长寿也罢,短寿也罢,贫瘠也罢,富有也罢,他经历的事情都是他写作必然的命题。
用实验的方法呈现萧红的“黄金时代”
记者:《黄金时代》的结构特别复杂,不是那种普通的人物传记式的平铺直叙,这一点您在创作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
李樯:在写《黄金时代》之前,我大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阅读和思考。《黄金时代》不是《乱世佳人》,也没有《乱世佳人》里面那些特别情节剧的东西。虽然萧红自身的绯闻轶事充满传奇性,但是当我沉浸到史料中,却发现她其实没什么故事,很多传奇是虚晃一枪,说穿了她就是跟那几个男人不合适。我的兴趣并不是说如何还原萧红,而是对于时空的一种探索,所以我用了解构的、实验性的方法来写一个经典的历史人物。传记片有没有别的写法?抛开平铺直叙生平履历式的东西,可不可以有新的东西?也可能不讨好,但我愿意去做与众不同的工作。
记者:您怎么理解“黄金时代”这四个字?
李樯:“黄金时代”这个词有波涛般的诗意,有点像“桃花源”。这个片名来自于萧红在1936年写给萧军的一封信。萧红当时人在日本,她说我现在有面包吃,有炉火可以去烤,但却是在时间的牢笼里面度过的,她说这真是我的黄金时代。其实她里边有一种反讽。可是她的确是生在那个时代,使她成就为萧红的也的确是她人生的某个黄金时代。我觉得,我们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时代,都是在追求一个心中的圣地。
记者:《黄金时代》有一种方式,让演员跳出他扮演的角色对着镜头说话,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
李樯:在你所身处的时代,你对历史的读解只能代表你主观的私人视角,而历史的全貌不会因为你是亲历者而一览无余地在你眼前呈现,你不可能成为历史的最正确和唯一的见证者。那对过往的时代呢,历史或历史人物已经离我们很远了,我们其实都是在二手、甚至三手资料包围的状态来看历史,有粉饰、有遮蔽,也有歪曲。
过去拍一个历史题材的东西,我们老是力争还原。后来我想,人和历史是不可复原的,你弄的细节再像、质感再像,那个时代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不一定。斩钉截铁的表达反而才是最不正确的。那在这个前提下,我就想,既然我写的时候很难,演员演的时候也很难,那倒不如把这种虚妄感排解出来,让演员在剧中扮演他所认为的那个人物的样子,同时也让演员从里面解脱出来,告诉观众演员是在扮演,把观众也带进人物去。他在正儿八经演的时候,观众知道是个故事片,而他突然对着镜头讲的时候,又像一个纪录片。我要让观众知道我们是在扮演这段历史,我们力争扮演得很像。就目前来说,可能很多人在以往的电影中是没有看到过这种方式的。
记者:《黄金时代》呈现了左翼作家群像,在您看来,除了左翼思想,这群作家是否有其他共性?
李樯:我觉得那时候人对共产主义信仰是特别敏感的,因为它憧憬了一幅人类最崭新、最美好的宏图。我如果出生在当时的话,可能也会是一个非常炙热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但这不足以使这群人就一定有相似性,比如说,萧红看似是一个左翼作家,结果走向了个人主义;丁玲看似个人主义,但走向了左翼。我认为他们的个性更迷人。
记者:有人说《黄金时代》是用商业片的方式去拍文艺片,您编剧的《致青春》票房也非常成功,您可以说打通了商业片和文艺片之间的屏障。
李樯:《黄金时代》本身没有一点商业心,它没有讨好观众,可是六千多万投进去,一定要让人家公司赚回来的。大家总说我写文艺片,其实我真的没有把它们当作文艺片去写。就是这样的故事让我感动,我就去写了。我没有把自己的剧本归为文艺片、商业片,我本身觉得这种划分很无聊,对什么素材感兴趣,我就会倾情而出。即使我写小说,我也想畅销。为什么一提畅销就一定和艺术发生分裂呢?莎士比亚在那个年代非常受欢迎。我们所热爱的那些电影大师,没有一个不想打进好莱坞。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有既有文化、又很娱乐的作品?
我感受到自己笔下人物给予我的力量
记者:您的《黄金时代》的时间背景是上世纪30年代,《孔雀》 描写的是七八十年代,《立春》是90年代,《致青春》又是本世纪初年轻人生活,您如何把握这种年代的变化,如何捕捉不同时代人的想法和生活状态?
李樯:每一个不同时期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都是不同的,每个时间段的人都有他们在那个时间段里特有的精神风貌。想捕捉那个时代的人的想法和生活状态,就必须要捕捉那个时代的特质。探讨不同时期的人,就是探讨不同时期人与社会的一种关系,以及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期,人所呈现的精神面貌。人是时代的尾随者。我很少讲一个人的故事,我对人物众生相有一种偏好,无论是《致青春》,还是《黄金时代》,《黄金时代》是讲一群人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故事。
记者:在您的故事中,很多人物都是为了理想而和生活争得鱼死网破的状态,这一点从《孔雀》开始,一直到《致青春》,到《黄金时代》,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您是怎么理解这种坚持的?您也是这样的性格吗?
李樯:人这一生并不是事事如愿,人都需要与自己的命运搏斗,每个人都是一个战士,你需要在命运的战场上厮杀、享受。所以我觉得不只我是这种性格,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一种处境。我觉得这是一个交相辉映的过程。我们都是在生活中修炼,没有绝对的改变,也没有绝对的坚持。我现在面对的未来岁月,依然有很多挫败在等着我,生老病死,人生的无常,全在我眼前,我依然要面对各种心灵的困境,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记者:您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您之前认为《立春》是“挽歌”,现在纠正为“颂歌”,为什么呢?是您自己的心态在变化吗?
李樯:我们不能拿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否来界定这个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这些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待事物的看法也会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有了一种新的写法,而是说,我慢慢感受到自己笔下人物给予我的那种饱满的力量。《立春》,包括《孔雀》,包括我的其他的电影,里面的人物都是敢于对自己的命运有担待的人,他们身上那股饱满的生命力教育了我。
写作本身就是一条崎岖的道路
记者:您出生在河南安阳,您的很多剧本都定位在小城市,描摹特别普通的生活场景,能不能谈谈您对这种日常生活是如何把握的?
李樯:我出生在小城市,小城市的生活是与我血脉相连的。其实多数人是在小城市长大的,毕竟大城市就那么几个,小城市代表了中国多数人的生活样貌,它有一种普遍性。我对菜市场有很深的感情,我觉得那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场所。菜市场有着对生活最基本、最朴素的依赖与要求。每次走进菜市场,我都觉得那是最能裸露生活面目的地方,里面有一种生生不息、孜孜不倦的对生活的渴望。
记者:您与关锦鹏导演和赵薇的合作,在接下来的《放浪记》中还将继续,选择他们是不是因为大家都很熟悉,合作起来更加顺畅?如果你们的意见或者想法有分歧,谁更容易妥协呢?
李樯:赵薇和我是很多年的好朋友,我们合作过《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后来她当导演需要找人写剧本,我又恰巧是做编剧出身,所以她约我为她写毕业作品的剧本。我们俩是一拍即合,很有默契。我们合作完《致青春》以后,双方对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了,我认为《放浪记》里的人物非常适合赵薇来演,这是一次客观冷静的合作。无论跟哪位导演合作,当然会有一些意见是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在法庭上辩论一样,谁说得更对,就服从于谁的意志。我们会把私交放到一边,这样的辩论是为了达到更准确的、更合理的结果。
记者:关于剧本创作,改编是不是比原创更容易一些?您认为一个编剧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李樯:原创剧本就像自我生长的一株树,而改编则像是一次嫁接,改编后的剧本是一株嫁接的植物。其实这两者都不容易,写作本身就是一条崎岖的道路,对于写作本身来说,是没有本质差别的。编剧要想成功并不难,一方面是要看你的作品是否可以打动别人。这个时代不太像梵·高那时候,天才容易被埋没。写《孔雀》那个时候是可能的,电影行业没那么发达,剧本很容易被隐匿。所以就看你能不能写出特别好的故事,很特殊、独树一帜,打动这些搞电影的人。另一方面是要看你有没有认清电影编剧和小说作者的区别。编剧不是一个个体化的东西,它一定是工业化的、群体性的东西,要看你的个性是不是和一群人的东西合上槽了,否则很可能十年八年都拍不了。
记者:入行以来您的写作状态有哪些变化?
李樯:现在我的写作状态,有一点和我当年写《孔雀》时是一样的,每次遇到新的题材都会面临困境。我对写作还是很胆怯的。编剧不是演员,不是你有一张脸,就成了符号,即使作者是李樯,电影公司还是要看了剧本再说。你这一部作品的成功和下一部作品的成功关系是零,一点都不意味着你的名声会让你下一部作品台词更棒、结构更棒。所以我要告诉每个写作的人,你每写一部作品都是一次冒险,是一次失败与成功互相折磨的历程。每年我都会发现自己新的兴趣点。现在帮关锦鹏写《放浪记》,就是一个与以往不太一样的东西。兴趣不同,东西就不一样。
记者:您以后会一直在文艺片这条路上走下去吗?您会亲自导演自己的剧本吗?
李樯:可能别人都觉得我很文艺,其实我不是一个一直维护所谓文艺片特色的人。但是我要坚持一点,不管写什么都有我的色彩。我非常喜欢警匪片,我要写一个警匪片,我还会写一个犯罪片,故事全有了。我相信将来自己会做导演,但一定不是我自己酝酿的题材。我会拍一个离我很远的东西,那时就是我对自己、对电影审美的考验,是我关于电影的见识和世界观,但我不会拍自己写的本子。本报记者 何玉新
(来源:天津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