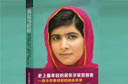茫茫戈壁,一位玄色行者,孤身独现。这是《随云行走》中《黑衣行者》一文记述的镜头。读到此处,我顿然而醒:马汉貌似平静的血液里,实际就一直潜住着这样一位隐忍的、满心渴求孤独前行的“黑衣行者”。这是我阅读《随云行走》的秘密发现。或者可以说,《随云行走》这本书,为我长期以来对这个作家的一种感觉,提供了佐证。
书中记载的一个场景——他记忆里恒久保存的一个梦幻场景,也直接支持着我的上述判断:“一匹说不清颜色的马,驮着我在荒漠中奔跑,那马没有镫子,我光着脚紧攥着缰绳。风很小,空气像液体一样,马蹄无声,心息无声。我看着自己在奔跑。照理说那骑马人不应是我,可我一直这么固执地认为,那是我。”
“我是游牧民族的后裔”,这是他“一直深埋心底”的一份直觉,这是马汉对自己的固执认定。
生命的本质应该是自由,但现实之中,我们却被有形无形的绳索重重束缚。
对于这生命的重重束缚,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麻木,浑然不觉,或者无奈。而马汉,则是少数的清醒者和倔强反抗者,因为他血液中的黑衣行者,是如此真切地听到世俗的听觉之外,远方的呼唤和自由的呼唤。黑衣行者日夜冲撞着马汉的身体,在奔突,在应答。
所以,马汉用行走来对抗生命的束缚;所以,《随云行走》,是一本呈示生命尖锐矛盾冲突的性情之书。
马汉是粗犷的。在夜晚的高原山口,在铁一般凝重的戈壁深处,在掠过大西洋的风中,在黄昏古老神秘的苏尔笛音里,他默默填充着自己的生命。常常,他有秘密的感受和秘密的心情。旅途之中,“没人知晓我的这种心情。我为这一没人知晓,而暗暗激动得心房发酸”。
这位自认是“游牧民族后裔”的作家,他的粗犷,是他生命的显性一极。而对于一名成熟的作家而言,生命,必定应该是完整而平衡的。是的,在《随云行走》这本书里,我还读到了他生命隐性的另外一极:敏锐与细致。
我特别注意到他的除夕心情。只有对时间和生命有着敏锐、细腻感受的人,才会拥有这样的心情——
“除夕的下午总是显得特别静谧。我总是小心地带着痛楚的心情来独自享用它。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回想着这里戛然消失的热闹和紧张,检点一番自己忙碌的一年。然后,用封条封好门窗,骑车在空荡荡的大街上转悠,看着纸屑垃圾在空旷的街上打旋,像一个好不容易分得一点可怜的糕点,想解馋又舍不得吃地捧在掌心的孩子一样,我珍视这份宁静;我为拥有这静谧而兴奋得心一张一弛地发酸。”
“有一年除夕的下午,我来到打烊前的书店。偌大的营业大厅里,除了焦虑等待下班铃声的营业员外,仅我一个顾客悠悠地浏览在书架前。这时,音响柜正在播放爱尔兰歌手恩雅缥缈、空灵的歌声,那歌声在大厅里回荡……那刻里,我有了裸体升浮在云朵里的感觉。”
粗犷、男性、敏锐、细致,再加上生命内在的矛盾冲突,结晶并成就了这册《随云行走》。
书中,这位作家说过的一句话,亦能加深读者对这本书的真正理解:“在热闹中只会滋生出左右逢源的浅薄,唯有在孤独中,才能熬炼成厚沉、纯真的人格。”
《 人民日报 》( 2014年10月20日 24 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