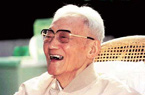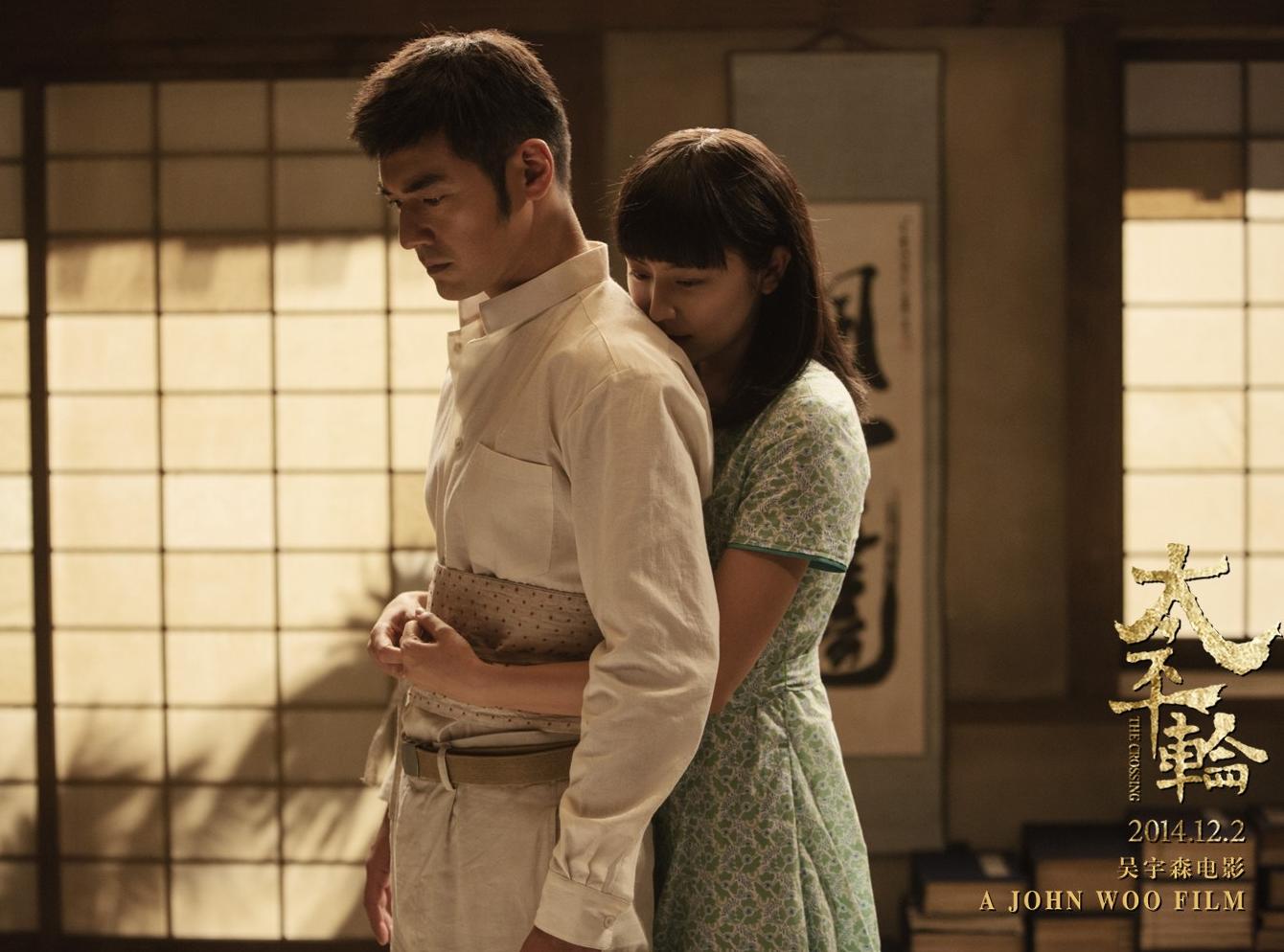原標題:好萊塢票房變革,從娃娃抓起
《飢餓游戲:嘲笑鳥(上)》自上周五起在全球各地陸續上映,這是年末備受關注的電影之一,中國觀眾預計將在明年1月看到此片公映。至此,這個在好萊塢掀起“少年電影”熱潮的系列進入尾聲,兩年前《飢餓游戲》上映時,只是被當作一部以少女為主角的成長主題電影,還有些步《暮光之城》后塵的意思。那部電影以難以想象的票房風暴,把銷量平平的小說送上暢銷排行榜,也讓“少年電影”成了好萊塢大片廠趨之若?傾注重金制造的“新類型”。兩年來好萊塢不停地尋找新的《飢餓游戲》,希望青少年市場成為新的利潤來源,然而作為后繼者的《分歧者》和《移動迷宮》再也沒能在市場和評論界掀起《飢餓游戲》曾制造的波瀾。
英國《衛報》的專欄作者總結了一下,在《飢餓游戲》和《移動迷宮》這些電影裡,青春期的主角們生活在一個禮崩樂壞的世界裡,成年人是冷酷的統治者,要活下去就要不停地戰斗,最有意思的是,讓少年們掙扎存活的大環境,是沒有任何先進通訊設備的原始叢林,電視、電話、網絡等一切媒介,是來自成人世界的殘忍武器。“這些故事很容易讓人想起《蠅王》,但是《蠅王》不會被貼上'少年'的標簽。”所以,在這兩三年裡迅速膨脹的“少年文學”和“少年電影”,更像是事先張揚的商業概念。
這也不奇怪,在傳統大片所針對的成年男性市場飽和以后,好萊塢把票房的希望寄托於青少年觀眾,但這個群體對於大部分的片商和制片人而言,是一個他們用想象難以去接近的群體,他們太靈活也太多變,好萊塢習慣依賴的“標准”遭遇了最抵制“標准”的一群人。跟風凶猛的結果是太多試圖成為“飢餓游戲第二”的電影在市場上潰散,過分的樂觀迅速帶來急於定論的悲觀,“少年電影”是否能成為好萊塢系統裡有穩固商業價值的一種“類型”,像它所面對的觀眾群一樣,也是個充滿變數、有待琢磨的話題。
《飢餓游戲》一反常規狀態地以電影帶紅小說銷售並帶出整個書市中“少年文學”的異常繁榮,好萊塢的大片廠幾乎是欣喜若狂地找到了新的改編來源。
在《飢餓游戲》電影上映前,蘇珊·柯林斯的小說原作銷量並不出眾,在書評版上,它被描述成一部概念先行、人物臉譜化、文筆很成問題的少女瑪麗蘇小說。
2012年,《飢餓游戲》第一部上映前,它在北美票房預售榜單上排在《暮光之城:新月》、《哈利波特和死亡聖器(下)》、《暮光之城:破曉(上)》和《暮光之城:月食》之后。那是一個驚人的開局,當時有產業分析師認為,這得益於《暮光之城》系列的巨大成功,是一部跟風的“少女電影”。
電影首映當天,統計數據驗証了分析師的預測,觀眾中39%是女性。然而首個周末放映后,格局大變,影片在三天內取得1.5億美元票房(僅北美),原作小說一夜脫銷,當時在紐約地鐵上,一度出現人手一本《飢餓游戲》的盛況。“飢餓”很快蔓延成一種現象,電影制造了以百萬計的新讀者,以至於“青少年小說”是2011年到2012年間產量和銷量都增長最快的一種圖書類目,2012年的歐美書市上,青少年題材的小說佔到16800種。《飢餓游戲》小說三部曲在電影拍攝前的銷量是240萬冊,電影上映的短短幾個月裡,小說的銷售量翻了2.5倍,數字增長到650萬冊。
在好萊塢這個龐大的娛樂工業系統內,事件總是比作品更重要。在《哈利波特》系列電影每年給華納公司帶來超過10億美元的收入時,“青少年題材”在書市上尚未成為一個能帶來巨大銷量和利潤的類別,根據2005年的數據,當年少年和兒童題材總共不超過1500種,J·K·羅琳的《哈利波特》像是一個不可超越的傳奇。當《暮光之城》橫掃被超級英雄片壟斷的暑期檔時,話題集中於“少女的逆襲”和“女性觀眾的購買力”。直到《飢餓游戲》一反常規狀態地以電影帶紅小說銷售並帶出整個書市中“少年文學”的異常繁榮,好萊塢的大片廠幾乎是欣喜若狂地找到了新的改編來源,並且試圖把《飢餓游戲》的成功當作可以復制的經濟模式。
好萊塢好大喜功的習慣透支了“少年電影”的商業潛能,不斷有同類的電影試圖成為新的《飢餓游戲》,但前浪尚未退潮,后浪們連沙灘都沒見著就已經銷聲匿跡。
從2012年至今不到三年的時間裡,少年電影從《飢餓游戲》這個成功的案例迅速擴散成一種發育過快的類型,這個曾經隻在中小制作電影中佔據有限比例的小分枝,被當作新的“系列電影”和“賣座大片”的培養皿。短短的時間裡,不斷有同類的電影試圖成為新的《飢餓游戲》,但前浪尚未退潮,反而是前赴后繼的后浪們連沙灘都沒見著就已經銷聲匿跡。
《吸血鬼學院》的小說賣了900萬冊,電影票房不到800萬美元。《美麗生靈》的原作銷量350萬,而北美票房隻1900萬。曾佔據暢銷排行榜的《宿主》改編成電影,票房2700萬。同樣針對少女觀眾的《聖杯神器》,3100萬的票房完全不夠回收它的高昂制作費用。《安德的游戲》是最入不敷出的,制作費用1.1億美元,全球票房勉強剛過1.2億。《記憶傳授人》的情況稍好,投資2500萬美元,票房5200萬,是這兩年裡扎堆的“少年電影”裡投入產出比例相對不算“慘烈”的一部,但這個票房成績並不足夠新開續集。以上這些電影,每一部的結尾都保持著未完成的開放狀態,但這些故事沒有可能繼續,它們有一個充滿壯志雄心的開局,卻淪為半途而廢的殘章。
《移動迷宮》的3300萬首周末票房和今年早些時候的《分歧者:異類覺醒》的5400萬票房,盡管在今年的排行榜上已屬良好,但和《飢餓游戲》第一部的1.5億美元首周末票房不堪相比。好萊塢產業內部對於“尋找下一個《飢餓游戲》”的焦慮從未停歇,《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分析文章回顧了《飢餓游戲》以及更早的《哈利波特》和《暮光之城》系列,整理出“少年電影”的前世。最初的兩部《哈利波特》電影--《魔法石》和《密室》的定位是需要家長陪同的兒童電影,也是好萊塢最受歡迎的全家歡電影,從第三部《阿茲卡班的囚徒》開始,這個系列向少年和青年趣味傾斜,在傳統大片專注的成年男性觀眾和全家樂市場之外,刺探到青春期少男少女這個不被特別重視的受眾群的范圍。《暮光之城》直接進入被好萊塢男性決策者常年忽略的領域--年輕姑娘尤其少女的市場,事實証明她們對票房的貢獻足夠讓《蝙蝠俠》黯然,在2008年前后露出疲態的超級英雄電影根本招架不住小清新的逆襲。《飢餓游戲》第一部的成功之處在於,它以少女歷險的主線故事立足於女性市場,而敘事節奏和影像風格完全能吸引成年男性觀眾。這三個系列各自有明確的目標和策略,是成功經驗難以被簡單平移的個案。然而大制片廠對利潤的飢渴,對“下一個哈利波特”、“下一個暮光之城”和“下一個飢餓游戲”不切實際的索求,拔苗助長地制造出“少年電影”這種根基並不牢固的類型。
專注於社交網絡數據分析的Fizziology,其創始人之一卡爾森認為,好萊塢幾十年來好大喜功的習慣透支了“少年電影”的商業潛能:“青少年群體當然是一個商人們必須去逢迎的群體,但少年電影遠遠沒到能成為票房巨獸的地步,以一部大片的商業要求,首周末票房必須在5000萬以上,1500萬就是失敗了。這對於眼下的大多數少年電影而言是不可能的任務,相反,安心地把一個故事做好,不要寄希望於續集,安於小布局,才是現實的策略。”確實像卡爾森提到的,除去《飢餓游戲》這一部現象級電影,這兩年裡刻意“做大”的少年電影除了《分歧者》和《移動迷宮》,無一幸免地栽了,反而是幾部甘於像1980年代校園片那樣的中小投資小電影,低調平穩地盈利了:以1100萬美元制作的《如果我留下》票房達到6000萬美元,投資不超過1200萬美元的《星運裡的錯》的全球票房則夸張地超過3億。
穿梭在二次元和三次元之間,經常“腦洞大開”的這一代少年,對電影類型的認知不再是傳統的類型概念,他們壓根拋棄了類型這回事。
盲目地把少年電影做成系列大片是過度發育,但不能否認青少年這個群體對電影市場的影響。《暮光之城》是個極好的例子:這個系列部部賣座,因為“暮光”的照拂,原本男性荷爾蒙泛濫的超級英雄片開始向女性趣味傾斜,漫威的《復仇者聯盟》、《美國隊長》和《銀河護衛隊》的巨大反響,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女性觀眾的認可,女人們貢獻了票房的半壁江山。既要在感情上籠絡女性觀眾,也要在審美造型上迎合少年趣味,於是少女風席卷影市,直到今年夏天,《移動迷宮》“撥亂反正”地打出廣告語:“這是第一部以男孩為主角的少年電影”。
少年受眾群的龐大數量和他們潛在的消費力讓片商不能不逢迎,但以90后甚至00后為主的這個群體,不同於之前的代際,在社交網絡和二次元的世界裡長大的他們,嚴重地欠缺群體的同一性。
美國票房追蹤公司Exhibitor Relations的總裁是這樣說的:“各大片廠的市場營銷和電影項目的決策者是成年人,成年人不要理所當然地以為自己了解現在的少年,不要用上一代的思維去想象下一代,也不要以為你們指著他們的腦袋就能讓他們心甘情願覺得你們的想法很酷。成年人做出的決定裡,70%是把握不住少年人的心思的,剩下的三成希望裡,如果你確實能擊中年輕人的興奮點,那將能大贏。”一位制片人直接地嘆苦經:面對這些年輕人,你永遠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風一吹,他們的想法都能變上好幾遭。
一位票房分析師針對好萊塢的“改編依賴症”指出:“對於電影這種投資越來越高的娛樂產品,一個完全原創的點子無疑承受太高的風險。但有現成讀者基礎的小說改編絕不是盈利的保險閥,無論有多麼強大的小說背景作支撐,一部電影成功的前提必須是它自成一體。”這段話很好地總結了《安德的游戲》、《聖杯神器》、《美麗生物》和《宿主》這些電影大同小異的失敗:它們過於依賴原作的粉絲群也過分地依賴情節,在背書式復制情節的過程中,放棄了電影自身的獨立與完整,劇情結構虎頭蛇尾,拙劣得像一集半吊子的連續劇。《移動迷宮》受到的指責也在這裡,片方早早確立三部曲的計劃,以至於這部電影成為懸念沒完沒了的長篇鋪墊。
再則,對於浸泡在互聯網文化中的這一代“少年”,穿梭在二次元和三次元之間,經常腦洞大開的他們,對電影類型的認知不再是傳統的類型概念,甚至,他們壓根拋棄了類型這回事。“少年電影”本身更像是上一輩強加於他們的腐朽觀念。他們和電影的相遇,其中交雜著游戲文化以及臉書和推特這些社交網站。能在這個群體裡制造回響的電影,更深層次地和眼下正在掀起的媒介革命風暴聯系在一起。
十幾歲的觀眾他們渴望看到一個和現實有明確差異又異常生動的異世界,那個彼岸本質上是對他們正在經歷的現實經驗的曲折呈現,是容納他們煩惱和叛逆的桃源鄉。
《分歧者:異類覺醒》被認為是《飢餓游戲》之后在票房表現上最有說服力的一部。這部電影的誕生看似是復制《飢餓游戲》的成功,但“復制”過程中操作細節才是真正耐人尋味的。2011年,獅門公司電影部門的老總費格在《暮光之城》誕生后的三年裡看了沒完沒了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模式的情感劇劇本,在《飢餓游戲》第一部的后期制作過程中,他聽說了《分歧者》這部小說,故事以近未來的芝加哥為背景,青少年要接受一個類似“哈利波特”裡分院帽的測試,被分成“勇敢、善良、無私、誠實”等族群,而其中有一個特殊的分類,就是分歧者。小說的背景和設定讓費格感到新奇,雖然主角是16歲的少女這點和《飢餓游戲》太像,他還是決定買下版權並簽約作者。當時,作者羅斯隻有21歲,剛從西北大學畢業,這部小說是她一年前開始在網絡上連載的。
其后,《分歧者》從連載到出版,從小說到銀幕,不僅是一部電影的改編,更像是一樁環環相扣的流行文化事件。羅斯寫《分歧者》第一部時,是隨時會消失在人海的網絡小透明寫手,獅門公司利用《暮光之城》的巨大粉絲群,進行點對點推送,先不選擇紙質出版而是把部分章節貼到《暮光之城》的臉書賬號上,那個賬號上有4500萬粉絲,隨之而來的閱讀量和傳閱率是驚人的,讓一個新人寫手的新小說迅速成為大眾話題。《分歧者》正式出版后,在《暮光之城:破曉(下)》和《飢餓游戲》的首映禮上,片方給這兩部電影的影迷免費送書。從社交網絡上牢牢抓住讀者之后,再經影迷群體的擴大,《分歧者》很快佔據暢銷書榜單上的席位。去年十月,續集《忠誠者》在哈珀柯林斯書店第一天上架,創紀錄地賣出45萬5千冊,當月亞馬遜的數據顯示,《分歧者》三部曲的銷量已經超過《飢餓游戲》20%。與其說這是對《飢餓游戲》的一次復制,不如說這是全媒體時代針對特定人群的一次高端定制——在對的渠道、找到對的用戶、發布用戶確實歡迎的內容。
(來源:文匯報)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回顧近10年的春晚主題
回顧近10年的春晚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