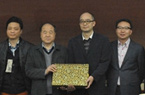最近,電視劇《紅高粱》上映。由我的小說改編而來的故事,發生在70多年前,為什麼還能吸引現在很多觀眾?我想主要還是劇中的人物都性格鮮明、栩栩如生,能夠讓觀眾從他們的生活感受到自己的生活,從他們的命運聯想到自己的命運,從而使一部歷史劇與當下的生活產生密切的聯系。我小說中的很多人物,都是以我的故鄉真實存在過的,或者聽過其傳說的人物改編的,基本來自於對人物原型的描述。
《紅高粱》中著墨最多的首推“我奶奶”,由3個現實中的人物合成﹔《檀香刑》中的戲班班主孫炳,就是清末時期反抗德國人被抓,后被清政府處以酷刑的高密農民孫文﹔《生死疲勞》中“單干戶”藍臉的原型是我家鄉一個堅持單干的農民,我爺爺也是其重要原型之一……這種原型的力量非常巨大。
很多人物都有真實原型,因為就是他們給我提供了靈感,是他們的存在讓我感覺到寫作的時候如魚得水。我想隻有作家獲得了這樣一種親切的、真實的感受,寫出來的人物才可能是有生命感的,才有可能具有鮮明的個性。
無論多麼有才華的作家,都不可能脫離自己的生活來寫作。盡管作品可以寫得上天入地,但就像一個人無法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土地一樣,作家也無法脫離自己熟悉的生活。我熟悉的生活是中國北方農村的生活,讓我寫一位南方的或者城市裡的人,我就感覺心裡沒底,非要寫也寫不好。我寫我家鄉的紅高粱,能寫得讓讀者仿佛身臨其境。我后來寫過一篇海南島紅樹林的小說,由於我不熟悉,盡管也去採訪過,也鑽到紅樹林裡實地考察過,但還是沒有親切的感受,覺得它跟我沒什麼關系。別人也問我為什麼寫的都是狗啊、牛啊、豬啊,沒有別的動物,我說因為我找不到別的動物的原型。如果讓我寫袋鼠、寫熊貓,估計我無法下筆。
小說構成的因素很多,作家要錘煉語言,要設計結構,要編織故事,要刻畫人物,但我想最重要的還是要圍繞著人物來寫。貼著人物寫,是沈從文先生教他的學生汪曾祺的一句很重要的話。寫人物的時候不要過多地考慮他的階級屬性,也不要給他貼上好人還是壞人的標簽,不管是好人還是壞人,都首先應該把他們當成人來寫,站在人的立場來寫,寫出好人的弱點,也要寫出壞人的尊嚴,這樣才能克服小說的地域性障礙,獲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証。
而且,作家要想持續不斷地寫作,就必須克服個人的好惡,與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越是你不喜歡的人,越有可能成為你小說中的原型。這樣的經驗積累得越多,對人的認識才可能越全面、越深刻,寫作才越有把握,寫出來的人物才越有真實感和生命力。
我曾經說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實際上我是一個觀察人、研究人,包括觀察我自己、研究我自己的人。隻有理解了別人才能理解自己﹔當然,也隻有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理解別人。
(本報記者賀林平根據作家莫言11月30日在中山大學的演講整理)
《 人民日報 》( 2014年12月01日 12 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