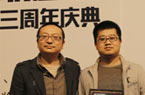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它既反映时代,又不可避免地受其制约。然而,文学又要追求永恒,经典的作品会让不同时代的读者在相同的文字中获得感动。那么,是什么特质让文学有了这种历久弥新的魅力?本文作者将带领读者,从萧红的文字中寻找答案。
电影《黄金时代》的上映,令萧红现在很“红”,也很“火”。微博上、微信上、报刊上、杂志里、地铁广告牌和电影大屏幕上,许多人谈论她的故事、情感、小说,这意味着这个作家回到我们的生活空间了,就像从未离开过一样。这件事情与她的年龄可真不相衬。其实她是年轻作家,只活了三十岁多一点,从开始写作到去世,统共写了十年。但是,就靠那十年的写作,也足够使人惊艳——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批评家鲁迅、胡风、茅盾等都为她的重要作品《生死场》或《呼兰河传》作过序,鲁迅接受记者采访时断言萧红会取代丁玲,正如丁玲取代了冰心一般。这“神”一样的预言延续到了今天。如果泉下有知,萧红和当年的伙伴们会怎么看今天的“红火”?我猜,这不仅会让与她同时代的作家大吃一惊,恐怕连那位贫病交困的女青年自己也会感到意外。因为她写得太少了。可这是事实。这个优秀的作家脱离了她的肉身和时代,一个人突兀而醒目地返回到了我们的文学公共空间。
这位青年女作家为什么这么“红”,又或者,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对这位作家念念不忘?这是一个问题。2011年,萧红诞辰一百周年时,作为年轻一代的萧红研究者,我和翻译家葛浩文先生曾就此进行过深入的讨论。葛先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首席翻译家,他另一个身份是《萧红评传》的作者,此书80年代在大陆出版后成为萧红研究的新起点。谈到当年第一次读到萧红作品的感受,他提到“亲切感”这个词,这使我印象深刻,也引发了我的共鸣。作为读者,我也认为萧红作品有跨越时代和国家民族的那种亲切感——如果你问一个四年级小学生,对《火烧云》那篇课文的看法,他多半会告诉你,他喜欢那文章,因为读起来好玩,有趣,有意思。
什么样的作品才会让不同代际的人产生亲切感?这个作品固然要有时代气息,但也要有脱离具体时代被人阅读的魅力,是历久弥新的魅力。《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写的是作为疏离者的她的战争经验。1930年代,东北沦亡,举国悲愤。作为东北人,萧红当然愿意以书写沦陷故乡的方式表达家国情怀,但她有书写的限度,因为她未曾经历真正的战争,那么,她便只写她看到的。一如孙犁先生所言,“她对国家民族,是有强烈的责任感的。但她不作空洞的政治呼喊,不制造虚假的生活模型。她所写的,都是她乡土的故事。”她写自己的细微感受,不越界,不夸大,不扭捏作态,发自内心和真情。另一部《呼兰河传》也打着时代的烙印,但同时也有脱离那个时代的能力,不讨好,不投机。她并不想在风潮上登高一呼,她真心为时代和民族而歌,但她写她力所能及的。
萧红能打动不同时代、不同年龄的人,也与她天才般的对人世和自然的整体观和理解力有关。那是一种超拔不俗的认识能力。她将人畜不分、天地不仁的人世命名为“生死场”。当我们说起《生死场》马上会想到轮回和混沌;当我们说到《生死场》里民族的濒死时即刻会触到它的伟大和恒长。《呼兰河传》中,我们能体会到她对于大自然的温度,那肥绿的叶子,烧红的云彩和作浪的麦田,那亘苦不变的大泥坑和牛羊都不是点缀或装饰,而是她作品中带有象征意义的光。我们在她那里体会到情感的某个高度时,不是通过激烈碰撞的故事,不是通过戏剧性的人物命运,而只是通过一个女孩子在村子里奔跑,看着牛羊慢慢吃草,听鸟儿歌唱。
萧红从写作开始就在尝试寻找一种整体认识世界的方法。她在试图写出人世存在的“普遍性”。那是什么样的普遍性呢?在《生死场》里是天地不分,生死无常;在《呼兰河传》里则是人与自然唇齿相依、万物皆有灵性、万物自在生长。当然,《呼兰河传》并不是关于故乡的赞美诗,远不是。想念故乡时在严厉审视着故乡的愚昧、封建与令人无法忍受的国民劣根性,书写眷恋和怀念时也带有微妙的讽刺和冷冷的疏离,萧红书写了永远的最复杂意义上的乡愁。
如果说那种对时代的认知、对世界的整体性理解使萧红具有了成为优秀作家的可能,那么她的起笔、行文和表达,则意味着这位作家有属于她自己的风格,这最终确立了她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这是萧红《回忆鲁迅先生》的起笔,起笔即是真率,起笔即是天然,起笔即是深情。怀念的文章写得生动,跳脱,灵性,别具一格,实在让人惊奇。读者们后来发现,鲁迅在萧红文章中某些地方“竟以脾气坏、固执而又刻薄的形象出现”(葛浩文语),但是,这恐怕也正是萧红文笔的魅力。她不是为了光环下的伟大人物而写,而只写生活中可亲可感可敬的人,她要把那个文学教父还原为一个人。
永远不会因为某个写作目的而遗失我们生命中那些“刹那”、不遗失那些被刺目的光环覆盖的“活生生”,萧红因此构建了她天真而富有活力的文字世界。为什么这位女作家如此让人念念不忘?固然与她传奇而短命的一生有关,但终究还是因为她的文字,因为她文字里潜藏着的天赋、勇气、胆识和才华,因为她的写作本身闪耀钻石般的光泽,于是,在她去世四十年后、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人们还是要忍不住大张旗鼓地去谈论她,阅读她。张莉
(来源:天津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