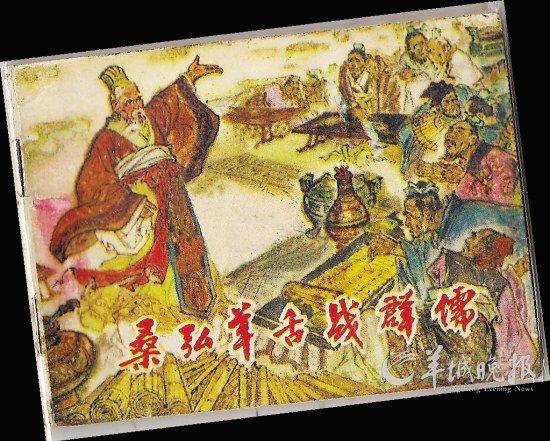
漢昭帝始元六年,桑弘羊代表京官集團,在鹽鐵會議上與60多名“基層代表”就鹽鐵官營、酒類專賣等政策進行激辯。圖為講述鹽鐵會議故事的連環畫封面

唐玄宗大明宮含元殿元日大朝會復原群像(大明宮遺址公園)
中國古代有“兩會”嗎?
那麼,古代中國又是如何表達民意、上交“提案”的呢?
1
古代“兩會”是什麼樣的會議
從制度層面來說,現代“兩會”制度為共和國首創,中國古代是沒有的。但從議事形式來講,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的形式。當然,古代中國的國家議事體系與現代有著本質的區別。
古代是皇帝一個人說了算的“家天下”,皇帝雖自稱天子,其實他是真正的明白人,知道“一個人拍腦袋”的局限性,於是有了“朝參”和“集議”。“朝參”又叫“朝會”,集議也稱“議會”———這便是中國古代的“兩會”制度。
“朝參”由皇帝親自主持,是小范圍的。是百官進入皇帝的辦公大廳(朝廷)參拜皇帝的一種形式,古裝戲中常見的君臣在朝廷上問答的場景,其實就是“朝會”。
進行重要的人事任免和重大的工作安排、典章頒布時,皇帝都會開“朝會”。有資格參加“朝會”的,都是相當於今天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委辦主官,所謂“三公”、“九卿”,最低也得是副廳級的正五品官員。
“朝參”實是一種御前會議或內閣會議,有點類似解放后的最高國務會議,中央工作會議。時間不長,但相對頻繁。到唐代,“朝參”變成了“常參”,每日或隔日舉行,成了制度化。
“集議”則由“三公”或地位相當於“三公”的大臣主持,皇帝一般不參加。集議實際上是應皇帝的要求或同意才開的,規模可大可小,參會者的范圍比朝參復雜。集議通過的議案都是要認真執行的。
2
古代“兩會”代表都是些什麼人
“集議”也分中央和地方,與全國人大和地方人大相似。但與今天“人大”代表都是選舉出來的不同,參加“集議”的人員都是由官方決定和領導推舉,代表中沒有普通群眾。
那麼,古代的“人大”代表都是些什麼人?從史料上來看,主要有四類:
一是相當於今天省部級高官的“二千石”以上大臣才有資格,實為官僚和利益集團的代表﹔
二是“地方代表”,以分封在外、待遇達到一定級別的列侯為主。列侯都是功臣名冑或其后裔,實為貴族和特殊階層的代表,這部分代表是不能參加“朝參”的﹔
三是“專業代表”,主要是列大夫、博士、議郎這些專職諫官。這類代表參政議政能力強,因為都是領俸祿的,也屬“公務員”群體的代表。
另外,在需要時,還會有“基層代表”。漢昭帝時召開“鹽鐵會議”,特別召集60余名地方和基層的代表參會。
這類代表以飽讀詩書、喝過墨水的“賢良”為主,表面看是來自地方和基層,但因為是相當於今天省市一把手的郡國國主和地方富豪推舉出來的,實為學術界和富人的代表。
雖然這些代表並沒有代表性,但其素質要求並不低,要求必須敢說話善表達,有較強的參政議政能力,和稀泥、當會油子,隻會摁表決器和鼓掌的不行。
3
古代“兩會”議案很難一致通過
古代中國的“兩會”很注重民主氣氛,“代表們”敢直抒胸臆,有人甚至敢在朝會上當面指出皇帝的不是。如果“代表”總是投贊成票便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可能會遭到皇帝的訓斥。
在“集議”上,議案也很難“一致通過”,有時還會出現“經年不決”的現象。西漢末年的王莽新朝,一次議會的議題之一是討論並頒布官員的工資制度,結果集議了好幾年,也未能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見。
由於政策遲遲不能出台,導致上自公侯、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資,即所謂“皆不得俸祿”,實在罕見。
古代最著名的一次“集議”是“鹽鐵會議”。會議時間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會上,60余名由相當於今天省市一把手的郡國國主推舉出來的地方和基層代表,與以御史大夫(“三公”之一,相當於副總理)桑弘羊為首的京官集團,進行面對面的激烈辯論。
會議由丞相田千秋主持,重點議題是對漢武帝主政時期國家施政政策的得失,進行討論。地方和基層代表們對鹽鐵官營、平准均輸、酒類專賣、貨幣發行等多項政策提出了尖銳批評,強烈要求廢除之。
桑弘羊深得漢武帝的信任,曾統管中央財政近40年,是這些政策的實際制定者,對“賢能”和“文人”的否定意見不以為然。會議最后經過表決,通過了廢除全國酒類專賣和關內鐵官制度,打破國有公營的壟斷。
4
“提案”影響力與皇帝的好惡
古代共商國是,除了“朝參”和“集議”這樣的“兩會”形式外,還有一種“諫議”制度。所謂“諫”本義就是規勸君主,諫議自然就是給皇帝行為和決策提意見,專挑毛病和不足。
諫議既有會議形式,也可個人約談,有時還會與集議混在一起,但與集議明顯的不同是,諫議多有“提案”。
與“集議”相比,諫議制度在古代中國影響很深,這與皇帝的重視是分不開的。實際上此制度原本就是皇帝提出來的,諫官往往也由皇帝親自挑選和委任。
諫議制度要求拿出提案供皇帝和中央決策時參考,開會時的味道有點兒像今天全國政協會議。諫官也都會積極建言獻策,其所扮演的“民主監督”角色,可說是古代中國的“政協委員”。
西漢中早期皇帝都重視諫議制度的建設,漢武帝劉徹對“政協委員”十分重視,出現了不少出色的諫官。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學”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上交給漢武帝的提案《舉賢良對策三》,可以說是古代中國影響最大的“提案”。
提案的中心觀點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觀點得到了漢武帝的肯定,提案被採納,儒家地位驟升,從此開始左右古代中國人的意識形態。
諫官的權力是皇帝給的,因而皇上想聽時會“納諫”,不想聽時便會“拒諫”。遇到開明的皇帝,諫官便很受用。唐太宗是個開明皇帝,也造就了魏征的“千古名諫”。如遇到隋煬帝,諫官就沒有好日子過,他最后將諫官全部廢除。當然,聽不進“民意”的隋煬帝結局很慘。
5
白居易當“政協委員”最窩囊
實際上,即便皇帝很開明,也很難不被暗箭中傷。如西漢時的賈誼、晁錯遇到的都是明君,他們二人均當過“博士”諫官,提案也都很出名。前者有給漢文帝的“三農”提案《論積貯疏》,后者有給漢景帝的“擴大內需”的經濟提案《論貴粟疏》。
可以說,西漢盛世“文景之治”就是在賈誼、晁錯這些“代表們”的暢所欲言中出現的。但他們的結局都不好,賈誼因建言有功,被漢文帝破格提為太中大夫一年后,便因遭群臣忌恨,貶為長沙王的太傅。
晁錯貴為漢景帝的“智囊”,因上交《削藩策》“提案”,在“七國之亂”中由漢景帝親自下詔,斬殺於西安街頭。
古代諫官中,“政協委員”當得最窩囊的大概是中唐時的著名詩人白居易。白居易於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被唐憲宗李純破格提拔為諫官左拾遺,當上了從八品的“處級干部”。
白居易當時太把自己當一回事了,大事小事都“建言”。唐憲宗要提拔寵臣吐突承璀,他堅決反對,結果被皇帝斥罵為“小臣不遜”,貶為江州司馬,逐出京城。
此后,白居易再也沒有上交提案的機會,隻能寫寫《長恨歌》,在“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中作自我安慰。
宋代以后,諫議制度變成了擺設,元代干脆取消諫院。到明清時,古代中國的“兩會”和諫議制度所散發出的民主精神幾乎不存,明世宗朱厚熜甚至把持不同政見、反對給他生父興獻王朱祐杬上尊號的朝臣當場杖斃16人,另外134人被關進監獄。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