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斯特科,19歲,士兵、死囚,戰爭期間奸殺了23名女子﹔她叫梅加,中年婦女,女兒是23名受害者之一。她把他從行刑的電椅上救下,條件是他要像奴隸一樣服從於她。此刻有什麼比“活”更具誘惑力?他答應了她。話劇《紀念碑》的故事,便這樣開始了。
《紀念碑》是加拿大劇作家考林·魏格納的代表作。1995年該劇在加拿大首演,1996年獲加拿大總督文學獎﹔后由吳朱紅譯成中文,當時的中央實驗話劇院(國家話劇院前身之一)導演?明哲將其搬上舞台,2000年在京首演,2005年再度演出。
今年8月,《紀念碑》復排,這部看似冷門的戰爭題材小劇場話劇迅速成為觀眾認可的“口碑佳作”,不僅場場爆滿,更出現了每場必須加座的場景。8月21日,《紀念碑》受邀參加2013全國小劇場戲劇優秀劇目展演和2013年國家藝術院團演出季,登陸北京國話先鋒劇場。
對人性的探討不會過時
13年前,《紀念碑》的首演不僅讓查明哲牢固樹立了“殘酷戲劇”的風格,也讓當時的觀眾展開了對戰爭、對人性的深入思考和熱烈討論。
開場時,坐在電椅上的斯特科沒有絲毫懺悔之心。他對罪行理直氣壯,把一切視作戰爭的一部分。他著魔般壞笑著說:“打仗時,這種事情可沒人追究。”而梅加為了女兒,為了讓斯特科說出罪行的真相,她隱忍著讓他生,更讓他生不如死——她鞭打他,讓他像牲口一樣干活,割掉了他的一隻耳朵,逼他搬起大石頭砸傷自己的腳,以此教訓他不懂“真話與謊話的區別”。
戰爭制造著各種各樣的廢墟,而建立在廢墟之上的人性,終究是脆弱、扭曲、善變的。作為受害者的梅加,也扮演著加害者的角色。兩顆受傷的心,若能彼此貼近、相互救贖,該是件多慶幸的事。
她請他喝啤酒,送他兔子作禮物,在傷害他之后又替他包扎傷口。斯特科這個曾經的殺戮機器,麻木的心臟開始慢慢復蘇,他感受到疼痛,感受到愛。他回憶起自己犯下的罪行,回憶起每個被他迫害的年輕女孩的模樣,用犯下罪惡的雙手,挖出一具具尸體。梅加用這些女孩的尸體,搭建起一座揭露戰爭真相的紀念碑。
“這部戲,是一次在廢墟上的跋涉,是一次在人性荒原上的跋涉。”查明哲說,13年前《紀念碑》問世帶給了當時的觀眾很多新鮮的價值觀。“那時,我的一位老師很認真地對我說,一定讓我搞清楚故事中的那場戰爭究竟誰是正義的一方。而我想討論的是普遍意義上的戰爭,無論什麼旗幟下的戰爭都是非人道的。而表現戰爭中的人性,也曾經是創作的禁區。但人性又是那麼復雜,在愛的名義下也能殺人。所以,我們以充滿感性的戲劇方式將這些曾經的禁忌赤裸裸地展現出來,自然會引起轟動。”
查明哲說,《紀念碑》就像魯迅評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但要拷問出潔白下的罪惡,還要拷問出罪惡下的潔白。”而對於戰爭的反思、對於人性的探討,不僅在13年后的今天不過時,在以后也不會過時。所以,此次復排查明哲在藝術處理上並沒有做大的改變。“我們依據的還是這個文本,我們的任務就是把這個文本裡深刻的、有價值的、有力量的,甚至是13年后我們發現,當年我們沒有重視的、沒有發現的凸顯出來。”
演員“走不出來”是幸福
《紀念碑》是兩個人的戲,但從13年前首演開始,查明哲便會一次起用4個演員。“《紀念碑》是一出1小時50分鐘的戲,兩個演員幾乎要各自說上55分鐘的台詞,難度可想而知。而且,這兩個角色又是如此復雜,演員不去撕裂自己就無法體驗角色,所以他們在創作上的艱辛可想而知。何況在舞台上,演員們要當著那麼多雙眼睛去撕裂自己、撕裂靈魂,去探究那些甚至是令人不齒、感到羞辱的情感,他們消耗著難以想象的心力與體力。”查明哲說,在13年前的演出中,梅加的角色由張凱麗與徐雷輪流飾演,但徐雷突然生病了,張凱麗一個人連演3場,結果整個人虛脫了。
而正是經歷了痛苦的體驗角色的過程,當年的4位演員段奕宏、邢佳棟、張凱麗與徐雷的表演不僅得到了觀眾的認可,更被譽為表演藝術的范本,成為舞台經典。“成功的代價是,他們進入角色以后可能很難再走出去。這是演員的痛苦,也是他們的幸福,而作為導演,我不會打擾他們的幸福。”查明哲說。
《紀念碑》13年前演出,也在查明哲的兒子查文浩心中埋下了一粒種子。“那時,他隻有9歲,總在排練場裡玩。有一天在家,我和他媽媽正在客廳裡,他躲進我的書房大喊:‘爸爸,你把門打開。’我們把門打開后看見他坐在一個小板凳上,然后開始背誦斯特科那段十幾分鐘的獨白,竟然一字不差。我們都驚呆了。”聽說父親復排《紀念碑》,查文浩主動請纓演出,因為考慮到他的年齡、氣質與斯特科確實接近,查明哲最終同意了。
“演出之前,我只是預判了一下,覺得他能夠完成。現在經過觀眾的檢驗,那些叔叔阿姨對他都還認可,我也基本認可。”作為導演,查明哲是嚴謹的﹔作為父親,他更是嚴格的。所以,他對兒子的表揚異常謹慎。“因為前面的演員有好的創作,他吸收和學習了,所以他才能夠得到這些認可。”
人性遠比我們想象的更復雜
《紀念碑》的尾聲,斯特科乞求梅加的原諒,並向她伸出了手,梅加轉身痛苦地哭嚎,兩個人的手定格在一段看似並不遙遠的距離上。之后,一座挂著23條白色裙子的紀念碑緩緩升起。
這是一個開放式的結局,也是不同於原著的結局。“在原著中,那些女孩的尸體就是紀念碑,但我在讀劇本的時候,一條條象征純潔的白色裙子在我腦海中閃過,所以我決定用這樣的處理。原劇本中,梅加的手朝斯特科不自覺地動了一下,這預示著他們的和解。但我讓梅加轉身,痛苦地嚎叫,讓他們的和解變得更加模棱兩可。我總覺得人類雖然絕望,但是希望和美好依然存在。但這種希望和美好與現實的差距,雖然近在咫尺卻遙不可及。”查明哲說,人性遠比我們想象的更加復雜。(記者 劉 淼)
(來源:中國文化報)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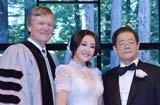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