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 納
她是京劇大師程硯秋的義女,被程硯秋認定為程派“執牛耳者”﹔她不顧勸說,棄醫下海,唱紅了大江南北﹔她改劇本、改唱腔,被誤解為程派的“叛徒”,卻笑納了帶有諷刺意味的“新程派”稱號……如今年逾八旬的京劇名家李世濟,有著傳奇的一生。
近日,由中國政協文史館、中國國家京劇院主辦的“濟世為民·藝術人生——李世濟藝術傳承暨傳記寫作座談會”在京舉行。此次座談會,既是業內同行、弟子傳人及戲迷票友對京劇名家李世濟璀璨藝術人生、精湛表演藝術的一次全面回顧,也標志著李世濟藝術傳記的寫作正式啟動。
11歲得“小程硯秋”之名
1933年5月,李世濟出生在書香門第,祖父曾是清朝官員。一次偶然的機會,她接觸到京劇,並從此結下一生的不解情緣。“我姨在銀行工作,那時候很多銀行的職工都很喜歡京劇,我就愛躲在八仙桌底下聽,也就四五歲吧。結果我姨沒學會,反倒我能一字不差地唱下來。5歲的時候,我已經參加銀行裡的票房演出了,這大概就是緣分吧。”
11歲那年,李世濟在朋友家見到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硯秋。“第一次見面,他就很喜歡我。周圍的人都說我長得很像他,比他親女兒還像,大家就說干脆認作干女兒。第二天,我4點鐘放學到家,程硯秋大師已經在家坐著了,還帶了認干女兒的見面禮,金鐲子、一對銀筷子、兩個銀飯碗。我們是戲迷家庭,我父母非常高興,當時就叫我磕頭,拜干爹,然后確定了父女關系。”
此后,李世濟一直得到程硯秋的親自傳授。“他對我非常寵愛,每天到家來跟我說戲。我們家很講規矩的,他坐沙發,我隻能坐小板凳。但我學得很快、很努力。”程硯秋教戲嚴厲而認真,李世濟學起來也不敢有絲毫懈怠。練唱詞,離牆一尺遠處,對著貼在牆上的宣紙念,直念到口中噴出的熱氣濕了宣紙﹔吊嗓子怕影響到鄰居,就在自家廁所裡架一個酒壇子,對著練,直到頭昏眼花、兩耳轟鳴為止。3個月后,第一出戲《賀后罵殿》學成,第一次演出,李世濟就博得了“小程硯秋”的美名。
一生未能拜程硯秋為師
程硯秋為了使她全面掌握京劇表演藝術,請了芙蓉草、陶玉芝、朱傳茗、王幼卿、李金鴻等名家為李世濟教授身段、表演、武功和昆曲,還請了梅蘭芳教她《貴妃醉酒》、《霸王別姬》。經過10多年的勤學苦練,李世濟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盡管如此,李世濟一直未能拜程硯秋為師,這是她一生的遺憾。她清楚地記得程硯秋反對得很堅決:“看我的子女,哪個是干這行的?我這是愛你呀,戲班可是‘大染缸’。”然而“蓮花出淤泥而不染”,李世濟有自己的堅持。但無論如何,程硯秋始終無動於衷,他深知梨園行的苦,外面,愛的敬的,分外有光﹔內裡,風雨連連,說話都浸透淒涼。
1952年,盡管程硯秋反對她棄醫從藝,李世濟還是毅然決然地從上海第二醫科大學肄業,來到北京自己組建戲班,通過當時的京劇工會進行演出,獲得不錯的反響。
1956年,李世濟進入北京京劇團,作為青年演員的她與馬連良等大師常常合作演出,得到了不少名師指導。
之后,程硯秋和李世濟以及其他一批當時卓有成就的表演藝術家作為新中國的文藝骨干代表被派往莫斯科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臨行前,負責該活動的周恩來無意中得知了李世濟多年來的夙願,向她承諾,等活動結束后他親自做東,為她和程硯秋主持拜師之禮。
那次演出非常成功,但李世濟的等待卻成了空——程硯秋突然病故。“我一生就看到兩個人七竅流血,一個是程老師,一個是我的兒子(李世濟的兒子在2001年因車禍去世)。那時候沒有面巾紙,隻有大手絹,我一點點給他擦。”說著,李世濟哽咽無聲。
京劇唱腔與美聲唱法
1966年,“文革”襲來。戲不能唱了,李世濟下農村、去干校、戴高帽、挂牌子,一度也曾想放棄唱戲,同屋的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就說她,“胡話,遲早是要登台的。”
郭淑珍和李世濟這對患難姐妹,不僅成了生活中的至交,也成了彼此藝術上的老師。“那會兒,我教世濟唱歌,她教我唱戲。我從她那學到了不少東西。我記得我教了她一個花腔女高音的歌《千年鐵樹開了花》,我突然發現,原來還可以這樣吐字歸音啊。唱美聲的有個毛病,經常吐字不清楚。是世濟教會了我把字咬准,還能唱出感情、唱出表現力。”郭淑珍說,這也是她唱好《黃河怨》的秘密。
而李世濟也在潛移默化中,將郭淑珍教給她的美聲唱法融進了她的程派唱腔之中。
流派要隨時代而發展
1979年,《鎖麟囊》在北京公演。這是十年浩劫后,程派劇目首次演出。那一晚的情景讓李世濟記憶猶新——每一段唱腔后面,都有潮水般的掌聲,觀眾的眼淚扑扑簌簌地掉,每個人的心都被韻味十足的程腔程韻幸福地包裹著。
當謝幕的燈光亮起時,盡管早有准備,李世濟還是吃了一驚:滿眼一片白花花的頭發。入目的惆悵,讓她不得不去思索這樣一個問題——“文革”“奪走”了多少雙年輕觀眾的眼睛。
於是,她到青年中間走訪,歌舞廳、電影院,凡是年輕人愛去的地方,她都去過,看他們什麼時候會叫好,問他們喜歡什麼樣的戲曲。很快,她看出了這一代年輕人和老觀眾的區別——他們更張揚,需要更夸張更奔放的藝術,來填滿他們的精神生活。
那京劇該以什麼樣的模樣面對年輕觀眾呢?李世濟想到,一次程硯秋為她說戲,一句“被糾纏,徒想起婚時情景”,由強到弱,對比很大,落腔時借鑒了荀派的唱腔,但完整的面貌仍然是程派。她似乎摸到了前輩藝術的脈絡——戲要貼著人物去演,戲裡要融入時代的氣息。程派藝術,不是呆滯的水,而應是一條繩索,連著過去、現在和未來,朝著更真更美的方向延伸。
於是,她請范鈞宏修改《文姬歸漢》劇本,刪去拖沓瑣碎場﹔請汪曾祺修改《英台抗婚》,吸取越劇特點,刪去了男裝部分,再請他在“報喪”一場加了二黃慢板,整理時保留各式哭頭,加用二黃慢板、二黃中板替代過多的散板以彌補某些不足﹔請楊毓?修改《梅妃》,以新的姿態重現舞台……她把美聲唱法巧妙地糅合於演唱之中,將程腔唱得透亮,一掃以前程派的陰晦而更顯明快,使程派唱腔更加豐富,更加細致,更富有感染力。丈夫唐在炘對伴奏手段進行了大膽的創新與改造,除了京胡、京二胡、月琴這“三大件”外,把笙也加了進去,以烘托人物的性格。
所有這些,她只是想讓舞台上的人物更加有骨有肉,腔裡要有人物,身段、表情都貼著人物去演,而不是木頭人一般地炫耀技巧。她要演活一個人,就得鑽到戲裡去,反復地試驗、探索,找出最能表達戲中人思想感情的動作和唱腔。她不是胡亂增刪,每改一個地方,都要來回推敲,直到找出完美的解決方案﹔也不是一味對著觀眾的胃口,藝術不是取樂人的“玩意兒”,也不是要縛住人的靈魂,而是解放心靈,感受美。
她做到了,明快豐富的唱腔,活靈活現的人物,一下子抓住年輕人的審美趣味。劇場裡,越來越多的黑頭發隨著她走入戲中,入耳酸心時,也會情不自禁落淚。名滿天下,謗亦隨之。有人將她的藝術冠為“新程派”,意為程派的“叛逆者”。李世濟清楚,“新程派”明褒暗貶,卻也坦然接受——她明白,所做的一切並沒有背離程硯秋的精神。她將生命之流涓涓不息匯入程派藝術這條大河,使之變得更寬廣、激蕩。
雖然有著那些無謂的流言與爭鬧,但肯定、熱愛李世濟藝術的人一直支持著她。與她合作了半個世紀的國家京劇院藝術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京劇名家高牧坤說,在近50年的相處中,他深深感受到李世濟對京劇那份發自心底的熱愛。“可以說,她一生的才智、精力、心血都奉獻給了京劇。”
“上世紀80年代初,流行歌曲風靡全國。有老先生說,咱們的李世濟就相當於唱歌的毛阿敏,足見李世濟主演劇目上座率之高和受觀眾喜愛的程度。”高牧坤說,一個演員在舞台上的光彩,取決於演員的藝術造詣。李世濟不僅繼承了程派,更結合自己的嗓音條件,創造了獨特的聲腔藝術。
而李世濟與唐在炘兩人對於程派劇目的改編和創作,也讓高牧坤佩服不已。“由他們二人共同創作的《陳三兩爬堂》一劇中,一段‘家住山東在臨清’的唱段特別精彩,清板接跺板的巧妙設計,極大地突出了樂器的個性音調,將彈撥樂器善於抒情的特色發揮到極致,這是在之前的程派劇目中從未有過的創造。”高牧坤說,當年他和李世濟同台演出,上半場他演《艷陽樓》,下半場她演《陳三兩爬堂》,每唱到這一段,定是滿堂彩。
(來源:中國文化報)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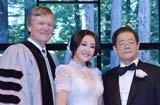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