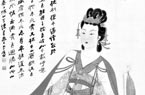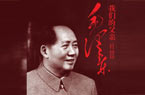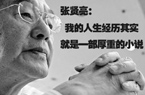|
|
圖為劇照。 |
1936年,飄零在日本的作家蕭紅在書信中寫道:“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閑,經濟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可是在籠子裡過的。”
那時,蕭紅才25歲,但已經在魯迅的幫助下,憑借《生死場》成為知名作家。此后6年,她創作了長篇小說《呼蘭河傳》,若干中短篇小說以及散文,直至病逝在香港聖提士反女校的臨時醫院,年僅31歲。
如今,這位已離開這片土地72年的女作家,依然引人關注。10月1日開始上映的電影《黃金時代》,由獲得四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兩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導演的許鞍華執導,編劇李檣歷時3年完成劇本。兩人從10年前開始策劃,劇組輾轉哈爾濱、上海、武漢、香港等地,歷時近3年,終於用鏡頭寫就了一篇蕩氣回腸的散文。為讓更多觀眾讀懂許鞍華的電影,中國電影資料館先后舉辦許鞍華回顧展及《黃金時代》首映禮。作家蕭紅與導演許鞍華,成為當下的文化熱詞。影片上映前夕,許鞍華導演向本報記者講述了她的電影觀。
蕭紅與文學
蕭紅臨終前說: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就因為自己是個女人。她踉踉蹌蹌、一生流離,她用瘦弱的身軀燃盡生命之火,展開稀疏的羽翼追逐自由之光、文學之美。
記者:作為香港導演,除了《黃金時代》您還拍攝過張愛玲的《半生緣》《傾城之戀》,那一代的作家和文學為何吸引您?
許鞍華:我們在香港念書的人會覺得中國現代文學的正宗是魯迅、巴金、老舍、冰心,他們的文章是被收入教科書的。小學六年級暑假,我在圖書館讀了許多“五四”時期作家的文章,非常喜歡卻並不懂得他們講的那個時代。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讀張愛玲,她所寫的香港與我所知道的香港如此相似,所以陸續拍了兩部電影。
記者:您的作品大多聚焦香港本土甚至社會邊緣人物。與之類似,蕭紅對於文學、愛情乃至人生道路的選擇也是與時代主潮區隔、背離的。您如何評價蕭紅?
許鞍華:電影導演也是某一種作家吧,同為創作者的我很想知道她面對生活、面對創作的心態。我認為,蕭紅是一流的作家,她的作品藝術水准非常高。上世紀70年代時,我第一次讀到《呼蘭河傳》,根本無法接受它的寫作方式,那是如同散文一樣的語言,但在40年之后,我卻讀到了蕭紅的好。
在電影裡,對於蕭紅身上的一些迷局、爭議的部分,我盡量用客觀的態度處理。她的是非對錯,我希望交由觀眾來評判。
記者:對蕭紅的歷史評價很復雜,人們熱衷猜測談論蕭紅的緋聞軼事,雖有哀婉嘆息,卻也夾雜著些微的“輕侮”和“鄙夷”。
許鞍華:蕭紅的一生,就是不斷出走、反抗、漂泊的一生。一開始,出於對父權的反抗,她離家出走。她與蕭軍戀愛但沒有結婚,后來又懷著蕭軍的孩子與端木蕻良結婚,這些事情即便放到現在也是很極端的。在那時,一個女性要脫離男性和家庭獨立是很難的,她在當時受到的壓迫很深,可是,她的內心自由、勇敢,這很了不起。
個人與時代
那個時代,炮火震耳欲聾,人命細若琴弦。魯迅、聶紺弩、蕭紅、蕭軍、端木蕻良、胡風、丁玲……他們用文字抒寫顯現了文化理想與家國情懷。
記者:這部電影描繪了一幅文人眾生相,十幾位響當當的作家悉數登場。那是一個動蕩的時代,一個孕育可能的時代,革命的種子在那時破土而出。那些文人的思想是時代的明燈,閃耀著青春般的色彩,激蕩人心。這是您所向往和倡導的嗎?
許鞍華:不,我拍這部電影並不想教化別人。我隻拍那一代人的生存方式與人際關系,呈現與當代的一些不同,讓觀眾自己去看,自己判斷。因為那時社會動蕩,外在環境封閉而強大,所以人們反抗的目的性更強烈,內在的自由也更強烈。現在時代不一樣了,在很多方面是不斷進步的,所以不能說以前就比現在好。可是,如果以前的一些東西可以繼承下來,也許我們的生活會更好些。這是應該思考的。
記者:《黃金時代》裡有大量的對鏡獨白,這種打破時空界限、讓虛構與真實交錯的敘述方式富有實驗性,對於觀眾也是一種挑戰。
許鞍華:這種方式我以前沒試過,不過我覺得這是這個戲特別的地方。一般電影裡的畫外音,敘述者都是后世的,而敘述時態也是現在的。但這部電影讓劇中人評述,他(她)也許穿的是1932年的衣服,講的卻是10年或20年后的事情,讓人產生超現實的感覺。我們想試驗一下進展中的美學。
記者:想象中文人的生活是比較精神化的,您如何把握到那時那地那些人?譬如,電影裡的魯迅處於生命末端,他慈愛、溫暖,也寂寞、不舍,十分生活化。
許鞍華:我只是把他們的音容笑貌、生活狀態,具體地表現出來。讓觀眾覺得,這些人不是“聽說”中的樣子,脫離肖像感。譬如,魯迅家的取景地就在上海魯迅紀念館隔壁,其構造與魯迅紀念館一模一樣。你走進裡面,就會知道魯迅在哪張桌子寫作、吃茶,屋子的哪個角落擺放了萬年青,這些具體問題弄清楚之后,魯迅的生活方式也便呈現出來了。我始終相信,魯迅不但是公共的魯迅,更是人間的魯迅。
歷史與電影
歷史有太多闡釋的空間,它被虛構、被粉飾、被私人化、被傳奇化,其中不免諸多悖論。電影講述歷史,其意義不在樹立抑或打破偶像,而是透過那些細微的裂縫,追逐歷史的真相與邏輯,讓歷史的光芒照進現實。
記者:“黃金時代”有豐富的解讀空間。不論投身革命,還是堅守文學的本質,那一代作家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黃金時代。那麼,什麼樣的時代可以被稱為“黃金時代”?
許鞍華:很難給出答案。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黃金時代,如果你的靈感、理想能與時代契合那再好不過﹔如果不能,盡力去把不契合的地方改過來,也就接近黃金時代了。
記者:比如電影呢?
許鞍華:從經濟指標來看,中國電影可以說已經進入黃金時代,可是從藝術文化水准來看,可能還沒達到。最近幾年,中國電影市場急速發展,內地電影界也正經歷新的變化。一些青年導演的作品票房很高,卻遭遇不同的評價,我認為這是很自然的情況。任何新事物的出現,一定會產生紛爭,而一個健康的電影市場一定是可以容納多元作品的。一個導演滅亡的先兆就是不能接受別人的批評。但是,不論你做商業片,還是藝術片,首先要認清自己。我們應該多鼓勵一些新人,而不是把他們作為自己競爭的對象。每個人都多做些事情,整個行業自然會變得更好。
記者:您是香港新浪潮電影的代表,又幾十年投入地拍“許鞍華式”的電影,是什麼讓您如此堅持?
許鞍華:現在,我有點排斥人家把我當作一個大導演,當作一個文化符號。在香港,因為年紀大了,人家頒給我一個終身成就獎,在內地,人們對我也是過譽了。這些過度的贊美會把你個人看得比作品更重要。我習慣了做幕后,不喜歡跑到台前去宣揚我個人怎樣,不論幸福還是痛苦,因為從事這一行,忍受痛苦是理所當然的,也沒有什麼值得稱頌的地方。對於作品,也不必稱頌。因為,電影跟觀眾是平等交流,如果觀眾喜歡,內心有共鳴,就足夠了,沒必要成為粉絲和偶像的關系。
記者:您希望與觀眾建立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一樣的關系?
許鞍華:對。就像看待《黃金時代》裡的那些文人,不要過分神化。
《 人民日報 》( 2014年10月09日 24 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