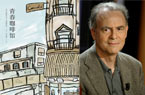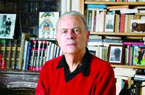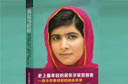|
|
制圖:宋 嵩 |
“我的詩帶著我的體溫和氣息,如同身體的一部分”
宿舍、木板、砂石、網吧、煙卷、鍵盤,流浪,還有詩。“我已不記得寫的第一首詩是什麼了。早些年流浪的時候,在工地的木板上,在工廠的集體宿舍,在公共廣場,隨寫隨丟。”47歲的郭金牛大口吞吐著,裊裊的煙霧拂過他的面頰。離開家鄉湖北的20年外省生活,他的汗水、眼淚,他的體溫和氣息,留在了他所經歷的每一條街道,每一家工廠,一磚一瓦一砂石。“以及青蔥歲月,野草一樣的年華。我的這些詩歌,記錄著我,走到生活的深處,摸到生命的痛處。”
他說的如此不經意,卻又句句成篇。正如他2012年在網吧不經意在論壇上貼出自己的一組詩歌,后來,牽引他從一個又一個工棚,一間又一間出租屋,走向了第四十四屆鹿特丹國際詩歌節,國際華文詩歌獎,首屆中國金迪詩歌獎。瑞士、德國的多家知名報刊刊發他的詩作,來到深圳對他進行專訪。他的詩集《紙上還鄉》,今年8月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帶著那一抹憂郁的深藍色封面,華麗亮相上海國際書展。
1993年,郭金牛離開家鄉,開始了他在深圳、東莞長達20余年的打工生涯。20多年間,中國有數以億計的年輕人,像郭金牛一樣,從農村涌入城市,難舍故土,卻又不得不投身城市的鋼筋水泥間。但是,他們當中隻有極少數人,像郭金牛一樣,把自己的經驗化為詩歌,化為紙上的曲折還鄉之路。
流浪,對於郭金牛,既是生活上的漂泊,也是一種詩意的浪子情懷。住過工地,干過搬運,擺過地攤,也在工廠管過倉庫。郭金牛說,他以前的詩歌是隨寫隨丟的,直到近幾年生活穩定,作品才慢慢得以存留。大多數時候,郭金牛喜歡在網吧一邊抽煙,一邊碼字。有的詩一氣呵成,直抒快意。有的詩則完全相反,眾裡尋“她”,愁腸百結。但郭金牛愛他的詩,“我的詩歌,忠實於我的內心。如果說我沒能按照內心去獲得詩意的棲居,但是,我遵照了我的內心去搬運漢字。這也是我最為得意的事情。”郭金牛喜歡自己的每一首詩,“她們取自我的肋骨,帶著我的體溫和氣息,如同我身體的一部分。”
“我不能預見未來,我隻注重當下,活在當下”
郭金牛這樣寫離鄉的少年:不安/比走動的火車/快上一步/少年/沉默/睡著的語言/心中的一塊石頭/向前滾動/少年/記住了母親格言/井水/和深埋的隱憂。
他這樣寫打工生活:這是我們的江湖/一間工棚/猶似瘦西籬/住著七個省/七八種方言:石頭,剪刀,布/七八瓶白酒:38°,43°,54°/七八斤鄉愁:東倒西歪/每張臉,養育蚊子,七八隻。
詩人梁平在《良好的氣節與風范》一文這樣評價郭金牛的詩:“既沒有波德萊爾那樣偏執的‘惡’,也不是飛機、高鐵、樓堂館所和燈紅酒綠的城市浮華外表,而是從城市人的精神向度上在雕刻標記。”
郭金牛被稱為農民工詩人。甚至不少人覺得,郭金牛的農民工身份和經歷,容易讓他靠題材討巧。而他對文字強大的駕馭能力和字裡行間的真性情卻往往被忽略。但在郭金牛的世界裡,“底層”“農民工”不是商標,而是思想。誰能鑽透自身的處境,觸及存在之根,誰就能構建一個“底層”。他常說,詩人唯一的身份識別就是詩歌,頭銜並不重要。“怎麼稱呼我,對詩歌品質既沒有提高也不會損壞。我寫詩的時候,我就是一個純粹的詩人。在我干活的時候,我就是一個地道的農民工。”
“我們每個人都在底層。能否意識到這個底層,寫出這個底層,且寫出它的深與廣,則看一個人的能力。”詩人楊煉說,郭金牛訴苦,訴得痛徹心肺。但同時,他寫出的“底層”,卻絕不卑賤乞憐。相反,從這些詩中,能夠讀出高貴、精彩、講究和美。“獨絕的詩思,輕靈的節奏,艷冶的字句,甚至匠心獨運的標點,在把墜入深淵,點化成一條超越之途。這些詩,是重和輕的絕妙組合。什麼是中國文化的創造性轉型?復雜嗎?難嗎?失望嗎?沒必要吧?請看郭金牛的啟示:中國農民工,藏龍臥虎!”
這位被他稱為鄰家大哥的詩人楊煉,對郭金牛的影響無疑是深刻的。2012年8月,郭金牛在論壇上第一次貼上自己的詩歌,就得到了楊煉的認真回帖和評點。那是第一次有詩人對郭金牛的詩作出評點。他的詩歌書寫,第一次得到了來自詩歌外部的力量。此后,郭金牛頻頻在論壇貼詩讀詩,且寫且讀且評,漸漸“混入”詩人圈子並受到關注。
2013年6月,楊煉與青年評論家秦曉宇推薦郭金牛的詩作《紙上還鄉》參加了第四十四屆鹿特丹國際詩歌節。郭金牛作品引起了詩歌節主席巴斯·科沃特曼注意。2013年9月26日,郭金牛詩集《紙上還鄉》獲得了國際華文詩歌獎。巴斯·科沃特曼來到中國,在北京大學的頒獎典禮上,給郭金牛頒發了獎杯。
同樣,也是這位鄰家大哥和秦曉宇的大力推薦,使《紙上還鄉》得以順利出版。“我自己從來沒有想到過要出版詩集,自費出版於我是一種經濟負擔,我不想為詩所‘累’。”目前,郭金牛的詩作已被翻譯成英語、德語、捷克語、荷蘭語等多種語言,並通過楊煉的國際友人,陸續譯至海外。
現在的郭金牛,在深圳龍華流動人口與出租屋綜管所做登記服務工作。“我不規劃未來,未來屬於未來。我也不能預見未來,我隻注重當下,活在當下。”郭金牛說。
《 人民日報 》( 2014年10月15日 22 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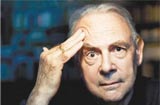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