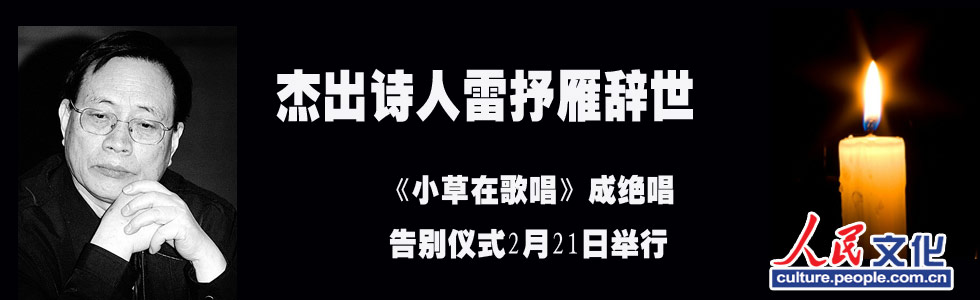編者按:我國當代杰出詩人、作家雷抒雁,於2013年2月14日凌晨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1歲。雷抒雁先生生前曾在幾次訪談中談到他對詩歌、對人生的一些理解與思考。訪談經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牛宏寶教授整理輯錄,人民網陸續發表。
雷抒雁詩話之五:寫詩是一種手藝
10. 我非常重視入詩的方式。如果一件事情不能從基本生活經驗上打動我,就很難進入我的詩。我對政治事件也是這樣考量的。雖然我們這一代人,受到“文革”的影響很大,在接受知識方面,也損失了很多。但不見得比“文革”后成長起來的人差,他們受到經濟的傷害,也同樣大。我們這代人的思想,受到“左翼文學”的影響,革命文學的影響,還有蘇俄文學的影響。這使我們非常重視詩的品格,文學的品格。這其中第一個是思想。總是想做“五四”精神的繼承者,做精神的啟蒙者或者張揚者,尋找我們生活中的精神力量。這是我們這一代人很重要的方面。我們覺得詩是給人力量的,覺得詩是最有力量的。即使感受到自然的方面,也是想到思想的方面,尋找到提升思想的東西。另一方面,那麼在語言上,很重視語言成色上的剛性,使語言有一種剛性的色彩,像石頭,像鋼鐵,而不是柔軟的,不是嫵媚的,或者脂粉色很重的,甚至骯臟的。我覺得我的詩的語言自始至終都很典雅。這也是有評論者給我說的。我說我不僅在詩的語言上如此,我在散文上也是如此。我在每個詞的推敲上,不會使它口水化,或者使它變得雕琢晦澀。再有,就是我對詩,對文學的溝通性的追求。我曾經寫過一首小詩,是說在公共汽車上,有人踩了我的腳,他說了聲謝謝。我就非常感動。我們的一生中有多少人踩了你,但沒有人說謝字。今天,有人踩了你的腳,說了謝謝,你感覺很滿足。有一個農民,到了城裡,他伸出手。就有人在他的手裡放了一塊錢,那農民說:我不要你的錢。我隻想和你握握手。手伸出來,不是為了要錢,而是為了友善。這是我所渴望的。我覺得還有一點,就是我們這代人,總是把文學,把文字看得很神聖,很高貴。就我本人來說,生活一直比較平穩。生活雖然不富有,但很平穩。所以,我不會降低對文學的要求,不會為了物質而去從事文學。所以,我不會降低對詩的品質的追求。我寫詩仍然是手寫,簡單的手工操作。就像一個老字號,做驢打滾的時候,做得很精細,做的也不多,生怕對不起顧客。而別人已經在批量生產了。我會把詞語、句子,放在思想的戥子上稱來稱去。所以,不會為了錢,去寫作。當然,這裡面有一種被視為落伍的、老舊的文學觀念。我始終認為,寫詩是一種手藝。
雷抒雁詩話之六:寫詩是不斷和自己的狹隘性做斗爭
11.人是一代代成長起來的,接受的教育、閱讀的范圍、經歷的生活是不一樣的。 一代代對文學的理解也是有差異的。但有一個最根本的東西,詩的東西,就是要使讀者接受。我欣賞高爾基的觀點,他說:我不懂詩歌這派那派,隻知道詩歌有兩種:好的和不好的。我覺得詩是很博大、很飄忽的東西,沒有任何人能說他已經得到了詩,我們隻能說我們在逼近詩,隻要你寫得感染了人,打動了人,就是好詩。
我們在寫詩的過程中,是我們不斷和自己的狹隘性做斗爭的過程。一個好的詩人能夠 接受各種風格的詩。要善於寬容和容納,我認為這是寫詩人必備的一種精神。既要向外國學習,又要向古典學習,同時要向民歌學習,向各種流派學習,這樣才能壯大自己。挑食的孩子長不大。稍微成熟的詩人就應該冷靜地、清醒地去學習,並堅持自己。不是說潮流來了就跟著潮流走。好的詩能從中看出各種傳統。風格即人, 如果你這個人是飄忽變化拿不准的,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人是執著的,對生活的理解是深刻的,詩不管怎麼變化,裡邊都會有一種沉重的東西。評論杜甫,人們用 “沉郁頓挫”四個字就概括了他的一生。杜甫也有寫歡樂的,但他的主要風格、代表他這個人的是“沉郁頓挫”。
12.我發現自己的詩裡邊有很多抑郁,就是比較沉重的東西。這是可能的。因為我覺得從寫張志新開始,到地震中的逝者,到對屈原這樣歷史人物的把握,都有一種沉重在詩裡。新世紀的前10年並沒有讓我的憂郁消失。在人類時空的坐標上,去者熙熙,來者攘攘,但我們精神上的孤獨,大約是永恆的。然而我們還是要前進的,正如我的一首詩所寫,《前方,前方,依然是太陽》。我覺得生活給我們的東西是很多的,關鍵是我們怎麼去理解生活。我還是篤信孔子所說的微言大義,詩是需要微言大義的,如果沒有大義,那個詩還是很輕的。要在詩裡邊賦予一些豐滿凝重的東西,讓詩凝練,有分量、有啟迪。
雷抒雁詩話之七:我在家鄉的根基上找到了真正的詩
13.我們這一代人傳統文化的底子,是在我們的基因裡頭。雖然,我們與傳統文化的關系,沒有老一代那麼深厚,但也沒有年輕一代那麼淺薄。我是1962年上大學的。這之前,當然政治運動很多。但1962年到“文革”前,恰恰有一個短暫的安靜。杜甫研究專家傅庚生給我們講古詩,讓我們不要戴著“白手套”讀,要脫掉“白手套”。就是不要把傳統文學都僅僅當作封資修。我對詩詞意境的把握,對入詩方式的探究,都與這個傳統有關。我是寫新詩的,不寫律詩。但我對詩的感悟,從傳統詩詞方面,獲得了最直接的敏感。
14.我的詩都很簡潔,我不會把詩寫得很拉雜。有兩種情況,一種就是像郭沫若那樣狂?式的,一種是西方詩中那種情感鋪陳的。這兩種情況,都很容易拉雜。另一種東西,就是我們古代詩詞的,它很簡潔,總是留下很大的空間。這是我從我們傳統那裡學到的。甚至包括宋詞、元曲那種語言和運思,都是簡潔的。我覺得我們過去講對古典詩詞的繼承,過多注重平仄、韻律上,而忽略了它的韻致和簡潔﹔看到了格律,而忘記了詩。除了簡潔,我從傳統詩詞中獲得最多的就是韻致。譬如,我寫《九月,雁與菊》,那是懷念黎煥頤的。“總是九月/又是九月!//一雁飛過/正秋老如歌/”這一下就是很大的背景。我想造成陳子昂《登幽州台歌》的那種蒼茫的空闊。下來,“往事如塵/都從肩頭抖落//一轉眼/天開地闊//我來祭秋/一片黃花,明如燭火//明年,雁從去處還來/能否捎幾行新詩給我”。
用詩人艾青的話說,就是扣動扳機容易,打中十環難。這就是怎樣直擊十環的問題,也就是准確的問題。寫詩就是尋找十環。你說的與秦文化的關系,這就是陝西地域文化的性格所造成的東西:語言上的不遮不攔,尤其是一種申訴性的東西。它要的是一種深刻和尖利,就像雕刻一樣,寧用鑿子、錘子鍛打,也不要蝕刻,一種化學腐蝕的辦法。鍛打的東西,雖然粗礪一些,但更有力量。
15.西方的一位作家說,文學就是一種記憶。應該說,我對關中農村的生活實在是太熟悉了。關中農村的所有農活,我都能干,種地、收麥、摞草垛。這些東西都變成了我根深蒂固的記憶,它們是我所有經驗的土壤和胚胎。我以后的城市生活,都是在這個胚胎上滋生和植根的。這其中,不僅奠定了我對土地、對鄉村的熱愛,也有積澱在幾千年鄉村文化的智慧、看問題的方式的智慧在我這裡的傳承。譬如,到冬天落霜了,地面白花花一片,你的腳踩在上面,發出的那種喀嚓喀嚓的聲音,也就有特別的感覺,“人跡板橋霜”的感覺就出來了。譬如,小時候我隨我母親步行去商洛舅家,沿途過藍田、翻秦嶺,看到山、田園、樹木。等到我上中學后,我把王維、韓愈、白居易的許多詩抄下來,都喚起了這些早年的記憶,覺得這些詩與我的生活,與我周圍的世界,非常親近。仿佛小時候的生活把那些古代的詩在我的眼前復活了。路邊的小溪,岩邊的古鬆,樹上挂的藤蔓,都復活了那些詩句。我也正是通過這些情景記憶進入詩的。青少年的記憶是詩發芽、萌生的根基。我現在有時候,在別的地方看到某種鄉村的情景,也會不由自主地喚起我對關中農村的生活想象,聯想起我青少年生活情景的某種深沉綿長的記憶。我在這些根基上找到了真正的詩。
最新動態: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