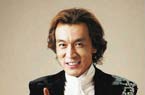喜歡古典音樂的人,不會不知道馬勒。喜歡馬勒的人,不會不知道《大地之歌》。馬勒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著名的浪漫主義作曲家,他的《大地之歌》根據中國唐詩創作而成,副標題為“一個男高音及一個女低音(或男中音)聲部與管弦樂的交響曲”,在全世界范圍都享有盛譽。1998年,德國交響樂團帶著《大地之歌》來中國尋根。此后,很多學者爭相破解隱藏其中的“唐詩之謎”。最近,一位荷蘭樂迷的求助信引起了我對馬勒及《大地之歌》的關注和興趣。
荷蘭人楊·維爾特曼是馬勒《大地之歌》的熱情擁躉。他收藏的一個《大地之歌》早期黑膠唱片集中包含一本小冊子,比較詳細地解釋了《大地之歌》中的音樂和唱詞,並提供了《大地之歌》脫胎於唐詩的直接例証,即翻譯家漢斯·貝特格的唐詩集《中國笛子》的英文版。引起維爾特曼注意的是小冊子中的一幅插畫,特別是落款“雪侯”的題詩。雖然不懂中文,但他隱約覺得,這或許可以幫助了解《大地之歌》的唱詞。
帶有神秘字眼的配畫詩
插畫是兩個仕女並肩讀書的場景,題詩曰:“閨中兩個女相如,長伴牙簽比蠹魚。偕□豐華消□恨,美人顏色古人書。”落款是“雪侯辛未冬日”。這首詩的意思不難理解,描繪了兩位美女閨蜜的讀書場景。“牙簽”原指牙骨制成的簽牌,系在書卷上作為標識以便翻檢,后泛指書籍。“蠹魚”即書虫,喻美女愛書。只是詩中的“□”令人費解。查《說文解字》,知是“得”的異體字,第三句就是“偕得豐華消得恨”。但是也有人認為,第三句是“偕首豐華消首恨”。
至於“雪侯”,我也簡單考証了一下,應是趙士鴻(1879—1954)。又查,該詩並非原詩。在袁枚的《小倉山房詩集》卷十八中,有一首《題永岩雙美讀書圖》。詩曰:“侍兒兩個女相如,管領牙簽逐蠹魚。供得年華消得恨,美人顏色古人書。”兩首詩雖然只是幾個字眼上的不同,但作者的觀察角度和心理感受大相徑庭。袁枚的詩似是寫自己的現實生活,而雪侯則是偷用袁詩,附庸風雅又怕別人譏諷,假裝是在贊嘆識得詩書的閨中美少女。
馬勒的《大地之歌》源自唐詩,但小冊子中為什麼配這樣一幅插畫?畫中題詩又非唐詩,其原因何在?我想,可能是唱片出版商想當然地認為這是美女題材的詩歌,而《大地之歌》的第四樂章就題為“美女”。
《大地之歌》是一曲生命頌
在維爾特曼提供的小冊子復印件中,可以了解到馬勒創作《大地之歌》的更多背景。只是對馬勒的作品認識膚淺的人,通常會把他想象為一個專門反省內心惡魔的人、一個神經質般揭示自身折磨的人。實際上,馬勒是一個不斷工作和抗爭的人、一個積極而熱情的人——這在音樂家裡是不多見的。在維也納或漢堡的演出季一結束,馬勒就會前往斯坦因巴赫或麥爾尼格,狂熱地開始新的創作。而一旦完成或階段性完成一部作品,馬勒都會沖向鄉野,長時間徒步行走或自行車騎行。可以說,親近大自然是他獲得創作靈感的重要途徑。
1907年的夏天是馬勒人生中最難熬的一個階段,各種打擊接踵而來——愛女瑪麗亞不幸夭折,他本人不得不離開付出10年青春的維也納歌劇院,又被診斷為嚴重心臟病。這些打擊消耗了他的能量和意志。由於極度悲傷,馬勒不能進行任何創作。1908年,馬勒來到意大利的多比亞科。在給布魯諾·沃爾特的信中寫道:“在我生命的終點,我必須像初學者一樣重新活過,學習如何承受……發現自己的道路,克服孤獨的恐懼。”
患病的馬勒逐漸學會用另一種方式觀察生活,可能比以前還要深刻、強烈,正如很多即將離世的人珍愛生命一樣。在森林中的小木屋裡,他日復一日地冥想和工作,開始思考那些指導和滋養他整個創作生涯的重大問題、生死的意義以及人死以后的歸宿。馬勒岳父的朋友提奧巴特·波拉克送給馬勒一本漢斯·貝特格翻譯的詩集《中國笛子》。這些中國詩歌或歌唱人內心的孤獨,或感嘆塵世間的喧囂,極大地激發了馬勒的創作靈感,讓他完成了人生告別之作,也是其最具個性化的作品。
最初,馬勒只是計劃選取幾首詩,寫一個有管弦樂伴奏的簡單組曲而已,但這個作品在他的手裡一天天變得龐大。他先是寫了管弦樂插曲,最終又變成名副其實的交響樂。西方許多著名作曲家是在寫完《第九交響曲》后離世的,比如貝多芬、德沃夏克等。據說,馬勒寫完《第八交響曲》之后,感到心事重重,生怕逃脫不了這種宿命。於是,他索性將下一部交響作品命名為《大地之歌》。不過,馬勒后來還是創作了《第九交響曲》,並留下了未完成的《第十交響曲》。
《大地之歌》的唐詩之謎
馬勒從《中國笛子》中挑選了7首德譯唐詩,譜寫了《大地之歌》。《中國笛子》不是直接翻譯自中文,而是根據漢斯·海爾曼的德譯《中國抒情詩》、朱迪斯·戈謝的法文版《玉書》和赫維·聖丹尼斯的法譯《唐詩》等改寫的。中外文詩歌互譯很難,何況涉及到多個語種的互譯。不難想象,發現《大地之歌》確切唐詩出處的難度之大。
目前,中外學者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第一樂章《愁世的飲酒歌》是李白的《悲歌行》,第四樂章《美女》是李白的《採蓮曲》,第五樂章《春天裡的醉漢》是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第六樂章《告別》選自孟浩然的《宿業師山房待丁大不至》和王維的《送別》。第二樂章《寒秋孤影》和第三樂章《青春》存在爭議,尚無定論。有關這兩首唐詩的“懸案”一度被稱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謎”。經過一番推論、考証和研究,目前,有人認為,第二樂章《寒秋孤影》應是錢起的《效古秋夜長》,第三樂章《青春》則可能是李白的《宴陶家亭子》、《姑孰亭序》或《贈宣州靈源寺仲濬公》——這在維基解密關於《大地之歌》的詞條中也得到了採用。
馬勒的《大地之歌》以及由此引發的關於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說明歐洲人是多麼地向往中國燦爛的傳統文化。雖然馬勒沒有直接採用中國的音樂語匯進行創作,但他所追求的唐詩意境和情調更能表現古代中國文人的氣質。這些優美的唐詩跨越了地域、時代和民族,同20世紀壯麗的交響音樂融為了一體,奏出中外文化交流的美麗樂章。(楊曉龍)
(來源:中國文化報)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