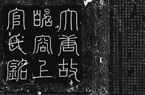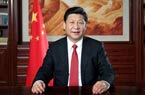市民手持鮮花和李梓生平介紹早早來到現場,送她最后一程。 蔣迪雯 攝
“我只是想告訴朋友、同事這個消息,沒想到一下子有那麼多網站轉載,那麼多網友留言……”昨天下午,上海各界送別配音表演藝術家李梓,第一個向觀眾發布李梓病逝消息的上譯廠導演、演員曹雷這樣感慨。“這個聲音,是一個時代的聲音印記。”告別廳裡,李梓配音的影片《簡·愛》、《葉塞尼亞》等片段循環播放,曹雷的“沒想到”正是觀眾對於李梓所代表的配音黃金時代的不舍告別。
“聽著她的聲音成長、戀愛、選擇職業……”
“高調低調調調繪盡世態,女聲童聲聲聲留住人間。”李梓在四十多年的配音生涯中,用聲音塑造了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1954年,她第一次配音的是一部兒童片《我們街上的足球隊》。為了把孩子的語調、語氣模仿得惟妙惟肖,她就和上影宿舍樓的孩子們打成一片,一起踢球,一起吵鬧,有時還故意挑起事端,和孩子們爭得面紅耳赤,觀察孩子們在各種情緒下的語音語調。年近五旬,她為西德故事片《英俊少年》中的海因切配音,把一個性格開朗、活潑、機靈、勇敢的13歲少年刻畫得維妙維肖。她的簡·愛,她的艾斯美拉達、她的葉塞尼亞……都是觀眾難以忘卻的聲音形象。
“聽著她的聲音成長、戀愛,聽著她的聲音,選擇了自己的職業和興趣……”13時不到,距離告別式還有1個多小時,年屆退休之年的楊子在告別大廳外徘徊,手中提著的袋子叮鈴作響。袋子裡是一條吉普賽風格的頭巾,紅紗上的金色絲線和鈴鐺反射出冬日久違的太陽光線。“《葉塞尼亞》、《音樂之聲》我看了一百多遍。那時十八九歲,我決定要學跳舞,后來,真成了專業舞蹈演員。”把自己稱為李梓“音”迷的楊子紅了眼眶,“我叔叔在上影廠工作,小時候偶爾會去串門,也許在院子裡遇到過李梓老師,但我隻‘認’得她的聲音。‘當兵的,你不等我了?你不守信用。’”剛背起台詞,周圍已是一片應和聲。
“在我們看不到她的地方,不知花了多少時間”
比李梓小整10歲的曹雷說,“不可重復的時代造就了上譯廠的輝煌,一批好演員的登台成就了上譯廠的品牌。李梓正是那個輝煌時代我們的當家花旦。”
“1960年代中,我還是個高中生,因為一部前蘇聯影片《白夜》,下定決心從事配音這一行。影片的主角是‘夢想者’,而我也在做夢。模仿片中男主角的台詞,我向想象中的女主角娜斯金卡發問。就在那個深夜,我堅定了自己的夢想。《白夜》裡,‘夢想者’的聲音是邱岳峰,娜斯金卡正是李梓。”憶起冥冥中的緣分,童自榮音調低沉,“1973年,我正式進入上譯廠,之后數年,我們這批新人漸漸挑起大梁,李梓老師等前輩當起綠葉,更多地配次要角色,我們正面對手戲的合作不多。但我永遠忘不掉,1978年我首次配主角的美國科幻片《未來世界》,李梓老師和我搭戲,因為我經驗不足,配了一條又一條,李梓老師陪著我,我達到要求的那一條,一定比她的最佳狀態遜色了……李梓老師是我心目中配音 ‘女一號’,她為人低調,很少有聲響,一站到話筒前總是發揮穩定。我就明白了,她的功課都是在家裡做的,在我們看不到她的地方,不知花了多少時間和精力。”
“我們希望也相信,未來會有這樣一天”
《簡·愛》的主題音樂中,排成長隊的觀眾緩步向前,一鞠躬、獻上一縷馨香。每一位走出告別廳的上譯廠老演員,李梓的同事、后輩,幾乎又都被觀眾圍住。淹沒在人群中的童自榮被迎到一張小桌前為觀眾簽名,曹雷在資深影迷的收藏裡看到了曾有雜志刊登過的她的結婚相片……熙攘人群裡,上譯廠的“80后”演員吳磊、黃鶯——“哈利·波特”、“赫敏”並沒有被認出。
“市場環境和時代條件改變了,我們不以成為明星作為職業追求,我對自己的要求是對得起觀眾的期待,對得起前輩創下的品牌。上譯廠品牌存在的價值就是質量,我們要做的是傳承和延續前輩的藝術傳統和語言的魅力。”1982年出生的吳磊20歲從上戲表演系考入上譯廠,是新一代中最早挑起大梁的。吳磊介紹,如今為進口片配音,要求配音者的聲線與原聲更接近,因為觀眾可以看到原聲版,希望配音效果不讓他們覺得太跳戲,這是不同於過去時代之處。
“市場經濟沖擊下,配音的現狀低落了。但還有很多年輕人迷戀配音、熱愛這份事業,他們也有他們的無奈之處。”童自榮這樣寄語,“配音的陣地需要重視,要重建一支優秀的隊伍。我們希望,也相信,未來會有這樣一天……” ■本報記者 施晨露
(來源:解放日報)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