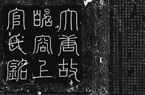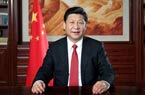伏生授經圖
最近上演的話劇《伏生》有許多亮點,如摒棄了非白即黑的以功過是非評定人物的傳統手法,而是通過客觀的歷史文化背景、學術思想背景來再現人格與行為,演繹矛盾與沖突。另,李斯有一句台詞也值得注意,他說:“我燒的不僅是儒家,燒的是諸子百家,為的是讓秦朝的文化光耀千秋,讓法家思想發揚光大”。這句話顯示了主創方對“焚書坑儒”事件的獨創性解讀。
肚裡藏書,或有據可依
伏生其人其事,《史記·儒林列傳》裡有介紹。伏生,濟南人,曾做過秦朝博士。據清末學者陳蜚聲考証,他生於公元前260年,卒於公元前161年,享年99歲。這說法不一定可靠,因為涉及伏生的直接歷史資料太少。但是基本的事跡還是清楚的,如“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注意,並非肚裡藏書),后來因戰亂流亡於齊魯之間課徒為生。漢文帝初期,朝廷征集散佚的儒家典籍,伏生遂口授《尚書》二十九篇,由太常掌故晁錯用隸書筆錄。
漢代隸書,在當時相當於今天通行的規范打印體,主要是便於認識和閱讀,所以又稱為“今文”。用隸書謄錄的《尚書》稱為今文《尚書》。伏生,原名叫伏勝。“生”,在古代與“子”、“夫子”同意,都是對飽學之士的尊稱,如同今天的“老師”或“先生”。比如孔丘,他的弟子及后世讀書人尊稱他為“子”﹔李白在《將進酒》一詩中提到的岑夫子、丹丘生等等,都是此類意思。
既然是藏書於壁,又該如何理解劇中的“肚裡藏書”情節呢?一個聰明的擦邊球而已。竊以為,倒不是真的把肚子剖開藏書於內,而是伏生通過多年苦讀,早已將《尚書》背熟悟透在肚子裡了,他自己就是一本活《尚書》。隻要他個體生命不消亡,文化堅守的使命就可以完成。
如今濟南一帶還流傳著關於他刻苦學習的故事,說他曾把自己關在一個陰暗潮濕的石屋裡,腰部纏上繩子,每讀一遍《尚書》就打個結,以至80尺長的繩子都打滿了結。如果傳說屬實,那麼肚裡藏書就有依據。
與李斯斗法,不太可能發生的故事
秦漢時期,黃河三角洲出現了兩位重要人物,一是茅焦,一是伏生。茅焦臨湯鑊而不懼,直面秦始皇淫威,凜然諫諍,終致始皇感悟,拜為上卿,賢名遠播。與之相比,伏生在當時並無高行令名,只是70名博士之一。
博士,是秦王朝設置的顧問之類的閑職,可議政,不可參政,沒有品級,也沒有具體的權責。也就是說,作為一名普通顧問的伏生,與丞相李斯,在政治地位上是不對等的。伏生或有一定的話語權,但是,倘若真的如該劇所設定的與李斯是一對公開斗法的“冤家”的話,僅憑區區話語權是遠遠不夠的。大家想想王安石與司馬光、劉墉與和珅之間的爭斗,也就明白了。李斯步步為營,伏生棋高一著,這樣的斗法故事,在當時不可能發生。
焚書坑儒,是李斯為獨尊法家而建議秦始皇推行的一項國策,有詔令為証:“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隨后諸生連相告引,460余人皆坑之咸陽。在天下為之怵惕的嚴酷形勢下,文化思想之交鋒,則是必然會發生的事實。
伏生是在朝博士,可能因此幸免於難,有了壁藏《尚書》的機會。然后流亡他鄉,典籍得以保存,李斯“力撼法家”的圖謀破產。這大概才是他們之間的真正斗法,文化大圍剿與大逃亡,僅此而已。
獨藏《尚書》,一代宗師的眼光
正如該劇導演王曉鷹所說的那樣,“當他(伏生)把自己的生命同書籍融為一起的時候,他自己都會始料未及遇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果他的生命遇到威脅,那他該怎麼辦?”這句話還凸顯出該劇疏忽的另外一個問題:先秦諸子百家典籍甚多,可謂汗牛充棟,伏生為何隻選擇《尚書》而藏而傳?
要弄清楚這個問題,首先要明了《尚書》是本什麼書。“尚”是上古的意思,“書”是指書寫在竹帛上的歷史記載,所以“尚書”即是指“上古的史書”,主要記載了商、周兩代統治者的一些講話記錄,其中也包括春秋戰國時代根據部分往古材料添加的堯舜禹的文獻匯編,如《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等等。伏生獨藏《尚書》,之后又獨傳《尚書》,原因或在於天下情勢之變化,比較各學派的優劣高下,擇有用、實用者藏而傳之。
當時秦始皇滅六國,並吞八荒勢如破竹。在這種大勢面前,孫子“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想發揮普世價值,難,難,難﹔老庄“小國寡民”、“無為而治”等思想,早在戰國時代即已“落伍”﹔墨家“非攻”、“尚儉”的理念此時也與潮流格格不入﹔名家“白馬非馬”的邏輯很難對現實社會產生實質性影響﹔法家的嚴刑峻法則與伏生的家學(儒學)傳統與人生理想相隔甚遠。
也就是說,藏儒家的書,必然是伏生的首選。“古文”雖難,卻難以阻止伏生對《尚書》的探索精研,“堯典”、“舜典”、“大禹謨”的學問淵博精深,“周盤”、“殷誥”的佶屈聱牙,都成了伏生“仰之彌高,鑽之彌深”的樂趣所在。也正因為如此,當秦始皇、李斯燃起焚書烈焰的前夕,伏生藏了《尚書》﹔當西漢帝國的大廈需要文化學術支撐的時候,他傳了《尚書》,此后終於形成尚書學兩千余年之無限風光。
伏生自己,也因授經而成一代儒家翹楚,贏得了崇高聲譽,千年后還被統治者封了侯,稱為先儒聖賢。史載唐代詩人王維曾畫過一幅《伏生授經圖》,圖中一位老者,在教一幫弟子讀書。王維認為這是個恆久美麗的題材。
(文並圖/趙炎)
(來源:北京青年報)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