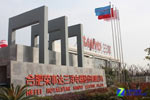|
|
|
如果說王獻之承繼了其父王羲之寧靜、儒雅的名士風范,他的兄長王徽之卻是一反父親的浪漫詩意,以狂狷不羈、卓犖放誕聞名。相傳這位“不可居無竹”的“偽名士”,當年進京時,泊舟於清溪側(現南京有一景點,為“邀笛步”),遇上擅長音樂的大將軍桓伊,二人素不相識,卻相互欽慕。桓伊應王徽之所求,下車吹奏一曲,曲終,徑自而去,二人不交一言。之后,有人將桓伊所奏笛曲翻入古琴,便成了現在廣為流傳的《梅花三弄》。
桓伊究竟為王徽之吹奏何曲?該曲是當時流傳的曲目還是桓伊創作而成?琴曲《梅花三弄》是否源於桓伊所吹奏的那首笛曲?這些問題恐怕已無法得出定論。但是,《梅花三弄》源於古笛曲《梅花落》,為漢晉民間音樂之遺聲,當是可信的。
《梅花落》系漢橫吹曲之一。在《樂府詩集》中南朝文人鮑照《梅花落》解題就言“《梅花落》,本笛中曲也”。唐段安節《樂府雜錄》亦記載:“笛,羌樂也,古有《落梅花》曲。”這裡所言的《落梅花》即《梅花落》的別名。唐代詩人高適、杜牧、皮日休亦有相關的詩句記述這首古笛曲的存在,而白居易的那句“《六?》《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更是佐証了這首笛曲在唐代的流行程度,無怪乎段安節以《落梅花》之曲來代表笛樂了。
笛曲究竟何時被何人移植為琴曲?有琴譜稱是唐代的顏師古所為,此說孤立尚無佐証。但駱賓王“鸚鵡杯中浮竹葉,鳳凰琴裡落梅花”之句,倒是証明《落梅花》一曲在初唐之時便已譜入琴曲。因琴為梧桐木所制,而鳳凰又有非梧桐不棲之說,所以,古琴便有了鳳凰琴的美稱,而“落梅花”三字則點明了來源。顏師古為初唐時人,被作為改編者是事出有因。
《梅花三弄》最早見載於明代朱權所編的《神奇秘譜》,在此后的近600年中,有43種琴譜都刊載了這首琴曲,其流傳程度,可見一斑。《梅花三弄》版本頗多,流行最廣的當為吳景略打譜的《琴譜諧聲》本《梅花三弄》以及廣陵派《梅花三弄》。前者被稱為“新梅花”,后者被稱為“老梅花”。前者節奏規整,曲調流暢,頗有“風蕩梅花,舞玉翻銀”的意境﹔后者自由跌宕,古朴蒼勁,盡顯老干虯枝,錚錚傲骨的氣韻。但無論何種版本、何種風格的《梅花三弄》,都有在古琴低、中、高不同徽位上重復的泛音段,這也是“三弄”之名的由來。
正因為有這“三弄”,許多人便將《梅花三弄》視為中國的回旋曲,但單純使用西方曲式學結構分析,難免讓人有牽強附會之感。我更願意將此曲的變奏視為中國傳統音樂中“疊”的發展技法。而全曲中的許多段落以“合尾”的方式收束於宮音,這種中國傳統音樂慣用手法的運用,也使整曲於變化中求統一,形成了結構上的渾然一體和統一平衡,亦體現出中國傳統中追求平衡、中庸的審美趣味。
很多人在學琴的早期便習彈了《梅花三弄》,我卻是在習琴十幾年后,方才開始練習此曲。開始學習的是“新梅花”,因彈得過於流暢,我總是戲言我彈的《梅花三弄》更像“桃花三弄”。后來終是跟父親林有仁學了“老梅花”,也許是與廣陵的宿緣頗深,一經習彈,那蒼勁的吟猱,便如梅花的傲骨身姿,印入了心底,從此便將“新梅花”丟開了手,再未彈過。
“老梅花”見載於《蕉庵琴譜》,十段,共兩個主題。樂曲開始,以渾厚低沉的散音,呈現霜晨雪夜、萬籟俱寂、草木凋零的景象。爾后,由輕靈的泛音奏出的第一主題,打破了蕭索的氣息,仿佛輕吐幽香的梅花為蒼茫天地帶來一絲生機。而這段泛音採用的混合節拍,更使這一主題在流暢生動之余,多了些許蒼古意味。該主題先后在第二、四、六段中重復出現,形成了特有的“一弄”“二弄”“三弄”。
在變化重復的“三弄”之后,我們迎來了第二主題,也是全曲的高潮段落。如果說“三弄”的主題運用泛音刻畫了冬陽下的梅花,仙風和暢、萬卉敷榮的清雅韻致,那麼第二主題則運用實音勾勒出雪中臘梅傲骨凌霜、鐵骨冰心的堅毅形象。隨著滾拂、潑剌、掐撮、長鎖、短鎖等技法的相繼使用,加之左手多變的吟猱,氣韻生動的散板,大幅跳動的音程,使旋律一反之前的平和清亮,一派欺霜傲雪、蕊寒枝瘦的景象。第二主題在高音區變化重復兩次之后,於第九段在中低音區進行了第三次重復。在古琴堅實沉厚的音色下,蒼古遒勁的梅姿,清逸幽雅的梅香,凌霜斗雪的梅骨得到進一步深化,使人不由發出“君當如梅”的感嘆!
其后,隨著第九段尾部的“入慢”,樂曲的情緒也漸趨平和。第十段中商音的不斷重復以及羽音的收束之感,使音樂帶著強烈的不穩定感,進入由婉轉清麗的泛音構成的尾聲中,余音寥寥,不絕於耳。猶如零落於塵的梅花,形雖沒,香如故。正如楊掄《伯牙心法》所言:“梅為花之最清,琴為聲之最清,以最清之聲寫最清之物,宜其有凌霜音韻也。”
《 人民日報 》( 2014年02月27日 24 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郎永淳與愛妻"生死相依"
郎永淳與愛妻"生死相依"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