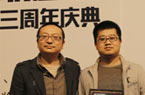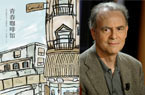上映之前炒得沸沸揚揚的電影《黃金時代》卻在上映之后“遇冷”。在國慶檔眾多大片的夾擊下,這部貼上了“文藝”“小眾”標簽的電影在票房上遭遇“滑鐵盧”。
就職於貴州廣播電影電視局直屬企業貴州星空影業有限公司,負責排片的資深影評人瞿倫春告訴記者,“《黃金時代》在10月1日上映當日,筑城院線的排片量不足8%,此后則一路走低。目前的排片量不足1%。”“期間,《黃金時代》在星空影城恆峰店的票房總產出,不足4萬元。”恆峰店總經理李本欣說。
值得關注的是:當下在出版界、學術界興起的“蕭紅熱”,為何沒能延續到影視界?《黃金時代》用堪稱“黃金陣容”的編、導、演團隊演繹蕭紅一生,票房慘敗的原因是什麼,會引發怎樣的連鎖效應?針對這些問題,本報記者作了走訪。
電商營銷發力今年“國慶檔”
“按照往年的經驗,今年電影‘國慶檔’我們的預測是‘四足鼎立’,即寧浩的《心花路放》、許鞍華《黃金時代》、陳可辛《親愛的》和蔡岳勛的《痞子英雄2》。此外,《麥兜我和我的媽媽》、《魁拔3》等動畫片也很有口碑和市場競爭力。”瞿倫春說,以上影片題材類型不同,各有目標觀眾。國慶前一周,星空影城出台放映計劃:節假日是許多家庭的親子電影時間,《麥兜我和我的媽媽》等動畫片類型分得20%的排片量﹔喜劇《心花路放》符合假日輕鬆、喜慶的氛圍,加上寧浩、黃渤、徐崢“鐵三角”的票房號召力,《心花路放》獨佔40%的排片量﹔《黃金時代》在夾縫中贏得8%的排片。
放映計劃初步確定后,影院的網絡售票端口向貓眼等簽訂合作協議的電商開放,方便觀眾網上訂票。“不同的是,電商貓眼與《心花路放》合作,聯手全國部分院線,以超低的票價預售、極准的上線時機炒熱了《心花路放》,使得該片在全國的預售票房近1億。”瞿倫春告訴記者,《心花路放》未映先火,院線不得不擠壓《黃金時代》等同期上映影片的排片量,增加《心花路放》的排片量。“該片在上映首日,星空影城的排片量就高達50%,贏盡了市場先機,而且該片排片量在國慶后續幾天一直遙遙領先,票房產出自然可觀。可以說,電商營銷是《心花路放》成功的關鍵。”瞿倫春說。
他告訴記者,《心花路放》在國慶期間的票房超過8億,在貴陽地區票房產出約150多萬。“其實,《心花路放》是寧浩導演所有作品中最糟糕的一部。此前,我們預估該片的全國票房大概也就3、4個億。”瞿倫春說,其實此前電商已開始逐步介入電影市場,但此次介入的力度、引發的效應前所未有,為《心花路放》贏得了大量的與電影質量不成正比的票房,此后,電影市場不得不面臨著電商介入引發的新變局。
“蕭紅熱”未能助力《黃金時代》成功
今年“國慶檔”,“四足鼎立”一下子變成了《心花路放》的“一枝獨秀”。“在市場總量有限的前提下,《心花路放》一下子切走了半個‘蛋糕’。加上其他影片的沖擊,留給《黃金時代》的市場空間就極為有限了。”瞿倫春說,此次《黃金時代》失利,主因在於選錯了檔期,有些生不逢時。《2013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顯示,最受歡迎的電影類型中,喜劇、愛情、科幻等題材的電影位列前列,類似《黃金時代》人物傳記題材的藝術電影顯得小眾化。“加上該片長達三個小時的片長,創新得有些冒險的拍攝手法,影響了影院和觀眾對它的關注度。使得本是小眾電影的《黃金時代》,顯得更加的不合時宜。”
“但優質的文藝片要獲得好票房,也是有規律的。”他總結的規律是:一、先在海外影展上獲獎,光環加身﹔二、選好相對冷門的檔期,最好是在國產片保護期內﹔三、做好宣傳。“之前《白日焰火》、《桃姐》、《觀音山》等藝術片都是遵循這一規律獲得票房成功。但《黃金時代》似乎是有意逆而行之。”
“蕭紅是近三四年來學術界、出版界、影視界的‘熱餑餑’,蕭紅的粉絲不可謂不多。2011年,蕭紅誕辰一百周年,各種學術會議、論文資料如火如荼的召開與出版。”長期從事文藝理論研究的貴師大文學院副教授索良柱博士說。他分析說,“蕭紅熱”的興起,源於“民國女性”已然成為閱讀時尚之一,民國女子們的才情和感情共同成為“八卦”的對象,而蕭紅的一生,恰恰不缺少這類“談資”。身為女性的蕭紅,感情世界的復雜曖昧,和相關史料的缺失,為這一輪蕭紅熱提供了無盡的想象空間。
值得探討的是,反映蕭紅一生的《黃金時代》影片似乎並未從“蕭紅熱”中受益。“這是因為人物傳記題材的電影本身很難拍好,加上《黃金時代》盡力避開蕭紅的‘八卦’,淡化戲劇沖突——這恰是大眾感興趣的,而是通過蕭紅的一生,串聯起那個時代形形色色的文化人的選擇與命運,使得電影有點像一篇長篇‘論文’,感興趣的觀眾自然不會太多。”索教授說。
但有意思的是,借助《黃金時代》的上映,蕭紅的作品再度在書市上熱起來。包括河南文藝出版社在內的出版社紛紛再版蕭紅的代表作,蕭紅的《生死場》、《呼蘭河傳》等作品擺在在筑城各大書店的顯眼處。“這段時間以來,蕭紅的書都走得很好。而且許多讀者選擇將蕭紅的一批書都買回去看,以系統地了解蕭紅。”西西弗書店營銷部經理呂英介紹說。
《黃金時代》的失利或引發連鎖壞效應
著名影評人譚飛先生說,近兩、三年來,文藝片似乎迎來了春天,很多低成本的文藝片成為票房黑馬,如《觀音山》、《失戀33天》、《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以及《桃姐》、《白日焰火》等。“大導演許鞍華+大編劇李檣+大演員湯唯、王志文”,再加上近八千萬的巨額投資,這一切都傳遞出同一個信息:《黃金時代》是一部影迷必看的好文藝片。“在中國電影史上,《黃金時代》的陣容與投資,明顯旨在開啟中國文藝片的大片時代。”
“其中,《桃姐》、《白日焰火》分獲八千萬、過億的高額票房。它們的出品方同為星美影業集團。”瞿倫春說,基於對文藝片市場的把握,使得長期發行文藝片的星美影業集團投巨資拍攝《黃金時代》,影片聚集的編、導、演陣容,許鞍華、李檣、湯唯,他們所具有的文藝片市場號召力,毋庸置疑是首屈一指的。“僅以湯唯為例,她憑借《晚秋》、《北京遇上西雅圖》兩部分獲八千萬、五個億票房的小成本文藝片,已經樹立起個人品牌。”
截至10月17日,投資八千萬的《黃金時代》全國累計票房僅有四千七百萬,血本無歸。“此一役,意味著中國文藝片的大片時代將被延后。”瞿倫春說。
“好電影得差票房的同時,是差電影得好票房的現實。這會引發一個極壞的效應:電影營銷比電影本身更重要。而這已經成為電影界的一種趨勢。”娛樂營銷專家田金雙說。當然,他也承認,電影營銷本身是無罪的,“但電影營銷隻能是手段,不能成為目的。而且,在差電影紛紛通過營銷獲得好票房的現實下,好的電影也得學會運用甚至創造營銷模式。畢竟,現在屬於‘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年代。”
★延伸·訪談
“好電影”如何
有“好市場”
電影如何既不當市場的奴隸,又不當市場的敗兵,做到藝術與市場共存,這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本報記者為此採訪了筑城的相關藝術界人士。
“有什麼樣的觀眾就會有什麼樣的電影,這是市場規律。不過反過來也一樣,有什麼樣的電影就會有什麼樣的觀眾。”黔籍導演唐煌認為,要慢慢培養電影觀眾的藝術品位。“好的電影有時往往是小眾的。我們並不是沒有高品位的觀眾,只是數量有限,把高品位觀眾從小眾培養成大眾,好的電影才有了生存的基礎。”他建議在政府的支持、幫扶下設立藝術院線。
“《黃金時代》的慘敗,給藝術電影提了個醒。很多人認為:藝術電影的價值就是看不懂,以至於很多藝術電影以晦澀難懂為榮,而絕大部分觀眾卻難以欣賞,不買賬。這不利於藝術電影的培育。”黔籍導演張巳陽說。
本報記者 鄭文豐
(來源:貴陽日報)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