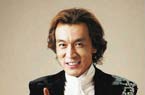原标题:“阅读”立法重在执行
“全民阅读立法列入2013年国家立法工作计划”的消息一出,全国一片热议。
赞成者认为,我国国民阅读现状堪忧,亟需改变;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阅读资源严重匮乏的贫困地区,一些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阅读需求远远得不到有效满足。通过立法,在国民阅读的场地、空间、条件、服务、财政经费等方面给予极大的保障和支持力度,可为全民阅读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多的便利。
质疑者说:“我不读书就犯法吗?阅读是私人行为,读多读少、读什么、怎么读不都是自己的事吗?难道一纸法令就能让我爱上阅读?”
诚然,“阅读”立法有助于解决诸如阅读资源不足、分布不均衡等问题,但显然,我国全民阅读存在的问题也绝非一部法规条文就能解决。试看,近些年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部门为推广全民阅读做了大量工作,在建设与阅读相关的基础设施上也下了番工夫。自2006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开始大力倡导和推动全民阅读活动以来,有多个省(区、市)成立了全民阅读组织领导机构,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城市常设了读书节、读书月活动,可有些活动流于形式、走过场,终究未能形成读书氛围与气候。目前全国基本实现县县有图书馆、村村有文化站,可在许多地方,相对于人满为患、热闹非凡的棋牌室、舞蹈室和健身房,图书阅览室则稍显冷清、甚至门可罗雀。
又以广西为例,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阅读素养评估报告(2012)》中称,经调查发现,阅读素养与阅读时间、学习环境、家庭藏书量、父母职业有关,而造成广西中小学生阅读水平偏低的原因是:学业压力、社会环境不容乐观。
由此可见,阅读立法的内容以及如何确保条文的落实成为关键。我们也注意到,相对于成年人阅读率难提升的事实,阅读习惯从小抓起更为可行。国外一些类似法案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美国《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其中针对学前教育的“阅读优先项目”包括:创设一套综合性的、州政府范围内的阅读计划,以确保每一个儿童到三年级时都能够阅读;开展公平起点的家庭读写计划;在学前计划和“提前开始”计划中资助阅读学习等。俄罗斯的《民族阅读大纲》,要求在出版、运输和传播儿童书籍方面提供国家保护措施,创建俄联邦国家权利委员会下属的联邦阅读研究中心等。这些法案在实际执行中,有明确的工作对象,有可量化的指标作为评估标准,有资金保障,所以成效显著。
“阅读”立法应以“促进”为目的、以“倡导”为本意,旨在呼吁公众重视阅读,提高他们的阅读积极性,保障阅读资源和权利,提供有利于阅读的良好环境。
(来源:广西日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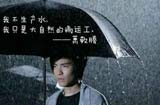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