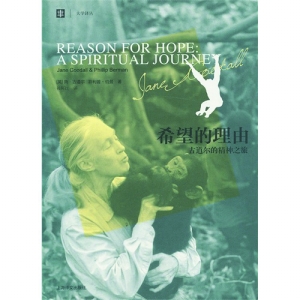
《希望的理由——古道尔的精神之旅》 (英)简·古道尔 菲利普·伯曼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4月
科学志
英国生物学家简·古道尔因其在黑猩猩行为领域内的开创性研究,而被誉为“我们的知识世界最有影响的贡献者之一。”(《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但令人惊奇的是,作为生物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古道尔并不具相关学术背景,甚至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因而,其对“知识世界”的贡献既耐人寻味,而关于“知识世界”的含义恐怕也要就此改写。
黄夏
《希望的理由》是古道尔回顾往昔、寄情未来的一部精神自传,在书中,她记录了自己从一个喜爱动物的小女孩,到远赴非洲从事黑猩猩研究,及至巡游全球推动环境保护、倡导可持续发展的心路历程。在此过程中,囊括人类和生物在内的系统性社会学知识,也以另一种方式被重新建构起来。
与偏见斗争的大半生
与一般学术类著作不同的是,《希望的理由》是一部饱蘸了作者深情的作品。在严谨的科学论断之外,我们时时可以读到作者对动物、对人类、对自然发自内心的爱,这种爱,绝非通过学术训练就能获致,而一旦得到这种爱,则可以成为学术和生活的共同信仰。
那么这种爱,来源于哪里呢?古道尔写道:“我的思想是在我20岁之前逐渐形成的,对我产生影响的是我的家庭、我所受到的教育、我所经历的战争岁月、多年来聆听到的震撼心灵的布道,此外还有我所读到的那些书,我在户外自然界所度过的时光,以及我们家所饲养的小动物。”
说来似乎稀松平常,无甚出奇。但哪个家庭的父母,会乐意看到自家的宝贝女儿与蚯蚓和海蜗牛共眠的呢?又有哪对父母会耐心地告诉女儿,蚯蚓无土海蜗牛无水便要死亡,以此培养孩子兼顾理性的爱心呢?这种张弛有度、鼓励独立自由思考的环境,以及在二战岁月中对人类命运的悲悯情怀,使古道尔在日后的生活和研究中,格格不入于打着各种“科学”旗号的世俗性偏见,她的大半生,即是在与这种偏见的斗争中度过的。
1957年,23岁的古道尔受雇于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权威路易斯·利基,慧眼识珠的利基给了古道尔一份旨在揭示原始人类行为模式的灵长类动物研究计划。1960年,古道尔来到坦桑尼亚贡贝自然保护区,开始了其长达40年的研究生涯。
颠覆诸多“科学原则”
从一开始,古道尔就颠覆了生物学研究领域中的诸多教条。根据“科学原则”,为了获得有用的数据,科学家必须保持“客观冷静”的头脑,把所看到的情况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尤其不允许自己对观察对象发生“移情”。古道尔对此不以为然:“我对这些聪明的生灵的理解,有不少恰恰是建立在对他们产生移情的基础之上。一旦知道有些情况为什么会产生,就可以对自己的解释进行严格的验证”。秉持“移情”理念的古道尔发现黑猩猩竟然能够利用花花草草制成的“钓竿”钓白蚁,这一发现打破了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的成见,重新开启了关于何为“人类”、何为“工具”等概念的大讨论。
古道尔还给黑猩猩取名,而按照“科学”方法只能对观察对象编号。这种离经叛道直接挑战了当时科学家认为动物是没有个性、思想和理性思维的一块活肉的论调。古道尔发现黑猩猩群体中存在着与人类相同或者相似的家庭、阶级和社会组织,而黑猩猩本身也具备和人类一样的情感、理性和思维能力。据此,古道尔质疑了当时以人类为中心进行科研活动的“归纳主义”过于简单化和机械化。
古道尔从事研究的近半个世纪,正是非洲深陷反殖民斗争、内战、独裁、政变的时期,而冷战也在全球范围上演正酣。外部世界的混乱使古道尔忧心如焚,但她没有不问世事做个专事涤净自我灵魂的朝圣客,而是从动物学研究出发,寻找人类区别于黑猩猩的那“1%多一点点的基因”的特出之处。
没错,人类的美德与罪恶存在于与黑猩猩相同的那98%的基因之中,但正是这1%的差异,使人类能知生与死,也能对未来作出长远规划。古道尔认为,人类的命运,不在社会,不在环境,而就掌握在人类自己、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里——改变,从自我做起。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对人类抱持的希望和关怀。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