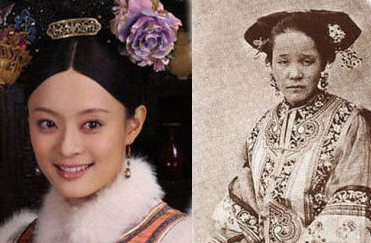|
|
|
一直好奇,这本平和冲淡、粗俗却也清雅的《繁花》背后,究竟是怎样一位作者?
《繁花》是金宇澄在2012年完成的长篇小说。自问世以来,几乎获得了所有的荣誉,包括排名2012年“中国小说学会长篇排行榜”榜首,以及最近公布的“施耐庵奖”。有评论称,“这是一部有关上海最有质感、最极致的长篇”、“将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深刻印记。”
在上海市作协,记者与作者见面,老金个子瘦高、为人谦和、眼神锐利,常年担任《上海文学》常务副主编,20年间极少提笔。60岁这年,这位小说界的“潜伏者”,厚积薄发,写出了这部“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冲向终点”的《繁花》。
《繁花》,一种缓慢、谦恭的传统叙事态度。
“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听见有人招呼,沪生一看,是陶陶,前女朋友梅瑞的邻居。沪生说,陶陶卖大闸蟹了。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沪生勉强走进摊位……”30多万字的《繁花》,生活就像河水,缓慢地流过眼前。
金宇澄说,这部小说,作者没有代入感,以中国方式,记录普通人的一生。“中国人特看重一生一世,永世不变;因此‘盛极必衰’应该是永远的主题,人生必然有悲,花无百日红,无法抗拒,大部分的人不喜欢悲,但文学应该直面人生。以客观的身份,讲这个城市人群,近百个人物,点点滴滴,形成普通的生活网。”
评论家谢有顺认为,金宇澄表现了“市井与俗世的庸常,从容还原,曲处能直,密处能疏,有着话本式的传统面影,骨子里亦贯通、流淌着先锋文学的精神血脉,把传统资源、方言叙事、现代精神汇聚于一炉,为小说如何讲述中国生活创造了新的典范。”
老金喜欢钱钟书先生。“《围城》里没有激昂慷慨的人,没有极其高尚的人,也没有特别卑鄙的人,处在一种混沌状态,是钱先生发觉的国民性。“无论什么时代,国人有些东西是不变的,虽然我们读大量翻译小说,那是别人的样式,我们国民性究竟是什么?”
“市井形成某种态度,就如无论海面上风浪怎样翻滚,市井接近水底泥沙的部分,它们那种波动和生态,跟海面是不同的。《繁花》试图反映这一阶层状态,不加任何议论,体现一种意味。”金宇澄说。
这部具有独特语感的作品的缘起,是在网络上完成的初稿。“每天我早起写一段发帖。开始两三百字,平均每天2000到5000字一大块,非常状态,写6000字也有。对话挤在一起,基本用逗号和句号,传统文本也都是这样。热心网友为我加了标点符号,分段单列,我不同意,分开就成剧本了,大块的文字,有一种介乎于对话和叙事的效果,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同样也有整页不加标点的,显示了文本的个性。”老金回忆。
后来,金宇澄将《繁花》从纯粹的上海方言,逐渐改成全国读者都懂的“上海官话”。“网上初稿的上海话味道,比印刷本更浓,文字修订花了很多时间,去掉有障碍的词语。如上海话‘侬’,地域特色很强,因此不用,上海话“伊”,也不用。逐渐收敛,30多万字,语言沟通调整,反复改20多遍,看上去很自然的句子,都经过复杂的折腾,费了很多功夫。上海话很多短句,《繁花》只保留句式和韵味。”
他想把曾经摧毁的文字找回来,“也许有意义,最近央视举行汉语听写比赛,也出现了那么多我们曾经抛弃的文字,都那么美好。历史就是这样回旋发展,就像传统的旧家具,有段时间我们都不要,现在,这东西很值钱。”
有人评价,《繁花》让小说回归到“说”的状态。
“写作期间,觉得有个苏州老头,一直在耳边絮叨。我父亲是苏州人,以前他上海话很标准,古人讲‘及其病革,遂复乡语’,到了老年,他的苏州音越来越浓。此外,我有上山下乡经历,在东北生活7年,经常用非上海人角度,理解上海,试图打开地域的屏障,让外人看上海人怎么生活。”老金说。
感铭自身的幸运,写出了最想写的《繁花》。金宇澄说,“我觉得前面几十年所有的积累,是有回报的。到《繁花》开始印刷,我忽然觉得,这小说可以一直写下去。它的场景一直在变,我只是拿玻璃罩子,固定了其中的一部分。”
《 人民日报 》( 2013年11月21日 19 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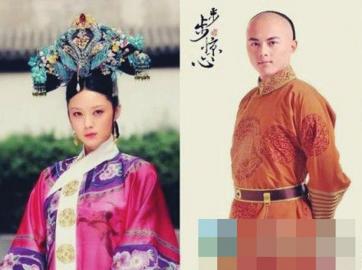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