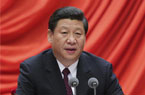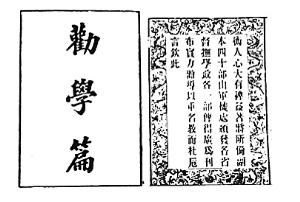
《劝学篇》是张之洞变法思想的代表作,被光绪帝认为“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如时人所谓:“遍传日下,一时都人士无不击赏折服。”

张之洞(中)署理两江总督时在江宁(南京)接见美国客人的合影。
张之洞(1837-1909年)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代表人物。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一个大变动时代,所谓“千古未有之变局”。其时,内忧与外患交加,危机与生机并存。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关系到国家与民族前途出路问题的时代中心课题,严峻地摆到了国人的面前。作为一个传统的官僚士大夫,张之洞的所思所想,能否跟上时代的脉搏呢?答案是肯定的。张之洞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其改革思想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要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寻求一条相对稳健的改革道路。
一、中庸之道
甲午战争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重要界标,中国被“蕞尔岛国”日本打败,强烈地刺激了国人敏感的神经;与此同时,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救亡图存迫在眉睫。于是乎一股维新变法思潮勃然兴起。
康有为、梁启超是主张维新变法的急先锋。他们上书光绪皇帝,主张亟待发愤自强,革旧图新,否则中国将为“土耳其、高丽、安南、波兰之续”,也就是遭受亡国的命运,到那时“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他们大发警世危言,主张从根本上进行全面改革,所谓“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然而,他们的激进变法主张遭到顽固保守派的激烈抵制。慈禧太后的宠臣荣禄声称“祖宗之法不能变”,大学士徐桐更是极言“宁可亡国,不可变法”。两派剑拔弩张,只有鱼死网破的结果。
如何在激进派的“全变”与顽固派的“不变”两个极端之间寻求第三条变法道路呢?这就是张之洞在其著名的变法思想代表作《劝学篇》中阐述的相对稳健的改革观。张之洞曾经自述其发表《劝学篇》的缘由时说:“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日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这里所谓“邪说”是指康、梁而言。显然,张之洞的《劝学篇》是针对顽固派与激进派两面而发的。近代中国处处交织着中西与新旧的矛盾。张之洞明确标榜“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其意正是要走调和稳健的道路。
张之洞的改革观是以儒家的“中庸”思想为哲学基础。《中庸》被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称作“孔门传授心法”之作。“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在“过”与“不及”之间寻找一个恰当适度的做法,这是儒家伦理关于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张之洞特重《中庸》,他曾自称毕生坚持的从政宗旨是:“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显然符合“中庸”之道。
张之洞把《劝学篇》二十四篇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五知”,即知耻、知惧、知变、知要、知本,认为:“凡此所说,窃尝考诸《中庸》而有合焉。”并引述《中庸》里孔子“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之言相比附,以为《劝学篇》“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可见,《劝学篇》之所作,是有意融会贯通《中庸》的意旨,其在中西与新旧之间所持的调和折中立场,更是合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理念。
二、权衡新旧
在晚清官场,张之洞向以干练圆滑的“巧宦”著称。因此,关于张之洞在戊戌变法时期发表《劝学篇》的动机便使人颇多疑惑。有人认为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意在两面讨好,是投机之举。殊不知《劝学篇》成书之时,事态尚不明朗,势必也将冒着两面得罪的危险。也有人认为《劝学篇》是专攻康梁激进派,因而使张之洞能够在戊戌政变之后得以无事。但有趣的是,《劝学篇》是在百日维新期间经康梁拥戴的光绪皇帝的谕旨而颁行天下的。如何理解这些矛盾现象呢?
其实,虽然难以排除一些外在的因素,但更应从张之洞自己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来解释。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实际上有针对激进派“言新学”、顽固派“守旧学”的情形,展开两线作战并调和两方面的意味。他认为:“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其《劝学篇》则是“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可见,张之洞的《劝学篇》之作,与其说是在于“破”,即与人论战,毋宁说是在于“立”,也就是要在新旧两方面矛盾冲突中寻求一条稳健的变法道路,正所谓“权衡新旧”。
当时,尽管维新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但是康梁维新派的势力并不大,他们的急进变法思想曾遭到普遍的反对。百日维新期间,杨锐密告张之洞说:“近日变法,天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相对来说,张之洞的稳健变法思想更容易能被保守势力所接受,他的《劝学篇》的部分内容被选进保守派言论集《翼教丛编》就是明证。《劝学篇》成书之日,正是康梁维新派得势之时,关于是否刊刻的问题当时在张之洞的幕僚中尚存在不同意见。“阻刻者嫌其不合时宜,劝刻者正为补救也。”所谓“正为补救”,正是针对康梁维新派的激进主义而言的。辜鸿铭曾明确地说:“我曾亲自出席过张之洞总督召集的一次幕僚议事会,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问题”,《劝学篇》是在那次会议之后“立即写出来的”。与康梁维新派的遭遇相反,张之洞的《劝学篇》在当时颇有市场,在光绪皇帝谕令颁行全国之前已经流传开来。如时人所谓:“《劝学篇》遍传日下,一时都人士无不击赏折服。……值此异学争鸣之日,实足以正人心,固士气,杜伪学,遏乱萌。”
光绪皇帝对《劝学篇》的态度颇可玩味。黄绍箕进呈《劝学篇》时在奏折中所述原委是:光绪皇帝召见他时说:“近来议论于中、西各有偏见。”显然是对激进的趋新与极端的守旧两种态度都有所不满。黄绍箕当即奏称:“湖北督臣张之洞纂有《劝学篇》,持论切实平允,尚无流弊,容当进呈。”得到皇帝的允许。光绪皇帝在将《劝学篇》颁行全国的谕旨中称:“朕详加披览,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应该说,《劝学篇》的思想主张光绪皇帝是赞成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作为康梁维新派拥戴的“变法君主”光绪皇帝对《劝学篇》持赞同态度,决不是因为它攻击康梁,而是因为它“权衡新旧”的相对稳健的变法思想。
三、会通中西
张之洞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是由《劝学篇》所构建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关于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张之洞明确标举:“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体系中,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不是平列对待,而是有主次之分、先后之序和本末之别;具体而言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先西学为后,取西学之长补中学之短。他并不完全守旧,而是主张有限度的变革,即在激进派的趋新与顽固派的守旧之间寻求一条稳健的变法道路。他所坚持的是中国的伦常名教,这是中学的核心内容;同时,他也主张学习西政、西艺,不仅是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还可以有某些制度的变革。他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这是他的“中体西用”论的核心内容。
“中体西用”的思想不是张之洞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大致在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已从清流派转化为洋务派,在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坚持儒家传统的道德精神之间,他采取了“调和折衷”的方法。张之洞主张在引进西方先进事物的同时,必须用儒家道德精神消除如辜鸿铭所称的“欧洲那极端的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可怕怪物”。如果说他的洋务活动就是具体的实践过程,那么《劝学篇》的写作则是一个理论的概括与提升。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随着他的《劝学篇》的刊刻与传播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曾先后颁布了两部私人著作:一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是张之洞的《劝学篇》。有趣的是,前者的一句“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向来被认为是“中体西用”论的初始表述;后者则是“中体西用”思想的系统阐释。这样,不仅《劝学篇》一书挟朝廷之力得以风行于世,而且“中体西用”思想更是借皇权之势而被广泛流传。《劝学篇》面世以后,不断地被人翻刻,并很快由传教士译成外文。据英文译者吴板桥(Samuel I. Woodbridge)牧师称,可靠的估计其发行量在100万册。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劝学篇》的大量发行,也使“中体西用”思想广泛传播。梁启超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了那个时代的“流行语”,“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虽然“中体西用”说不是张之洞的最初发明,也不是他的独家思想,但是,说他是这种思想的最具权威的发言人或典型性的代表人物,则是毋庸置疑的。应该说,《劝学篇》已经收到“劝学”的效应。
毋庸讳言,对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时人与后人亦多有非议。无论是严复讥之为“牛体马用”,还是近人批评其在封建主义之体上嫁接资本主义之用,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亦未必击中要害。究竟问题何在,尚需进一步深究,姑不赘论。在近代中西文化激烈冲撞的大变局下,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便成为决定中国文化前途与出路的根本性问题。颇为时下学界推崇的学术大师陈寅恪,在论及中国学术思想创新的路径时曾经精辟地指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他还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可见,陈寅恪服膺的正是曾国藩(湘乡)、张之洞(南皮)的“中体西用”文化观。“中体西用”论提供了一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中庸而开放式的思维框架:既不完全固守传统,也不一味全盘西化,而是要“权衡新旧,会通中西”,也即以调和折中的方式,走中西结合的道路,当然是要把中西文化优秀的东西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中国文化。尽管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究竟什么是中西文化优秀的东西,以及如何将其结合起来,则是对不同时代的民众、学者尤其是政治家智慧的考验,但无论如何,这种思维框架业已昭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新方向。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