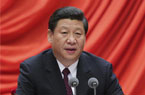灰色的西便装,白色的衬衫领子整齐地翻出在灰色的羊毛衫领口,头发梳向脑后,微眯着双眼,这位形象可亲的“中年大叔”就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2日,莫言首次来到浙江大学,受聘杭州文艺顾问。在杭州,他比较罕见地全面剖析了自己文学的风格,表示他并非要写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翻版,而是想写出有自己特色、中国特色的小说,即“梦幻的现实主义”。
“我要避开这两座灼热的高炉”
2012年10月,莫言摘得诺奖桂冠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走入中国普通阅读者的视野,人们也总爱把莫言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加西亚·马尔克斯相提并论。
对此,莫言并不否认马尔克斯对自己的影响。“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从根本上颠覆了我们这一代作家。我在1984年第一次读到《百年孤独》,心情就像当年马尔克斯在巴黎读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
莫言说,当时,中国作家们意识到生活中充满了魔幻的素材,可以用来描述和表现个人经历与中国现实。1984年前后,“中国文坛出现了许多(马尔克斯的)模仿者,我的一些中篇《球状闪电》《金发婴儿》也有它的痕迹”。莫言回忆,当时还有许多作家模仿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的意识流写法,几千几万字中不分段、不用标点符号。
“我想这样的模仿没有出息,我要‘避开这两座灼热的高炉’。”莫言强调,事实上他与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搏斗多年:他并非要写西方小说的翻版,而是想写出有自己特色、中国特色的小说。
莫言认为,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辞中说他的作品是“梦幻的现实主义”,这是比较合适的,如果仅是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的结合,就没有原创性。
与故乡作家蒲松龄“一拍即合”
“要避开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影响,只有一个办法是向民间学习。”莫言回顾说,向民间学习有两个方式,一是学习老百姓的口语,另一种方式是向口头传说中寻找素材。
莫言认为,民间故事的记述者在他的老家山东已经有一位先行者,就是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
“蒲松龄创作《聊斋》时,在门前大树下支起茶炉,请行人喝茶抽烟,请他们讲奇闻逸闻。事实上,马尔克斯也深受他外祖母所讲述的许多故事的影响。”莫言表示,能表现一个民族的特质的东西,必然能在民间找到源头,在此基础上加上丰富的想象力和生活经验,以及优美的文笔,就是对抗西方文学的重要力量。
“每个作家都应该从所熟悉的民间汲取营养,形成独特的艺术特色。如果他找到了独特的叙事语言,找到了特别擅长的一类故事的原型,写作就会如鱼得水;如果他始终找不到自我,找不到文学的一块根据地,就会变成一般化的讲故事的小说家。”
莫言表示:“对我影响更大的是蒲松龄这样的作家,他与我有血脉上的联系,是故乡作家,和我是一拍即合。”
“‘反对生活决定艺术’太狂妄”
“本来我也是反对‘生活决定艺术’的作家。在1980年代我写过一篇《天马行空》,认为没有见过大海的人写大海,可以比见过的人写得更为壮阔,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写爱情,也许比情场老手写得更美好。但是后来觉得太狂妄。”莫言反复强调现实生活的重要。
“魔幻现实主义刚看眼花缭乱,但还是要从现实中写出来。”莫言分析《百年孤独》中的一段著名情节:吉普赛人拖着磁铁走在路上,把家家户户的铁制品都吸了出来。“这样的情节显然违背生活真实,但是磁铁吸铁是常识,魔幻还是建立在现实之上,只是作了夸张,从而为创作打开了自由之门。”
“写小说确实是一件需要灵感和想象的事情。”对于80后作家的文风,莫言分析了他们想象力的物质基础。“我出身农村,在高粱地里钻来钻去,写它如鱼得水。而现在一些年轻作家,在我们放羊放牛的年纪,他们在看动漫,头脑里积累的是动漫的形象,一旦成为作家,这些素材当然会控制他们的想象力,成为他们想象的材料。”
《红高粱家族》曾被文艺评论界视作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滥觞,莫言表示,1980年代后许多作家已经不满足于忠实再现历史的要求,而是把重点放在人上,写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命运、人的情感在历史特殊环境中的变化,这就是“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但是,没有完全的历史小说,都是借助历史事件表述当代的思想,用历史的瓶子装当代的酒。”莫言说。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