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彦,1963年生,陕西省镇安县人,一级编剧,中共十七、十八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三次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创作电视剧《大树小树》获电视剧“飞天奖”,多次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首届“中华艺文奖”获得者。出版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散文随笔集《必须抵达》《边走边看》《坚挺的表达》,以及《陈彦剧作选》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文化部优秀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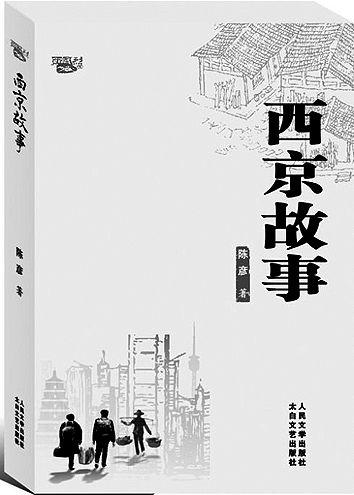

2016年1月,中国小说学会公布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装台》入选年度5部长篇小说排行,并位列榜首。
刚刚过去的2015年,对于陈彦而言注定难忘,惯常于戏剧现代戏创作的他,在当年10月出版了长篇小说《装台》,这是继《西京故事》之后其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小说。
2014年10月,陈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界的优秀代表,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总书记说:“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
《装台》正是陈彦在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后出版的一部力作。小说一经推出,即刻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评论家白烨说——
“如果说201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标志着戏剧家陈彦向小说家陈彦成功转型的话,那么,由作家出版社新近推出的长篇新作《装台》,就不仅把陈彦提升到当代实力派小说家的前锋行列,而且突出地显示了他在文学写作中长于为小人物描形造影的独特追求。”
延续着《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被誉为“西京三部曲”)等戏剧作品的创作宏旨,陈彦的小说依然将自己的笔触对焦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那些普普通通的平凡人。
2015年的最后一天,带着这本《装台》,陈彦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聊小说、谈戏剧、论创作、话人生。
“小说是书写生存的艺术”
写作《装台》,可以说完成了陈彦长久以来的夙愿。
从1990年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至2013年离开,23年,从编剧到团长、从团长到院长,陈彦与戏剧的缘越结越深。“我的一切喂养,都靠的是这块土壤,尤其是这块土壤上生长的人。”
到机关工作,陈彦虽然挥别了戏曲研究院,却挥别不了那些潜藏于心底的人和事。那些形象、那些故事都成为他写作的资源宝库。早在七八年前,写一部反映“装台人”生活的小说的想法就在他心中生成。
随后数年,几易其稿,距离的产生反而激发了陈彦的创作热情,经过沉淀、加工、修改,2015年终成此稿。
《装台》描写了一群常年为专业演出团体搭建舞台布景和灯光的人。打了20多年交道,对于“装台”这样一群人,陈彦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从这个小行当中琢磨出了大滋味——
“有人说,我总在为小人物立传,我觉得,一切强势的东西,还需要你去锦上添花?我的写作,就尽量去为那些无助的人,舔一舔伤口,找一点温暖与亮色,尤其是寻找一点奢侈的爱。”
在陈彦看来,装台工作虽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陌生的,但他们在生命中所不能承受之重,他们的坚守与挣扎,光荣与梦想,与我们却没有根本的不同。“我熟悉他们,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欢乐着他们的欢乐,忧愁着他们的忧愁。”
《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一期全文选载了《装台》,卷首语这样评价——
“关注底层小人物并不难,难的是你了解不了解他们的营生勾当,熟悉不熟悉他们的言语做派,对他们的内心和命运有没有足够的体察和思考。陈彦熟悉舞台,熟悉后台,他用小说的方式把隐身于帷幕背后的装台人推到了前台,让读者随着刁顺子和他的伙伴们的劳苦努力、悲喜哀乐而俯仰感叹,而有所领悟。”
在《装台》中,主人公刁顺子和他的一帮弟兄们长年奔走于西京城的各个舞台,干着最累的活,说着最软的话,受着难忍的气,在一个又一个的装台现场为生活奔命。虽然生活极尽苛刻,数次让刁顺子在困境中难以突围,被逼得进退失据,但他从来都是认认真真劳动、踏踏实实工作、本本分分做人,“帮衬着一起装台的兄弟,关照着他所遇到的不幸的女人”。
评论家李敬泽说——
“很少有一本书会像《装台》这样,我拿起来,竟心甘情愿地走下去了,在那喧闹的生活里,在那些浑身汗臭的男人和女人身边,和他们一起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而我竟不想放下不想离开。现代小说常常空旷,而《装台》所承接的传统中,小说里人头攒动、拥挤热闹。《装台》的人物,前前后后,至少上百,大大小小,各有眉目声口。大致上是以刁顺子为中心,分成两边,一边是他在装台生涯中所交道的五行八作、人来人往,另一边是他的家庭生活,特别是通过他女儿菊花牵出的城中村的纷繁世相、形形色色。两边加在一起,真称得上是呈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
陈彦说:“小说是书写生存的艺术,书写生存的卑微与伟大、激情与困顿”。《装台》正是展现了这样一群在底层挣扎的小人物们困苦而庄严的生存故事。
“重新拨亮一种价值”
读完小说《装台》,人们或许会发现,装台人也有他们的“生活逻辑”,有他们的价值坚守、责任和担当。在陈彦眼中,刁顺子们持守正道,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这就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延续的“恒常价值”,时代的变化并不应让这些基本的价值失色或者暗淡,陈彦自觉地在艺术作品中不断拨亮,让其光华不减。
陈彦笔下的人物起点并不高,但作品中对底层人生活困境的挖掘却十分充分。从《迟开的玫瑰》中的乔雪梅、《西京故事》中的罗天福和《装台》中的刁顺子这些人物身上,我们读出了困境之中他们的成长与突围。
陈彦的作品总是着力展现这些身处生活底层的普通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让人们在对其满怀爱与悲悯的同时,生发由衷的敬意。
讲述20世纪50年代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现代戏《大树西迁》,没有写迁校上层的方案之争与宏大场面,而是将焦点对准一个最普通的青年女教师孟冰茜,用她五十年的生命史,从反对西迁,到完全融入西部生活,并深沉地爱着西部,多侧面多角度展示了她苦难一生、奋斗一生、奉献一生的心路历程。
在陈彦看来,小人物,普通人,永远是他书写的主体。他认为,城市中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值得更多人关注与书写。一个大城市,少则几十万,多则成百万,甚至数百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往往出现在这个城市最破烂、最肮脏的地方,清扫马路、建设高楼、疏通管道,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一旦哪里建设得花坛簇拥,一道围墙便把他们永远挡在了墙外。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他们在城市的边缘谋生,支撑着他们在苦难中前行?是什么样的生命信念让他们坚持着这种谋生方式,守望着他们的生存与道德底线,且长期与城市相安无事,一切的一切,都值得城里人很好地去回眸、关注、探究,并深刻反思。
陈彦在用一部部戏剧作品、也在用一部部小说作品回答着这些问题。
在评论家吴义勤眼中,陈彦的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没有理念化地将农民工作为简单歌颂的对象,也没有将城市简单塑造为欲望都市,而是站在中立的基点,在人性的视野内,审视两者的关系,以此凸显民族精神在压抑中的延展”。
“《西京故事》延续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所开创的思想传统,直面现实,本着‘为普通人立传’的主旨,紧紧扣住‘尊严’两个字,努力挖掘并呈现时代之痛与当代人的心灵之痛,全面展现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立体而多维地揭示了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人性救赎史。”吴义勤说。
陈彦除创作外,还发表了大量文论、评论,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创作要持守恒常价值”——
“我不喜欢在作品中过多地演绎新观念,而始终在寻找人类生活中的那些恒常价值。人类生活是相通的,都要向善、向好、向美、向前。那些经过历史检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对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调节起着永恒作用的长效价值,可能是我们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进行重新阐释,重新拨亮的价值。”“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对一些价值观进行重新省察、甄别,有许多值得重新拨亮,拨亮之后,这些传统价值就是时代的,甚至可能成为一个时代的最强音,比如厚德、比如诚信、比如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等等。”
陈彦说:“联系到城市中这样一群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我觉得他们始终坚守着一种东西,那是中华民族甚至人类最为朴素的恒常价值,这些价值让他们的劳作,让他们这些小人物的人生充满了坚韧性、道德感和尊严感。”
无论陈彦的戏剧“西京三部曲”,还是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都让人们看到普通人也能活出生命的尊严。普通人正大光明地用自己的汗水和勤劳去坦坦荡荡地获取自己的劳动所得,这样一种人生也是有尊严、有价值的人生,也是我们社会应该大力提倡、关注的人生。
陈彦始终相信,艺术家不仅要有悲悯情怀,还需要认同甚至提升普通人的生命尊严。“我们需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进入式地去审视他们的生活,不能漠视甚至指斥他们的生存价值。”
“我比较能下笨功夫”
在陈彦看来,到要创作时才去寻找素材、深入生活,这对写作而言是困难的。创作是对生活深入咀嚼后“化枣为泥”般的自然流淌。
面对如今文化快餐消费的时代,陈彦有着自己的坚持。他的作品在“出笼前总是慎之又慎”,需要静静地梳理、思考、沉淀、打磨。他认为,创作一部文艺作品,一定是“内心有话想说”,并且“是别人没说过的,如果都是别人已经说过的,而且你说的还没有别人好,没有别人精彩,那你说这个的必要性就不大。”
陈彦坚信,如果作家对生活没有感性的、内化为自己生命里的一种感情、认知,那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比较“隔涩”。
为了写出个性饱满的人物形象,陈彦始终将自己与所描写的人群置于同一位阶,无须仰视亦无须俯视,而是平等地走向他们的生活、认同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生活。评论家雷达说——
“《装台》是在人们,也包括作者自己没有事先预谋和明确期待的情况下积少成多写成的。《装台》与时尚的小说观念没有多少关系。作者只是写他的观察已久,烂熟于胸的人物以及环绕他们的世界,沉浸其中,才造就了这部人物活灵活现,世情斑斓多姿的现实主义力作。”
陈彦常常琢磨“装台”这个特殊的群体。他发现,“他们大多数是从乡下来的农民工,但也有城里人,往往这些城里人就是他们的‘主心骨’,当然,也有的成为他们的‘南霸天’。”
在写作之前,陈彦还特地找来几位比较熟悉的装台工作者,进行了长谈,做了好多笔记。正是平时这种细致的观察,和创作前的长期准备,“黏合了好多装台人的形象”,才有了刁顺子这样真实丰满、充满个性的人物。
在陈彦笔下,主人公们往往面对着内心的困境、矛盾与两难选择,当两难选择被完整呈现、人生困境被真实再现、心灵世界被充分打开后,主人公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做出了持守正道的人生抉择,这样的人物形象是在充分的张力中呈现人物内心的纠结、矛盾与反复,而在这样的铺陈后,人物最后的选择就是一种水到渠成。
评论家孟繁华说——
“好小说应该是可遇不可求,这与批评和呼唤可能没有太多关系。我们不知道将在哪里与它遭逢相遇,一旦遭逢内心便有‘喜大普奔’的巨大冲动。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就是这样的小说,这出人间大戏带着人间烟火突如其来,亦如飓风席卷。”
从《迟开的玫瑰》中的乔雪梅到《大树西迁》中的孟冰茜,从《西京故事》中的罗天福再到《装台》中的刁顺子,人们感到陈彦笔下的这些人仿佛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有评论家认为,这些主人公在陷入重大人生困境之中时的选择与坚守,少了一分“矫揉造作”,多了一分“生活使然”。这也最终使这些人物能够站住并且为读者和观众所认可。
“这就是我们身边真真切切的一个人,而人物的心路历程也会走得相对比较完整。”陈彦说。
写《西京故事》时,陈彦当时所在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门口,每天晚上都有十几个农民工在单位的屋檐下打地铺住着。为了对他们的生活有更深入地理解,他先后到西安的东、西八里村,访问过数十户人家。这个当地居民仅3000多口的城中村,竟然居住着10余万农民工和附近上学的大学生。
而走进西安木塔寨,这个原本1500余人的村子,却密集充塞着50000多农民工。陈彦在小说《西京故事》的后记中写道:“只有深入进去,触摸到了那一家一户、一摊一店地形复杂的生存河床,才能真实感受到这个特殊群落的人性温度与生命冷暖。”
写《大树西迁》时,陈彦在西安交通大学深入生活4个多月,随后到上海交通大学住了35天,前后找了100多位教授、学校管理层和学生进行交谈。陈彦说:“创作之前的做功课比创作本身下的功夫要大。《西京故事》舞台剧只有两个多小时,但是我后来写了50多万字的同名长篇小说,我多少年跟踪农民工生活,舞台剧只能表现很小的一块,大量的生活素材,尤其是对城乡二元结构当中所出现的社会矛盾进行的思考无法运用,最后必须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
看过陈彦戏剧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触,合辙押韵的唱词、扣人心弦的独白、婉转高亢的唱腔让人听得如痴如醉。从那些堪称经典的唱词中,我们读出了现代人的情困纠结,更读出了富有传统意味的隽永深沉——
“我喜欢写舞台剧,是因为我喜欢古典诗词,喜欢唐诗、宋词、元散曲。中华传统文化真的是奥妙无穷,有些作者将句子锤炼得那么精彩、那么情景交融、那么‘一石三鸟’,尤其是元曲,竟然那么生活、生动,那么有趣,雅能雅到不可‘狎玩焉’,俗能俗到像隔壁他大舅与他二舅聊天对话,真是一种太神太妙的艺术境界。”
陈彦说他的唱词写作,也与早年为数十部影视作品创作近百首主题歌词与插曲词有关,歌词提炼与戏曲唱词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妙,都需压榨,都需凝结,都需“以少胜多”。大量的歌词创作,还让他在戏剧、文学创作之外,收获过《陈彦词作选》的结集出版。
陈彦始终信奉这样的观点:“写历史剧,需要认真研究现实,而写现实题材、写当下社会,则需要更多地关注历史,只有对历史有比较深入的学习和了解,才能很好地把握当下和未来,如果我们割裂了对历史的学习和认知,我们对当下的把握很可能是浮泛的、短视的。”
陈彦学习历史、学习传统,那是下了真功夫的。他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担任院长10年,有晨跑的习惯,每天早上一个小时。别人都以为他在锻炼身体,其实,陈彦在晨跑中完成了一个庞大的学习计划——背诵元典。
从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秋水》,到《大学》《中庸》,再到17000万多字的《论语》,还有35000万多字的《孟子》,陈彦都是在日复一日的晨跑中完成背诵的。
当年,陈彦创作电影剧本《司马迁》,他认真地将《史记》通读了四遍,而且阅读的是四种不同的评注版本。每读一遍,他描红批注都是密密麻麻——
“通读完了之后还是找不到人物形象,后来我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背了下来,随后在构思剧本的时候,躺在床上一边背着《报任安书》,一边在头脑中复活司马迁的人物形象,他的为人、做派、性格、性情、说话的语言表达方式逐渐清晰。”
剧本创作如此,对于书法学习,陈彦也表现出同样的执着。二十年前,陈彦有了学习书法的念头,别人告诉他要多多临帖,陈彦就先用三年时间将《圣教序》临了100遍。
陈彦说,如果自己有什么可以值得“炫耀”的,那就是“比较能下笨功夫,认真做好每一件该做的事,无论创作还是工作,都当如此”。
“继续保持艺术的敏感”
1979年,16岁的陈彦学习改编了舞台剧《范进中举》,这算得上是他在戏剧创作上的牛刀小试。1980年,他创作了第一篇小说《爆炸》,写的是政府改河工程给小人物带来的生存危机,发表在内刊《陕西工人文艺》上。
1981年,陈彦开始在镇安县剧团学习编剧。在那几年中,他写了6部大戏,有现代戏,也有历史剧,形式上有话剧,有山歌剧,也有地方花鼓戏。
而在陈彦22岁那年,甚至有几个不同的演出团体,将他创作的《沉重的生活进行曲》《爱情金钱变奏曲》《丑家的头等大事》等多部剧作同时搬上舞台。
跨进艺术之门的陈彦在随后的创作道路上不断收获着被汗水浸润的果实。舞台剧《九岩风》《留下真情》等剧纷纷进入国家级平台调演展演。这期间,他还创作了30集长篇电视剧《大树小树》,不仅在央视一套播出,而且还获得了“飞天奖”和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更是让陈彦蜚声戏剧界,所获荣誉可谓将这一领域的大奖“一网打尽”。
《迟开的玫瑰》从创作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在陕西和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演出近千场,至今依然常演不衰,并有多家剧团多个剧种移植上演。《大树西迁》也已保持了14年的持续演出生命力。
《西京故事》搬上舞台仅4年多,但演出已近500场,不仅在大西北的“秦腔窝子”里斩获盛誉,而且在远离秦腔本土后,先后在广东、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吉林、黑龙江、福建、海南、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省市的数十所高校巡演,赢得老师和学生的普遍赞誉。
各种评价体系中相对集中的关键词是:“真实”“深刻”“感人”“接地气”“正价值”“正能量”。当说到“三部曲”的成功时,陈彦屡屡谈到——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是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成立的一个戏曲文艺团体,七十多年的历史,已经让这个院聚集起了一大批顶尖艺术人才,他们敬畏艺术,敬畏规律,敬畏创造,所谓‘西京三部曲’,是这个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只是一个受益匪浅的编剧。”
收获荣誉的同时,这些作品也在收获着历经时间检验的赞美。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在陈彦看来,“用传统形式来表现现代生活内容是可行的,是没有障碍的,关键是看你与时代血脉接通了没有。一切艺术都是可以穿越时空地域限制的,关键是看你走进他心灵了没有,走得有多深,其深度决定温度”。
陈彦从来不以成功者自居,但是,在创作道路上的他,如一位斗士,不断地尝试着不同创作式样的可能性。
散文集《必须抵达》《边走边看》《坚挺的表达》让人们意识到,戏剧家陈彦同样也是生活的思考者、社会的观察家与语言的设计师。每一本散文随笔集无不文香盈盈。
继《西京故事》《装台》两部小说后,陈彦即将进入第三部长篇小说《旦角》的创作,写站在舞台中心的“主角儿”的生活。陈彦说:“他们既是舞台上的主角,有时也是社会的主角。这部小说将从舞台辐射到相对广阔的社会生活。我对他们的生活很熟悉,以前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时候不好写,没有与他们拉开审美距离,我调离戏曲研究院到机关工作后,这些人物的形象常常扑面而来。”
当被问及是否已将创作重心转向小说时,陈彦说——
“小说是一种个体阅读,而戏剧欣赏则集合了几百、上千甚至数千不同背景、身份、年龄的人们,有时一场好戏甚至达到万人同看。戏剧这种群体观看的作品样式与小说这种个体阅读的作品创作,在很多处理上是不尽相同的。无论写舞台剧还是小说,都是为了让人观赏、阅读,但是我们必须为受众思考一些问题,要认识到观看者、阅读者的不同感受。一群人集体看与一个人个体看,有时感受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什么东西你觉得是合适的,触动了你的创作神经,你有表达的欲望,并且你认为用这种方式表达最合适,就用这种方式表达好了。”
访谈到最后,记者问陈彦平常对自己的时间都怎么安排,他毕竟还有机关工作缠身——
“再忙的人,都有学习思考的时间。我在工作上没敢马虎过,并且机关工作还经常占用节假日和晚上时间,因为我负责的是文艺工作这一块,好在与我的专业有关,也算是驾轻就熟吧。一个人只要有心,就会有很多时间。”
陈彦将写作视为“肉身给心灵的思想汇报,是自我对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的定期定时的盘整回望,是心灵的自然需求”。
陈彦说:“我现在每年的阅读量是60~80本书,有空便开卷,尤其是出差路途,让书籍填充得十分愉快,作家需要开阔的思想和生活视域。我认为无论是一个创作者,还是一个机关公务员,都需要不断地阅读和思考,阅读和思考可以让你的创作更好,也能让你把工作做得更好。”
结束访谈时,陈彦正要出差,记者看见他把厚厚两本书塞进拉杆箱,都是哲学著作。他说:“阅读是很快乐的事情。尤其是出差,你想,一路跟比你高出不知多少倍的高人对话,岂不快哉。”
本报记者 雷晓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