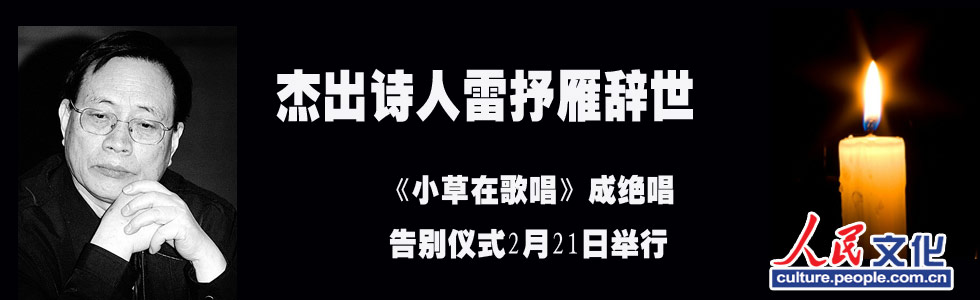雷抒雁詩話之三:好的詩人也應該是個哲人
5. 我曾想過,什麼時候會產生詩?有兩種觀點我很認可。一個是法國18世紀啟蒙主義思想家狄德羅說的:什麼時代產生詩,那是在經歷了大災難和大憂患之后,當困乏的人們開始喘息的時候。那時,想象力被傷心慘目的景象所激動,就會描繪出那些后世未曾親身經歷的人們所不認識的事物。另一個是英國19世紀浪漫主義詩人雪萊說的:在一個偉大民族覺醒起來為實現思想上或制度上的有益改革的斗爭中,詩人就是一個最可靠的先驅、伙伴和追隨者。在這個時代,人們積累了許多力量,能夠去傳達和接受關於人和自然強烈而使人激動的概念。
6.我1979年寫過一首《空氣》:“快把窗戶打開,快把門打開!讓新鮮 的空氣進來!海上的風,請進來!高原的風,請進來!吹我們的草,讓草綠﹔吹我們的花,讓花開!窒息的空氣,對健康有害,快把窗戶打開,快把門打開!”當時的詩就是直接對保守和禁錮的猛烈抨擊。另外,同一個時期寫的還有《種子啊,醒醒》、《希望之歌》等,都是在呼喚,興奮地呼喚。說的是種子,實際上是呼喚一 種希望,呼喚一種思想,呼喚一種能夠改變堅硬土層,改變這種禁錮的、落后的、封鎖的、專制的狀況的革命。那個時期我們的激情像狂飆一樣,都是圍著新的人生、新的社會、新的理念在呼喊斗爭。我們把自己作為啟蒙者,對著昏睡的耳朵喊:醒醒,醒醒!我們認為一個新的制度的建立,是需要文學家去呼喊、去吶喊、去催促的。現在提起來,有人常常說那些詩是政治,其實是錯誤的。那是一個狂飆突進的年代,社會處在重大改革發展過程中,當然需要吶喊。它不是在談情說愛,隻給一個人的耳朵說話,是需要警醒,需要大家頓悟、明白。也就是孔子講的,要“群”、要“怨”。“群”,就是把大家組織起來﹔“怨”,就是把情緒、怨憤宣泄出來。
我們現在對詩歌認識有一點矛盾,以為從個人經驗出來的詩是真正的詩,其它的就不是。其實我認為,一個好的詩人,除了關注自己,還應該關注大家,關注千百萬的人民。這裡邊涉及到我提出的一個概念,即人類的情感疆界:自身-父母-血親-配偶-子女-親朋-部落-種族-全人類-動物界……情感疆界的大小及遠近,正是一個人心胸和精神境界寬窄的証明。現在我們的詩人,能寫情歌的很多,能寫國歌的找不到,我們現在就缺少大胸懷的大詩人。一個詩人應該是有思想的,好的詩人也應該是個哲人,他提供給我們的,不僅是審美的,同時也應該是啟迪的、思考的,這些是促進人類進步的東西。我這話不單包括年輕人,也包括老作家,這裡邊除了情感問題,除了理念問題,還有駕馭能力的問題。把社會經驗、社會情緒給概括起來,不是說想做就能做到的。
當然詩歌除了“群”、“怨”,還要有“興”,要符合詩歌本身的規律。我早期的 詩歌《種子啊,醒醒》、《希望之歌》都是按照詩的方式寫的,裡邊都有形象。我在1979年的另一首詩歌《路旁的核桃樹》是寫當時知識分子的狀況的:“誰給你澆過水?誰給你施過肥……秋天,人們突然發現寶貝,一根根棍子,卻為你留下悲傷。”當時知識分子群體基本都是這樣,在你的成長過程中很少有人關注你的成長,當你有了成果,批判的力量就來了。在詩中我把一種意象和人生的經驗結合在了一起。從我寫第一首詩到我詩集的最后一首寫地震的詩歌,始終按照詩歌的規律去寫,有形象和情感,同時又有一種思想在裡邊。
7. 當那種井噴式的渲泄過去之后,面對生活世界,我們就需要另一種入詩的方式。但我從1979年就開始追求用詩性的方式既思考社會,也思考生活了。我寫詩,是一隻眼睛盯著社會,一隻眼睛盯著自然。我的創作,在1979年是比較激烈的﹔但從1980年我的詩已經擴展開來了。無論是寫社會事件,還是寫生活經驗,我都從詩性興發的意象,從詩入詩,而不是從事件出發,也很少用概念的東西寫。比如《希望之歌》,希望很容易被概念化,但我卻從生活的具體體驗、細節入手。我寫希望“是實實在在的,像鐮刀,握在農民強壯的手中”,“像重錘擊打在鐘上,能發出嗡嗡的叫聲”……我把從僵化中獲得解放,寫成“種子啊醒醒”﹔到1980年我寫了許多小詩,那些詩已經非常個人化,但也有一種真正的詩出來了。那時,有了真正的文學。所以,老詩人艾青讀了,專門寫了一個評論,從形象思維的角度給予總結。像我寫《那隻雁是我》:“那隻雁是我,是我的靈魂從秋林上飛過﹔我依然追求著理想,唱著熱情的和憂傷的歌。//那隻雁是我,是美的靈魂逃脫了丑的軀殼﹔躲過獵人和狐狸的追捕,我唱著熱情的和憂傷的歌。//飛過三月暮雨,是我!飛過五更曉月,是我!一片片撕下帶血的羽毛,我唱著熱情的和憂傷的歌。”我覺得我的感情是比較凝重的。包括我后來1991年秋到前蘇聯訪問寫的《泥濘》。那時,前蘇聯的變化還沒有出現。但我已經感到了它的許多問題,從我所接觸的人們那裡,感受到了生活的尷尬和困頓。許多人隻寫人文景觀,觀山觀水。但我寫一種瞬間印象,一種情感體驗。我甚至將聽到的蘇聯的一個笑話寫進了我的詩裡。一個狗熊每天晚上都去敲打獵人的木屋。最后,木屋倒了,獵人和狗熊都被壓死了。那是怪獵人呢,還是怪狗熊呢?是誰毀了生活?這是我聽到的笑話。但我對它進行了升華,讓我們來思考,是誰毀了生活。這首詩,從一開始,就是從凝結著復雜內容的意象進入的。“其實,那座城堡/鋸齒般高聳的圍牆/已構成了險惡的背景//烏雲之手/正遮掩著教堂金頂的輝煌//十月,注定是多雨的日子麼/注定有一條泥濘的路/等待我們/濕淋淋,每片草葉上/都挂滿上帝的淚水/灰鴉,像是感冒/每一聲啼叫/都在打著噴嚏”。這首詩中包含政治,但我卻是從生活,從人的生活的深處入手,去揭示政治轉換前對人、對生活的更深的影響。我選了落雨的日子,泥濘的日子,這些都是我們從生活中感受到的。在這裡,我沒有用干吧的概念,而是從生活中凝練出活的詩性意象、畫面。詩人要將素材溫暖了,滋潤了,要找到讓人顫動的東西,然后拿出來。許多人寫詩,只是在記錄,在給人原料。那不是詩。因為其中沒有創造。所以,寫詩,是詩人不斷開掘自己的過程,要尋找思想和意象的結合,要從精神上汲取東西。就像一顆橙子,你要把其中的果汁不斷地擠壓出來。當然,有時候很難。我最近就想寫共和國走過的60年的歷史。但我嘗試了許多次,都失敗了。這中間,很可能我還沒有找到一種思想的東西,沒有發現一種觸發點,或一個豐富的意象去把握它。但沒有找到,不等於沒有。我不能很懶惰地按照時間的順序去寫。
雷抒雁詩話之四:詩歌在1980年代的轉換
8.說到1980年代的轉換。那是個很重要的問題。當意識形態並不迫使詩人必須做傳聲筒的時候,詩是否能成為詩?現在看來,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詩歌存在逐漸邊緣化的趨勢。詩不再屬於廟堂之高,就會歸於江湖之遠。這就說明,我們沒有轉換好。
當詩不在廟堂時,它是否自立為詩?所以,當詩不自立為詩時,其實就存在著詩人自身的邊緣化,一種自我邊緣化。寫詩的人自外於詩,詩在寫詩的人那裡已經沒有了尊嚴,沒有了詩的本色。比如口水詩。它不再尋求詩的尊嚴。再比如陶淵明,他雖然可以不做官了,他可以不去寫官場,但他回到了詩本身,他的個人經驗的升華。他將個人經驗變成了詩的旋律和意象,別人在他的詩句中,獲得了自己個體經驗的升華。詩人凝聚出旋律、詞語和意象,普通讀者則在這些旋律、詞語和意象中獲得普遍的經驗。古代的詩,與恐龍蛋化石是不一樣的,恐龍蛋化石已經鈣化了,沒有一點生命的信息。但古代的詩不一樣,它蘊含那個時代的信息,以及詩人的情感。我們閱讀的時候,就把我們的情感投射進去。
9.詩人必須以文字的名義站立在紙上。詩沒有政治的功利,並不等於沒有功利。當詩歌從廟堂轉向生活世界時,是否能將個體經驗轉換為詩,是否自立於詩,這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這30年中重要的問題。當詩不再將生活的尊嚴、庄重揭示出來的時候,它就立不住了。一個人無論貧困還是富有,是達還是不達,當他為詩的時候,他就必須對人生思考,而不是把詩變成下酒菜。我們在寫詩的過程中,是我們不斷和自己的狹隘性做斗爭的過程。這樣,個人的經驗就可以擴展開來,為所有人所共享。這樣,詩就像自然一樣,成為一個偉大的媒介、一個橋梁、一個管道。這就是個人經驗與社會經驗、個體的與共通的交叉起來。當我們寫個體經驗時,一定要把個體經驗中的有深度的東西,概括出來。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