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4月2日,成都,四川大學考古學教授林向向記者講述自己的求學經歷和人生故事。

2006年,林向(前排中)在重慶酉陽清源遺址川大考古04級考古發掘實習工地講授《巴蜀文化的新探索》后,在發掘現場與全體師生合影。

1981年,林向(左四)帶領川大考古78級考古實習隊赴川南考古調查,在筠連清理崖葬。

1985年,林向(左四)赴雲南調查石棺葬遺址,與重慶的董其祥(右一)、唐昌扑(左一)、攀枝花的鄧耀宗(右二)、成都的王家祐(左三)、李復華(左二)、徐南洲(右三)等諸先生於途中合影。(這組圖片由本人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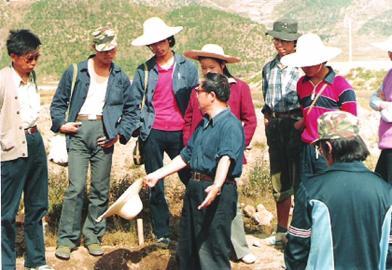
1988年,林向(前中)在四川西昌東坪冶鑄遺址發掘工地為川大考古86級考古發掘實習隊講授探方的布方原則。
4月2日,當我們懷著“探寶”的心情走進林向家中時,卻發現他的客廳裡擺的都是各式各樣的文物模型,“我沒有一件真品。”林老淡淡地說。看到我們的驚訝,這位一生都在與文物打交道的老者笑了笑:“考古不收藏,不然難免瓜田李下。”
靠近窗台的位置上擺著一張麻將桌,這是老人為祝賀妻子80歲生日專門置辦的。看到我們捏著筆記本,善解人意的他在麻將桌上鋪了一層桌板,又把桌子挪到對光的位置,這才招呼我們坐下。
隨后,這位健談的學者,將記憶中珍藏的禮物贈送給了我們——一次又一次充滿神秘的考古探險和人生傳奇。
命名大溪遺址
林向人生中的第一次考古,來得非常突然。
1958年,為配合三峽水庫建設工程,四川省博物館、重慶市博物館、四川大學歷史系合作組成了四川省長江三峽水庫文物的調查隊。當時林向是川大歷史系55級甲班班長,馮漢驥先生在給這個班講授考古學課程時,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同學們,該班本科生成了調查隊的主力。
“這是我考古生涯的開始,這次讓我的學術生涯有了重大轉折。”林向是所在小組負責人,主要負責巫山、奉節兩縣的考古調查。
1958年10月,林向到達巫山,第一站需租木船在巫峽十二峰下的急流中漂流,直到川東頂端的碚石,然后沿巫峽纖路尋覓而還。“江水很急,木船像水中的樹葉一樣打轉,下船后又需在齊腰深的水中跋涉。”林向說,當時他才26歲。
考古調查開始一月后,林向的小組到了巫山西界江南的大溪鎮,在林向后來撰寫的《三峽考古瑣記》中,記載了那次考古的詳細情況:大溪鎮西臨大溪河,在入江口與瞿塘峽口的洄水沱相遇,水面很寬,遠望發現,這裡正是林向等人要找的理想的遺址所在地。
林向等人到岸邊已近正午,久等不見渡船過來,同組的同學自持水性好,不聽勸阻竟下水泅渡,不料水冷湍急,頓生險情,幸有打魚人搭救,才到了對岸。林向等人過河后發現,斷崖上暴露出了2米多厚的文化層,白色的魚骨渣夾雜著人骨、獸骨、陶片、石器,大家都非常激動。
當天下午,他們採集到了一大堆標本,所得數量比前一月總和還多,且許多文物都是第一次發現。這個遺址后來又經6次考古發掘,每次都有新收獲。這是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首次發現,為探索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面貌,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后來,林向在自己的研究生畢業論文《巫山大溪遺址發掘報告》中,首次提出並論証了大溪文化的命名,並請夏鼐、石興邦等著名考古學家審閱,獲得學界認可。這也成為了他學術生涯中的一個重要注腳。目前,川大歷史系資料室還保存著一份1962年的論文原稿。
發現西昌大石墓
在林向的考古生涯中,有兩項考古發現是由他命名的。除“大溪文化”之外,還有“大石墓”,林向說,這是他學術生涯中最值得提及的部分。
1975年春天,由四川大學歷史系、四川省博物館和西昌縣館組成的“四川省安寧河流域聯合考古調查隊”,在西昌市正式成立。他們第一次到四川西南的安寧河谷流域時,便首先發現了這種由眾多巨大石塊組成的石堆,這些巨石曾讓他們認為,這是一處新石器時期的遺址。
但在清除坑內泥土時,林向發現了一些砂紅色陶片。接下來,考古隊員還發現了一些零散骨架。“我們認定這是人體的骨骼。它的出現或許可說明,這裡並非一座建筑遺跡的基礎,極有可能是一種罕見的古代墓葬。”
“在考古學上,墓葬的種類有磚石墓、土坑墓、火葬墓、崖葬、石棺葬等,但這個墓是以大石為主要載體砌成的,用大石來覆蓋墓頂很特別,因此我給這個古墓起名大石墓。”林向說。
西昌位於四川西南部,早在秦漢時期,這裡就曾是中國西南地區一個重要的人文地理節點,它也是古代南方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
隨著大石墓的發現,考古隊的工作重心轉向了對大石墓的調查和研究。也正是從那天開始,安寧河流域大石墓的考古工作拉開了序幕。它的文化內涵可與《史記》等記載的西南邛都夷相匹配,目前“大石墓”已成為西南民族考古的重要發現之一。
參與廣漢三星堆發掘
廣漢三星堆遺址的系統發掘是在1980年開始的,但早在1964年,林向的恩師、著名考古學家馮漢驥就對三星堆遺址做過大膽預測。
“當時馮老師喊我和他的助教去廣漢打前站,去看下哪塊有‘搞頭’,我們証明有‘搞頭’后,就決定發掘。”發掘中馮漢驥坐在月亮灣(如今的三星堆博物館的背后)那裡,指著三星堆遺址的方向說:“你看,那裡氣象萬千,很可能有重要的遺址。”事實証明,馮漢驥的預測是對的。
后來,大量廣漢農民在遺址附近興建起磚窯,“他們在燒磚挖土時,挖出很多古代陶片,這些都是真東西,一看就有很大的歷史價值。”為搶救歷史遺跡,1980年,三星堆遺址開始了發掘,作為分批進行項目,林向參與到1986年的發掘中。
說起這次發掘,還有一段趣事。林向說,發掘現場揭露面積達1325平方米,當時現場工作的實習學生等人員大概100多人,很多人都穿著皮鞋,有些女學生還穿著高跟鞋。”如任意進出,會對考古現場造成極大破壞,為保護現場,林向下了死命令,“全部換成平底鞋,否則一律回家。”
於是就出現了有趣的一幕:廣漢的布鞋一夜熱銷。“雖這是一件小事,但后來國家文物局的專家對該做法大為肯定。”當時參與發掘的很多學生,后來都成為各考古文物部門的骨干。
從1986年3月到6月,林向帶的實習隊負責的發掘工作很快結束。就在他們走后不久,后續接手團隊發現了著名的三星堆遺址祭祀坑。
這次發掘的作用很快就體現出來了。
據碳測年代分析,三星堆古城的始建至廢棄年代,在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000年間。但三星堆消亡的原因一度成謎,經多年研究,林向發現答案藏在淤泥之中。
在1986年的發掘中,林向就特別研究了文化層中厚實的淤泥沙。典型的層位在三星堆土堆旁的第三發掘區,文化堆積可化為16層,其中13到16層相當於龍山時代的(后命名為“寶墩文化”)堆積﹔8到12層相當於夏商時期的古蜀文明的“三星堆文化”堆積,遺跡遺物非常豐富,城址和祭祀坑的地層年代可分別插入其中。
緊接著三星堆文化層上之上的7層,卻是厚約20厘米到50厘米的洪水淤積沙泥,包含物極少﹔再往上內容物更少。林向對這些泥沙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分析,“問題就出在第7層厚達50厘米的淤沙泥上,從埋藏學角度分析,這麼厚的沙層必然是長期被洪水浸泡的結果,故可以說是洪災中斷了三星堆古代文明,三星堆作為中心聚落成為了過去。”
那三星堆文明是否有延續和繼承?林向大膽預測,“失落的三星堆文明不可能就此湮滅,肯定能找到文明的延續。”在對金沙遺址的發掘中他發現,金沙遺址群的房址與三星堆遺址一樣屬於“木竹骨泥牆”式建筑。而祭祀用品中,兩者出土了同樣的金玉銅器和象牙,另外,祭祀坑等遺跡也是一脈相承。
后經多年考古發掘証明,金沙遺址的主要文化年代相當於商晚期到春秋早期,三星堆文化的年代約相當於夏商期至商代晚期。故年代上,兩者是緊密銜接的,雖略有重疊,但可肯定三星堆遺址在前,金沙遺址在后。比較兩地發現的遺跡、遺物,能發現從三星堆遺址到金沙遺址間,有明顯的文化承襲與發展關系。這就証實了古蜀都邑遷徙的推想。
小酒杯中探析川酒文化
地處成都平原的古蜀國,同中原殷商王朝一樣,釀酒技術和酒事活動都相當發達昌盛。在主持三星堆遺址發掘的過程中,林向發現很多樣子小巧的酒杯。“如酒的度數很低的話,拿這麼小的杯子喝酒是不合理的,這說明用這種酒杯喝的是高度酒。”一個小酒器引發了林向對酒文化的研究。
翻閱大量資料林向發現,成都平原出土的古蜀銅酒器已有一百多件。其中最有特色的是銅鍪,銅鍪是巴蜀酒具中的特產,是起源巴蜀而流布各地的溫酒器。這說明,蜀酒文化自先秦來不僅發達,且對周邊區域有一定的影響,因此撰寫了《蜀酒探原》等一系列文章。
川內地震考古第一人:
成都歷史上,未發生過大地震
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周恩來總理建議學術界是否也可參與到預報地震的隊伍中。這引發了林向的思考。林向認為,從地質力學的角度分析,地震發生的地方會不斷重復發生地震,因為大地有斷裂帶,有斷裂帶才會有地震。換句話說,如歷史上發生地震的地方就可能會重復發生。
1976年的唐山地震,巨大的破壞性又一次警示全國。當時,成都地震局專家邀請了林向參加了專題討論,主題為,應對地震,成都基本建設要不要加固?而如果加固,地震烈度提高一度,國家投資就要增加15%。
“正在一頭霧水時,一盤錄像帶點醒了我。”當時,大家在觀看唐山大地震的錄像帶,林向對畫面中的煙囪產生了濃厚興趣。“我發現一個特點,因唐山地震的震中在城裡,所以很多大煙囪都往城中間的方向倒。這是為什麼?地質專家告訴我是地震波的原因。因此,高層建筑就往震中方向倒,這啟發了我。”
通過大量的現場調查和文獻研究,林向和學生們得出結論:歷史上,成都地區沒發生過大的地震,最高沒有超過7度,主要是受龍門山斷裂帶的波及。后來,林向參加了《中國地震歷史材料匯編》和《四川地震資料匯編》的編撰,使用考古材料進行歷史地震研究,后者還獲得四川省社科二等獎。自此,林向開創了巴蜀地震考古的新領域,成為川內地震考古的第一人。對話巴蜀考古
改變中華文明起源格局
華西都市報:您在川大考古專業掌舵30余年,能談談您的教學理念嗎?
林向:我對學生的要求有三方面:識、才、學。馮漢驥先生曾對我說,學問有兩種境界,一種是曉得一個問題該怎麼去查書、哪裡去找資料來解答,也就是知道解答問題的路徑﹔還有一種是融化在研究者的血液中,下意識就能夠反應出來,這才是真正的知識。
華西都市報:天天與古物打交道,但考古似乎是一個冷門專業,您怎麼看?
林向:考古學現在已經不冷了,在川大有很多其他專業的學生都想轉來學這門課程。考古絕不只是埋頭做研究,每一次田野調查、遺跡發掘都像探險一樣,而一旦有所收獲,又能通過眼前的古物與古代的人、事相連接,樂趣很多。
華西都市報:那一個合格的考古人應該是怎樣的?
林向:我覺得一個合格的考古學工作者,白天要能在田野摸爬滾打,沾一身泥巴,要會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會抽煙會喝酒,和當地人稱兄道弟,具備很強的交際能力。
而到了晚上,要能挑燈夜戰,讀書、寫文章,做記錄,把白天得到的東西轉為知識,這是必須具備的兩個要素。同時,知識面要寬,天文地理都要有所涉獵,從多維視野去進行考古研究。
華西都市報:您在古蜀文明研究領域做了這麼多年的研究,又是三星堆文化的發現者之一,對目前發現的古蜀文明遺跡,您如何理解?
林向:以四川盆地為中心,北跨陝南盆地,東到江漢平原西側,南到雲貴高原北緣,這是三星堆典型器物所輻射到的區域,構成了一個巴蜀文化區。我們發現文化區裡的好多圖像都有承襲性。
巴蜀文化區的研究,說明成都平原是長江上游古代文化中心,應在中華文明起源格局中佔有一席之地。三星堆文化的發現突破了這一點,推上去還有史前的寶墩文化,后面還有巴蜀文化,它們一脈相承。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