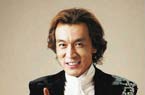今年入夏,從倫敦到維羅納,從薩爾斯堡到佛羅倫薩,全球紀念歌劇大師朱塞佩·威爾第誕辰二百周年的活動如火如荼。在中國,在“威爾第萬歲!”(VIVA VERDI!)口號的感召下,國家大劇院一系列紀念威爾第誕辰200周年的演出也應運而生。
今明兩天,國家大劇院特別策劃的、世界級大師烏戈·德·安納打造的威爾第200年特別獻禮——威爾第“折子戲”音樂會上演。這台集結10位著名的華人歌唱家以及3位意大利優秀藝術家,曲目選自威爾第24首著名唱段出現在節目單上。著名影視演員張國立也將登台當起這場音樂會的義務講解員。9月5日至8日,國家大劇院制作的威爾第歌劇《假面舞會》將再度上演。世界著名歌劇演員羅伯托·阿羅尼卡和羅伯托·福隆塔裡攜手華人歌唱家戴玉強、和慧、孫秀葦、廖昌永和郭森,締結夢幻明星陣容。
曾被米蘭音樂學院拒之門外
1813年10月10日,一個男孩在意大利北部帕爾瑪公國布塞托附近的一個小鎮上出生了,他的父親是當地的旅館主人兼食品商,雖然沒有淵源家學,但這個孩子從幼年時期就顯現出了很高的藝術天分,父親便送他去家鄉的管風琴師那裡學習音樂,當時誰也不會想到,一代歌劇巨匠由此誕生了……他就是作曲家威爾第。
在威爾第88年的生命中,他的藝術創作貫穿了19世紀的大半個世紀,共創作出26部歌劇。即使歷史走到了21世紀,屬於19世紀的威爾第的名字依然被歌劇愛好者們崇敬,他的作品依然雄踞於世界舞台。今年是威爾第誕生200周年,在這樣的日子裡,我們應該向他致敬,向他崇高永在的音樂致敬,向他永遠不會離去的身影致敬。
“很多大師常常在死后獲得名氣和受到世人的尊敬,生前他們的藝術往往不受理解,生活也很落魄,但威爾第是罕見的在有生之年既有名氣又富有的大師”,國家大劇院歌劇藝術顧問朱塞佩·庫恰這樣評價威爾第。有意思的是,記者連續問到兩位專業人士,他們對威爾第的評價和庫恰驚人的一致。
不過威爾第在成名之前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比起很多出生於藝術世家的人不同,威爾第就是個普通家庭的孩子,但威爾第幼年的時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音樂迷,在他8歲的那年,他的父親在教堂裡做彌撒時看到小威爾第對管風琴如醉如痴的樣子,便省吃儉用給他買了一台舊的斯比奈風琴,因為便宜,那琴本來已經是破爛不堪了,誰知沉默的他迷上了那台破風琴,整天瘋了似的在上面彈奏,沒過幾個月琴就讓他給彈得徹底散了架。威爾第是教堂合唱隊的一員,他參加小教堂的彌撒儀式,第一次聽到管風琴的演奏,美妙的天籟令小威爾第如痴如醉,以至於神父命令他拿水的時候他都渾然不知。可憐的小威爾第被神父推下了聖壇,當場就昏迷不醒。然而小威爾第正是因為這次經歷,立志要學習音樂。
威爾第的父親很開明,也很為兒子的音樂天分感到高興,於是送他到家鄉的管風琴師那裡學習音樂,並且在他12歲時將他送到了距離米蘭不遠的布塞托去讀書。
在布塞托,威爾第遇到了生命中的伯樂,也是他后來的岳父安東尼奧·巴雷奇。當威爾第18歲時,巴雷奇出資將他送到米蘭音樂學院深造,但是由於威爾第的鋼琴功底差,理論知識也不夠等原因,他被米蘭音樂學院院長拒之門外,但他並沒有放棄音樂。威爾第在米蘭的兩年中,請私人教師教授作曲與配器,並開始創作歌劇《奧貝爾托》,修改后的《奧貝爾托》於1839年在米蘭斯卡拉歌劇院上演,廣受好評。
一度成為了意大利精神代表
庫恰和威爾第同為意大利人,他對威爾第的了解比其他國家的人有更深切的感受,他認為威爾第在世時能夠名聲和利益兼得,除了藝術水准高之外,對他個人發展有極大幫助的還有當時意大利的歷史背景,也就是所謂的“時勢造英雄”。
威爾第是在29歲創作了歌劇《納布科》之后迅速蜚聲全國的,他當時獲得了幾乎所有民眾的喜愛,也贏得了很多劇院長久而熱烈的邀約,自然也賺得缽滿盆滿,這部戲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是唱出了民眾的心聲。
在1840年到1860年之間,是意大利歷史上殘酷的反動年代,法國與奧地利的先后統治激起了意大利人民的強烈反抗。當時真正意義上的意大利是不存在的,意大利的區域分成很多小塊,由伯爵侯爵們各佔一方,而且很大的領土都控制在外國人手中,在這種四分五裂的狀況下,意大利人心裡有強烈的統一願望,各個小國的國民也有統一的訴求。此時威爾第的《納布科》上演了,他在音樂中表達了對統一的要求和對國家的熱愛,雖然《納布科》中故事發生在一個遙遠的,甚至是想象中的國度,但其中反對外來侵略、反對壓迫的民族和民主精神讓觀眾深感共鳴,劇中有一首合唱《飛吧,讓思想乘著金色的翅膀》,受到觀眾的狂熱歡迎,歌劇散場后,人們從劇院涌到大街上,高唱這支歌曲游行。
《納布科》的音樂樣式也非常新穎,據當時的報道,《納布科》在彩排時,由於音樂的奇特與新潮,當時劇場裡進行演出准備工作的所有工作人員、工匠和畫師,都被聽到的音樂打動了,他們不約而同地放下了手裡的活計去觀看彩排,目瞪口呆地站在那裡看著舞台上發生的一切,劇場內部工作完全停止。第二天,歌劇正式公演,米蘭人爭著去看演出。米蘭市民向來自詡歌劇欣賞水平很高,卻都為這位年輕藝術家的音樂所折服。他們馬上斷定:一個真正的天才誕生了。威爾第自己也認為:“隨著這部歌劇的誕生,我的藝術生涯才真可謂開始了。”
在這之后,威爾第的音樂一度成為了意大利民族精神的代表,而威爾第本人,則被意大利人視為統一意大利的精神領袖,連他的名字,都被認為是全國統一的象征。在城內城牆上,曾寫有無數的“Viva Verdi”(威爾第萬歲),隱含著“意大利國王V·I萬歲”的意義,因為Verdi這五個字母,正是“意大利的國王維多利奧·埃瑪努埃勒”一語的縮寫。
“威爾第萬歲”,既歌頌了這位作曲家,也表達了人民對堅決驅逐外國侵略者、統一意大利的國王的擁護。
事業登峰造極生活很不如意
雖然在藝術上獲得如此高的聲望,物質上也非常豐厚,但生活對威爾第還是不那麼公平。威爾第28歲時就遭遇了連續失去妻子和兩個孩子的痛苦。在威爾第生活的時代,歐洲的醫療條件很差,兒童的死亡率很高,誕生的孩子每三個中就有一個會夭折,成年人的平均壽命也就在50歲左右。威爾第最先失去的是他一歲的小兒子,緊接著兩歲的小女兒也因病死去了,威爾第的妻子無法承受如此大的打擊,也身患重病,不治而亡。至親一個接一個地離去帶給威爾第巨大的打擊和傷痛,接觸過威爾第的人都覺得他性格並不好,給人感覺非常難相處,不通情理,極端完美主義,這很大程度上源於28歲這年生活上的打擊,這對他的一生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威爾第的人生中有不少情人,其中最重要、對他影響最大的是朱塞比娜·斯特列波尼,威爾第到巴黎發展歌劇時遇到了朱塞比娜,她是紅極一時的女高音歌唱家,曾幫助威爾第的事業。但是因為朱塞比娜私生活上的不夠檢點,他們的愛情並不被威爾第的父母和鄰居理解,於是威爾第帶著朱塞比娜搬進一所鄉下的農庄,過著與外界隔絕的隱居生活。但是當地居民也為朱塞比娜感到恥辱,在往后的幾年裡,她成為小鎮人們說閑話的對象,飽受冷言冷語和人際關系的孤立。
威爾第和朱塞比娜交往多年,一直到70多歲才和威爾第結婚,但是朱塞比娜卻沒有從威爾第那裡得到任何財產,威爾第把自己的所有財產都給了他收養為養女的侄女,直到今天有關威爾第家族的一切都是從他的侄女的后代傳下來的。
威爾第是個奇怪的人,這位創作出《阿依達》、《茶花女》、《歐那尼》、《游吟詩人》、《奧賽羅》……將19世紀意大利浪漫樂派的歌劇藝術推向頂峰的作曲家,在填寫自己職業欄的時候,從來不填“作曲家”,而是“種地的農民”。他在歌劇創作上收獲了不少財富,拿著這筆錢,他離開了米蘭,跑到他最喜愛的鄉村,去買田地和豬圈,過著真正農民的生活。他在鄉村親自種植遍野的薔薇,養殖野雞和孔雀,並讓它們繁殖出一窩窩小崽。他還養了起名叫做盧盧的狗﹔他還想培育叫做威爾第的新品種的良馬,為此到農村的集市像模像樣地去挑馬……沒有一個音樂家如威爾第一樣真的把鄉村當成自己的家,自己的歸宿,而和城市如此格格不入。
威爾第很慷慨,他最好的一部作品並不是哪部歌劇,而是自己出資在米蘭建立的退休藝術家療養中心,讓生活貧困的藝術家在這裡養老。這個機構特別偉大,直到今天還在發揮作用,全部由威爾第基金會出資。
當然對一個音樂家來說,威爾第對音樂的影響還是最大的。如今每個歌劇院每年排期表上都有威爾第,很多歌唱家更是因威爾第的歌劇而出名。庫恰的妻子便是一位歌唱家,她就是因為與帕瓦羅蒂主演《假面舞會》一炮打響的,給她開啟了一段非常美好的事業,她要感謝的正是威爾第。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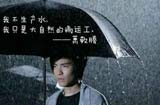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