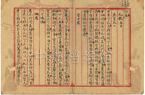年輕時的紅線女
為粵劇而生為粵劇而活 為推廣粵劇不遺余力
12月8日,紅線女辭世,在粵劇界引起極大震動。從14歲拜師學藝,女姐的一生都奉獻給了粵劇。她對后輩更是愛惜有加,晚年更在編劇、演員培養、支持各劇團建設上做了大量工作,不遺余力地推廣粵劇,就在離世的前一天她還在給學生們上課。
昨日,本報採訪了粵劇圈內多位知名人士,他們在追念前輩的同時,也在思考粵劇的未來,“誰能接過紅線女的大旗?是留給后人的一大問題。”
76歲時,紅線女初學電影隻為讓孩子們多接觸粵劇﹔84歲,她帶著200多名小粵劇迷練“百日功”,為街坊奉上精彩的新年演出﹔87歲,她與“小紅豆們”一起荔枝鄉裡頌荔枝……
昨日上午,年過八旬的從化民間粵劇團——“小紅豆粵劇團”團長冰姨接受本報專訪,講述紅線女關注“鄉村兒童粵劇傳承”鮮為人知的故事。
托起“小紅豆”的傳承夢 古稀之年玩電影 動畫教娃學粵劇
一句“不因急雨驚春燕,自有皇凰乘秋雲”未唱完,從化民間粵劇團——“小紅豆粵劇團”團長、紅線女的老友冰姨已淚眼婆娑。
這一句,正是紅線女第一次來“小紅豆”時,給小團友們上的第一節粵劇課所唱。
昨日,冰姨向記者講述,紅線女來劇團那天,孩子們看到了世界第一部粵劇動畫電影《刁蠻公主憨駙馬》。她回憶,紅線女當時告訴孩子們,望把經典粵劇做成動畫片以培養孩子們的興趣。
初學電影時,紅線女已76歲。在《刁蠻公主憨駙馬》中,紅線女老師任編導、監制並為片中“刁蠻公主”配唱。該片歷時四年完成,獲第十屆中國電影華表獎優秀美術片獎。
心系民間粵劇發展 為孤兒種下藝術夢
“她對孩子非常細心,一眼就看出誰喜歡粵劇,而且一定要幫那個孩子實現夢想。”冰姨動情地說,孤兒馮斌的藝術之門最初就是由紅線女開啟的。
4年前,當時19歲的馮斌第一次聽紅線女唱粵劇就喜歡上了粵劇。冰姨回憶,當時馮斌較?腆,紅線女來到“小紅豆”粵劇團那天他很開心,“眼睛裡一直亮亮的。”冰姨說。表演結束后,紅線女親手將DVD送到孩子們手中。冰姨后來得知,那盤DVD,馮斌反復看了不下百遍。
如今馮斌已回到家鄉江門,在當地粵劇團已小有名氣。他曾告訴冰姨,如果不是紅線女老師,他就不可能找到自己的夢想。
兩年前,已近九十高齡的紅線女再次來到了從化,已87歲高齡的紅線女再次登台表演《荔枝頌》。
記者了解到,2006年2月,冰姨等老年粵劇愛好者,組織一批“小紅豆”藝術團,如今已輸出13名好苗子到省粵劇學院就讀。
84歲親自授演技 帶小孩練“百日功”
令冰姨印象深刻的是,紅線女曾多次說要幫孩子們培養粵劇文化的根。
5年前,在友誼劇院舉行的一場少兒粵劇新年晚會上,由荔灣區200多個孩子擔綱,挑戰粵劇藝術的瑰寶——“紅派”粵劇。當晚表演非常完美,但是鮮為人知的是,這場精彩的演出背后,是紅線女帶著孩子們練了3個月多的“百日功”。
原來在那年9月初,當紅線女得知此次活動主要是孩子們擔綱后,主動提出讓他們到紅線女藝術中心排練。每到周末,紅線女不厭其煩地給孩子們做示范,作講解,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哪怕只是一個細微動作、一個嘆氣聲或是音准偏低的唱詞,她都仔細地手把手教,耐心帶唱。
而孩子們也十分努力,一個動作經常要練幾十上百遍。經3個月的排練,終於在當晚的舞台上大顯身手。
文藝界追憶(上海)
瓊劇表演藝術家陳育明:優美“紅腔”讓我受益匪淺
瓊劇表演藝術家陳育明與紅線女有過多次交流,他甚至記得,1959年粵劇大師馬師曾、紅線女曾在欣賞完自己的演出后,送給自己一個雅號——“金嗓子”。他回憶:“我對紅線女一直心懷感恩,她作為前輩,雖屬不同劇種卻不忘提攜后輩。”
得知紅線女離世后他十分震驚。“是紅線女與馬師曾二人一起將粵劇從一個地方劇種提升至海內外著名的劇種。尤其是紅線女創作的‘紅腔’,將粵劇固有的旋律、板腔等與現代藝術相結合,優美動聽,不僅受到粵劇迷們的喜愛,也讓我們兄弟劇種的演員們受益匪淺。”
(記者李曉璐)
業內惋惜
廣東粵劇院院長、國家一級演員丁凡:她把粵劇推向全世界
丁凡說,紅線女是中國戲劇界的標志性人物,“她把眼光放得很高,她要把粵劇推向全世界,她對粵劇非常專注,每次和你聊天都是關於粵劇,有人會覺得她脾氣怪,不理解,那是因為想法不一樣。她是一個可愛的老人。”
他認為紅線女非常值得敬佩,“很多人退休就開始住別墅,徹底離開粵劇,但她雖然年紀很大,但從未離開粵劇,一直在培養人才。雖然她已經退休,但我們粵劇院大大小小的活動她每一次都參加,每一出新戲都要來看,而且一定要開座談會,當面給后輩說戲。”
廣東粵劇院的大劇場建設曾因資金不足而面臨中斷,紅線女隨即寫信給時任省委書記汪洋,最后得到批復,大劇場也順利竣工,並在12月8日試業,“本來她答應了要來捧場,而且點名要我們演《六國大封相》,后來說身體不舒服就沒來。她走了,我們都很舍不得。”
談到紅腔流派,丁凡說:“大部分女演員都學,甚至全世界都在學,但要超過她很難。”
梅花獎得主、國家一級演員曹秀琴:她像媽媽一樣提攜后輩
曹秀琴和紅線女的師生緣分是從粵劇學校開始的。當時曹秀琴隻有11歲,又是從農村來的,很多次都被紅線女拉到同學前面唱,緊張的她即便唱錯,覺得自己不爭氣當場大哭,紅線女都會安慰她。“老師對我很疼愛和照顧,給我開小灶,我天生聲音渾厚,其實唱紅腔不是很合適,但她說學我的東西要‘舍我其誰’,能發揮自己就更好,讓我去開拓自己的東西。感覺像媽媽一樣可親。”
畢業以后,紅線女仍然很提攜后輩,“晚上一兩點還打電話過來,問有什麼難處。這幾年我工作沒那麼忙,就和她喝茶聊天。能做老師的學生,是我一生的幸運。”
11月26日,為了慶祝弟子們畢業40周年,紅線女還和大家在中山紀念堂一同演出。曹秀琴當晚表現很出色,紅線女一上來就吻了她,最后1000多人一起唱《荔枝頌》,場面很感人。到了12月7日早上,紅線女還給粵劇學校的同學講課,覺得表演方面還有很多不足,要繼續努力。“她對我啟發很大,她教導我們靜下心來才能出精品,質量搞好了才有市場。”
長年跟隨紅線女的知名編劇梁郁南:最焦慮粵劇后繼無人
本土知名編劇梁郁南近幾年長期在紅線女身邊工作,12月7日還和紅老師一起研究工作,約定12月9日到紅線女藝術中心當面匯報,可老人家卻走了。梁郁南極度惋惜:“紅老師心中還牽挂著粵劇的許多事。”
“紅老師曾說對粵劇要有愛,有愛就能搞好粵劇,對推廣粵劇不遺余力。學校、街道、農村,不論是高雅的劇院,還是簡陋的鄉下戲棚,我們都能經常看到她的演出﹔無論是對小學生,還是劇團的青年演員,我們都能聽到她誨人不倦的教導。”梁郁南說,晚年的紅線女最焦慮的就是后繼無人的現狀,尤其是粵劇編劇的培養。
數年前,她請求時任省委書記張德江支持開辦為期三年的粵劇編劇高級研修班。她說,粵劇要發展,就一定要創新,要創新,首先要有劇本。
“前年春節剛過,她就讓我召集有志於粵劇編劇的年輕作者‘談心’,就如何培養粵劇編劇出謀劃策,急切之情和殷殷期望令在座的領導和作者動容。”在紅線女的大力促動下,“廣州市戲劇創作孵化計劃”得以實施,由此產生了一系列包括《碉樓》在內的新編劇目。
省藝術研究所所長、著名粵劇評論家梅曉:誰能接過她的大旗?
梅曉認為,紅線女老師的離世對粵劇界是極大的損失,粵劇能走到今天,這個旗幟性人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於各種原因沒有建好人才梯隊,這是關乎粵劇生死存亡的關鍵問題,“我們要借祭奠逝者的機會,呼吁行業認真思考粵劇的未來。粵劇界現在缺乏旗幟性人物,連靠近她水平和地位的人都沒有,必須有人扛起她的旗幟,否則粵劇的衰亡難以避免。”
他說,要學習紅線女對粵劇的熱愛,“她的一生為粵劇而生,她在利益面前毫無所動,耐得住寂寞,比如有一個老板請她做戲,但這個戲會損害到戲劇本身,她就會拒絕。”
其次,他認為還要學習紅線女的鑽研精神,“紅腔的成就就是因為她吸收了很多創意,忠於粵劇本體,敢於嘗試其他東西。包括她在香港拍默片,隨后把拍電影的手法融入到粵劇之中,使之更加豐滿。”
“昨天晚上在電視上看到了她去世的消息,今天走著走著就到這裡來了。”昨日中午,開平市水口鎮泮村鄉向北村村民鄺叔來到了村裡“紅線女”的祖屋前,看著已經顯得衰敗的房子發了一會呆,慢慢轉身離開。
“我見過她三次。”鄺叔回憶,最后一次見“紅線女”是在2007年,回鄉助開平碉樓申遺的“紅線女”回了一趟向北村的祖屋,當時來了很多嘉賓。而在1992年祖屋重修入伙時,“紅線女”不僅從廣州帶回了四棵木棉樹,還親自栽種在祖屋門前,很隨和地與鄉親交談。“我們現在很多老人都在聽她的粵劇,她是我們鄉的驕傲。”
文/記者陳杰、黃國金、黃文生
家鄉曲藝陷入低潮 開平女兒帶團回鄉連演四晚
“開平失去了一名好女兒!”開平市戲劇協會名譽主席張巨山昨天對記者說。昨晚,不少粵劇發燒友聚集在開平市中心廣場,一起唱起《賣荔枝》,向記者講述紅線女回鄉故事。
開平走出藝術大師
開平市戲劇協會名譽主席張巨山對紅線女有很深的感情,退休后,他連續寫了3本書,介紹紅線女的生平及對家鄉及粵劇界的貢獻。他說,一直以來,開平就是曲藝之鄉,從開平走出去的,有紅線女、鄺新華、關國華、關德興等曲藝大師。新中國成立前后,開平市各鄉村唱戲成風,許多鄉村都有劇團,或者私伙局,張巨山所在的開平六合村,其中6條鄉村都有粵劇團。“當時,開平除了唱粵劇外,開平民歌在開平也十分流行。”“賣雞調”、“小賣雞”等開平民歌,許多小孩都會歌,而紅線女在12歲離開家鄉時,深受家鄉民歌的感染,對家鄉自然有很深的情結。
粵劇團一度准備解散
“開平的曲藝發展與紅線女的關心支持分不開的。”開平市原粵劇團的團長李雲仙與紅線女有深厚的感情,李雲仙與紅線女是在1992年認識的。“那時候,粵曲受到電視電影的沖擊,家鄉的曲藝事業到了最低潮的時候。”“粵劇團准備解散,在這關鍵時候,我找到了紅線女,給她匯報了情況。”“你們一定要堅持!”紅線女對她說。
紅線女親自登台獻唱
“那是1992年,紅線女帶著徒弟郭鳳女,以及小紅豆藝術團40多名團員,來到開平為家鄉曲藝事業打氣。李雲仙回憶,那時候,小紅豆藝術團一連在開平表演了4晚,好戲連台,場場轟動,小小一個劇院,連門口都站滿人,人們聽說紅線女回鄉,紛紛涌來觀看,場面十分壯觀。
68歲的紅線女親自上台,女扮男裝表演《搜書院》,而在第二晚,紅線女還登台,為家鄉人民獻唱《荔枝頌》。
為靚嗓天天噴魚腥草
原開平藝術團團長李雲仙很佩服紅線女對藝術的執著。
她說,紅線女生活十分有規律,對飲食、作息都十分有講究,早餐吃的是冬菇撈面,每天吃兩隻雞蛋,為了保持聲線,她每天都要用“魚腥草”制劑進行噴喉。每天飯后都要散步,可能是在晚上失眠,下午需要休息,而休息時一般很少接見外人,因此,一些人會說她“高傲”,其實是不了解紅線女的生活規律。
紅線女曾經說過,“其實保持好的身體,就是有更多的時間,更多的精力投身曲藝事業,而許多人不理解我。”
文藝界追憶(廣東)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黃天驥:完美“紅腔”后繼難有人
黃天驥表示,紅線女的去世是中國戲劇界的重大損失,她對粵劇發展的貢獻不可磨滅,對擴大粵劇在海內外的影響貢獻巨大,對培養粵劇接班人也付出良多。
在黃天驥看來,紅線女對粵劇的最突出貢獻是唱腔領域的創造性革新。她創造的“紅腔”,將粵劇唱腔演繹到非常完美的境界,對粵劇有繼承更有創新,在粵劇唱腔的藝術性上可說是達到巔峰。黃天驥認為,紅線女在表演時的發聲方法和發聲部位與傳統演員頗有不同,她吸收了西洋歌唱的發音方法,這不是每個粵劇演員都能做到的,估計以后要達到這個境界很難。
(記者徐靜 通訊員黃愛成)
著名雕塑家潘鶴:她的“青春”從70歲開始
新中國成立前后,潘鶴與紅線女相識於香港,當時,紅線女已是非常活躍的知名藝人。潘鶴回憶,“后來我回到廣州,大家一起回到內地發展文藝,相見不多卻很投契。”
潘鶴說:“我和紅線女接觸較多倒是在我們70歲之后。她很有活力,很活躍,仿佛這時 (70歲)她的青春才剛剛開始。我一直以為她比我小,直到今天,她過身,我得知這個消息,在報紙上看到,她原來比我還大一年。”
“最近十年,我們常常一起參加文代會等活動,她每次必到,也有很多創新的想法,在我心中她永遠是年輕時的樣子,那麼活力活躍。”(記者譚秋明)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