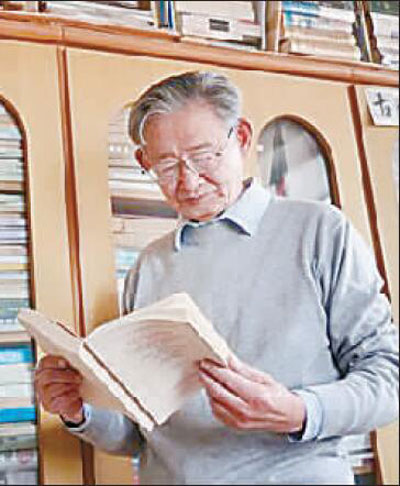
羅新璋 資料圖片
1980年,44歲的羅新璋從中國外文局《中國文學》雜志社調入中國社科院外文研究所,從事法國文學研究。當時很少有人知道,這位在雜志社做了17年中譯法的學者,其實對法譯中情有獨鐘。早在青年時代,他就與著名翻譯家傅雷通信往來,還花了4年時間手抄200多萬字的傅雷譯文。外文所前輩錢鍾書點撥他:“照你的情況,不如翻譯幾本喜歡的法文書。”於是,羅譯本《特利期當伊瑟》《列那狐的故事》《紅與黑》《栗樹下的晚餐》《巴黎公社公告選》接踵而至,“傅譯傳人”的美譽在讀者和學界流傳開來。
站在傅雷的肩膀上
“我的翻譯全靠學習傅雷,才有了一些小本領。”羅新璋回憶,1957年他從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法語專業畢業,受“反右”影響,沒能去成原定的分配單位人民文學出版社,而是進入了國際書店,整天與訂單、發票打交道。在這種情況下,他開始利用業余時間系統學習傅雷的翻譯。
1960年,羅新璋在東單市場發現了一部法文版十卷本《約翰·克利斯朵夫》,要價35元。當時,他的工資不過每月46元,但羅新璋還是攢了兩個月的錢,買了下來。
“最初,我是對照原文看傅雷的翻譯,把一些好的譯文抄在法文書上。沒有這套書,就沒法抄進去。”羅新璋做了一個統計,從1949年到1960年,傅雷總共發表了275萬字的譯文,而他抄了255萬字,“有20萬字譯文沒抄,那是因為我買到的法文書行距太窄,寫不進去字,但也做了筆記”。
羅新璋嘗試著把自己的習作寄給遠在上海的傅雷,很快收到了回信。面對這位素不相識的年輕人的習作,傅雷沒有客套應付,而是嚴肅地指出了問題:單獨看每個句子,譯得都沒錯,但是通篇來看,每個句子各自為政,不夠連貫。傅雷教給他改進的方法:自己作文寫信,行文往往會比較流暢,翻譯作品可以從中得到借鑒。
經過四年磨礪,對於傅雷譯作中的經典譯法,羅新璋已爛熟於心。《紅與黑》中有一句話,如果依照法文直譯,可以譯作“用一種外交家的神情看著妻子”,但他會想到《歐也妮·葛朗台》中,傅雷把一句類似的話翻譯成“老謀深算地看了她一眼”。
“傅雷的翻譯重神似而不重形似,把原文的內涵表達出來了。”羅新璋說,在傅雷200多萬字的翻譯中,有不少這樣的句子,有的讓他受到啟發,有的甚至可以借用,“我站在傅雷的肩膀上,稍微佔了點兒便宜。”
2004年到2006年,羅新璋應邀赴台灣師范大學講學。羅新璋用一個學期的時間,從傅雷的翻譯中選出200個例句,分成20種譯法,向台灣學子介紹傅雷的翻譯方法。
“年輕人看到傅雷是怎麼翻譯的,就會有所啟發,比較容易進入。這些例句是從200多萬字中像大海撈針一樣撈出來的,如果出書的話,擔心不全面,需要進一步完善。”羅新璋希望,天假以年,能把這項工作盡早完成。
“苦讀”之后是“苦譯”
在台灣講學的三年,羅新璋還做了件“出格”的事——編了一部《古文大略》。
“做翻譯,外文好當然是基礎。傅雷的翻譯之所以好,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法文好,理解得深。但是搞外譯中,中文也要好。有時候,我們能體會原文的意思,但如果中文的詞匯量不夠,就表達不出來。”羅新璋認為,中文能力的養成需要靠長期閱讀積累,熟讀古文選本是一條捷徑,但對於外語專業的學生來說,閱讀《古文觀止》等古代選本中收入的先秦古文,存在一定困難。於是,他根據當下青年翻譯的實際情況,編寫了這部180篇文章的《古文大略》。
“《古文大略》選文以漢以后的文章為主。劉師培在《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中說‘非偶詞儷語,弗足言文’。提高翻譯的文採,這也是一個取巧的辦法,所以還選了15篇駢文。”為了讓青年人了解中國古代的翻譯思想,羅新璋還把支謙的《法句經序》、嚴復的《天演論·譯例言》等翻譯文獻收入其中。
平時上網,看到一些年輕人把外國的詩歌翻譯成典雅的“詩經體”“離騷體”,羅新璋感到很欣喜:“江山代有人才出。我們那時候是苦讀的辦法,有所本才能有所發揮。”
羅新璋不僅年輕時“苦讀”,年近花甲翻譯《紅與黑》,也堪稱“苦譯”。那時,他每天早晨4點到7點連續工作3個小時。大部分的時間不是翻譯,而是反復閱讀《紅與黑》的法文原文。
“后來我總結了一下:這是‘悟而后譯’。看了原文,自己有了感悟,再把它譯出來,而不是照著字典翻譯。”按照每天1000字的速度,羅新璋用了兩年的時間,數易其稿,才最終交出《紅與黑》的譯文。
如今,在市場的驅動下,譯作的出版周期往往非常短,留給青年譯者“苦讀”“苦譯”的時間越來越短。在羅新璋看來,人的才思不同,翻譯的速度有快有慢,但對待翻譯的態度都應該是認真嚴謹的,“傅雷比較花工夫,他的文字也很講究。朱生豪就曾用一年的時間翻譯了18部莎士比亞戲劇,其中的《哈姆雷特》至今無人能及。”
羅新璋希望,青年譯者能本著對原稿負責、對讀者負責的態度,更加謹慎小心,少犯一些不必要的錯誤。
(本報記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