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的明代邊景昭 《竹鶴圖軸》
本報記者 范昕
今天,隨著電影紀錄片 《我在故宮修文物》的上映,修復師這一隱藏在文物背后不為人所知的群體,再次被推向大眾視野。他們的技藝令人驚嘆———與時間賽跑,讓一件件稀世珍寶容光煥發、起死回生。他們的專注更令人感佩———於俗世喧囂中獨擇一事、終其一生。這一系列紀錄片掀開的,畢竟只是文物修復師行當隱秘的一角。前不久於中國美術學院舉辦的“古書畫鑒藏與修復國際研討會”,則讓人們了解到宮牆內外、世界各地博物館古書畫修復師們背后更多的故事。比如,這一行當沒有生搬硬套的所謂標准化流程,單單調制漿糊即可成為一門大學問,不同的紙張、不同的破損程度,甚至不同的天氣,需要的漿糊各不相同,如何把握全憑目測、手感等經年累月的實踐經驗。又如,修復觀念越是更新,面臨的尷尬可能越多:要賞心悅目,還是歷史真實? 高明的接筆的確可能替代作者補全有所缺失的畫面,而臨摹高手再怎麼高明都不是作者本人。
有的疑慮因修復而消,有的茫然因修復而起。歷經一次次的修復,中國古代書畫才是人們今天所見的模樣。
中國古代書畫歷經數百乃至上千年流傳至今,沒有多少是未經修復的。在一些作品身上,甚至輕易就能找到補綴的痕跡。
比如元朝衛九鼎的 《洛神圖》,畫面下半部分,是遼闊江面上冉冉升起的洛神,上半部分卻隻見淡淡的遠山佔去最頂端的三分之一,四行題字偏安右隅,其余部分均為空白。這樣的布局並不完美。這其實是一塊方形的全補。對此,最合理的推測是,這裡原本是一段題字,題字的人或許因筆誤,或許因位置不夠滿意,於是請人將這部分挖掉。又如在宋畫 《宋高宗坐像軸》 中,人物部分非常精彩,背景卻總讓人感覺沒涂勻,這是因為背景部分完全是后人補上去的。元人 《梅花侍女圖》 的補綴痕跡很難發現,其實原畫隻剩下人物部分,后面的梅花樹、水仙完全是另外一個人畫的,很可能是修復者順著人物邊緣把它非常完整地切割下來,再請專家參考原本的樣子來做補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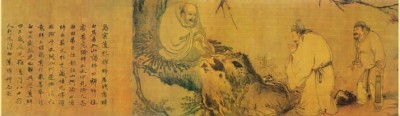
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的南宋梁楷 《八高僧圖卷》(局部)
既往的修復痕跡對於書畫的鑒定可以發揮重要的輔助作用。現藏於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南唐董源 《溪岸圖》軸究竟是不是真跡,就曾引發過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起初,這幅畫是抗戰時期徐悲鴻在桂林發現並收藏的。張大千聽說,借去一觀,十分喜歡,遂以金農《風雨歸舟圖》 軸作為交換將 《溪岸圖》軸收入囊中。誰料,上世紀50年代,這幅畫被張大千賣給美籍華人收藏家王季遷,並於1997年為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買下。對於如今人們在大都會博物館看到的 《溪岸圖》 軸,學界存在這樣的質疑:這很可能是一幅20世紀的仿作,出自張大千的精心策劃———張大千模仿的功力極深,幾可亂真,他幾乎把美術史上的名家名作挨個臨摹,堪稱天下第一“造假”高手。事實真是這樣的嗎?《溪岸圖》 軸鬧了烏龍? 今天,借助軟?光片技術,這幅畫所呈現的裝裱結構透露出了重要的線索。《溪岸圖》 軸有層層破損並修補的痕跡,先后被裝裱過3次,破損的痕跡各不相同———這說明這幅畫有著悠久的歷史,絕不可能是現代的。在軟?光片的拍攝下,董源的題款“北元副史董元畫”也歷歷可見,董源的“源”在元代一直是用作“元”的。
南宋梁楷 《八高僧圖卷》 上世紀60年代進入上海博物館時,畫面灰暗,浮灰很多。正是經過裝裱,“梁楷”的款字才浮出水面,此前人們隻把款字當成石頭或者桌子的襯點。佐証作品身份,這個關鍵的款字功不可沒。
反之,不知所以然的修復,帶來的是一連串的鑒賞問題。現藏於美國納爾遜藝術博物館的一幅傳為五代畫家荊浩的 《雪山行旅》 就曾因修復惹上爭議。這幅畫1930年出土於山西南部的一個墓志室,狀況不堪,濕氣很重,被送至北京重裱,修復師卻不僅將其重裱,還自作主張添了幾筆。關於這次裝裱,當時沒有留下任何記錄,人們僅能從這幅畫的現狀來了解。如今呈現在人們眼前的這幅畫,按照該博物館副研究員陸聆恩的描述,“空間的處理有點曖昧,沒有宋畫的利落,山水皴法很簡單”,在她看來,畫面顯出的這些尷尬或許可以解釋為宋代山水畫發展成熟之前的風格,然而,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一些很粗略的手法有點像工匠做法。
有著大面積全補的一幅傳為南宋李唐的 《文姬歸漢圖》,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也被認為畫面有諸多蹊蹺之處。有專家推測其修補時間應該發生在明朝,明代畫家的筆觸與宋代畫家的筆觸風格截然不同,不自覺地會流露出屬於自己時代的風格。一些不合理的細節也出現在畫面中,比如其中第四幅,描繪文姬被俘虜到北方后,有一天走到戶外緬懷家鄉,隻見她與身旁的仕女爬上了很陡的坡,而那位仕女手裡拿了一把看上去較重的琴。兩位弱女子出門,不是應該站在平坦一些的位置嗎? 專家猜測,很可能是補筆的人沒有對原畫做過仔細的觀察,如果修復不當,很可能會模糊了原來繪畫的面目。
中國古代書畫的修復非得用中國的方法。就連調制漿糊都是學問,不同的紙張、破損程度,甚至天氣,需要的漿糊各不相同。
與西方繪畫材質的截然不同,決定了修復中國古代書畫非得用中國的方法。中國書畫的材質通常不是紙就是絹,質地比較纖薄嬌嫩。一方面,這使得中國古代書畫的流傳保存相當不易,多有殘損,受到氣候、環境、保管等因素的影響,容易造成各種不同程度的損傷,尤其是畫心產生折斷、裂痕﹔另一方面,這也為中國書畫的修復增添了難度———西方繪畫因畫面可被拆分成光油層、顏色層、底層、補面層、支撐架等很多層面,所有在畫上的修復都可以被復原,而中國畫所用的紙本或絹本一筆下去就是裡裡外外融合在一起的綜合體,深入肌理,不可以被復原。

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的隋朝展子虔《游春圖》
今天人們在博物館裡看到的古書畫,總是神採奕奕,人們不知道的卻是,為它們“提神”的修復工作耗費了修復師們多少時間與心力。
中國書畫修復之步驟從洗畫、揭命紙、小托、上板、全色到裝裱等,工序眾多而煩瑣。並且,沒有生搬硬套的所謂標准化流程,每一幅書畫作品的修復方案都是獨一無二的,憑借的就是修復師們經年累月的實踐經驗。
單單調制漿糊即可成為一門大學問。修復的每一道工序都需要用到漿糊,它關系著書畫卷軸的平整問題。上海博物館文物修復研究室副研究員諸品芳坦言,這些漿糊都是修復師們手工調制出來的。他們往往憑借目測、手感來配兌漿糊的適度。“面粉和澱粉都可以成為漿糊制作的原料,面粉裡面因為含有面筋,搗起來比較省力,澱粉的密度比面粉略低,漿頭不能太稀,沖的時候要格外用勁,不過用澱粉打出來的漿來裱畫會更平整﹔同類的紙張在雨天和在晴天,需要的漿糊各不相同,雨天水分蒸發得慢,漿糊需要略稠一點,而晴天水分容易蒸發,尤其是夏日晴天,漿水需要薄一些﹔調整漿水的厚薄、稠稀也要根據紙張的質地,漿水太薄了沒有黏力,太厚了又偏硬﹔新搗好的漿糊先別急著用,漿糊有一定的脹性,沒有完全脹開時性能不穩定,用來裱畫容易出現不平,需要冷卻之后等到脹性穩定……”
為大英博物館修復中國古書畫近30年的修復師邱錦仙透露的一些關於修復的小秘密,更是令人大開眼界。幾年前在修復清代畫家禹之鼎的書畫時,普通的豆漿水竟然變成“秘密武器”,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修復過程中,我們需要觀察紙本畫本身的質地,找到與畫心同樣粗細紋理、質感的紙,但今天的宣紙往往與老紙有著不同的光澤度。用豆漿主要是做出一種老紙的光澤。大英博物館要求不能使用化學藥品,而全色紙一定要有一點熟才能全得上,於是我們往往用豆漿來代替化學的膠礬水把補洞打熟。豆漿本身是白色的,因而不能很厚,上得厚的話以后染色也染不上,我們通常用一杯生豆漿兌三杯的水,淡淡的。先用生豆漿水把紙染一下,染好等它干了以后再上顏色,根據畫心的本色,比它染得淡一點作為托紙。”
無論採取了什麼樣的修復方法,重要的是讓后來的人們知道這些古書畫經歷了什麼。有專家指出,在美國藝術修復協會,有這樣一條規定,關於修復的任何操作都需要照片和文字記錄。即便從前的修復沒有記錄,也可以在如今的修復過程中開始記錄。這些記錄就好像為古書畫建立起一張病歷卡,清楚地告訴后來的人們對於這幅書畫的保存曾經採取過什麼樣的措施,結果又是什麼。
修復包含著非常主觀也非常微妙的判斷揣摩。修復到什麼程度最是理想,這常常是一道兩難的選擇題。要賞心悅目,還是歷史真實?高明的接筆的確可能替代作者補全有所缺失的畫面,而臨摹高手再怎麼高明都不是作者本人。
什麼樣的古書畫應該採取什麼樣的修復方式? 很多時候,這個問題是沒有標准答案的。你以為古書畫修復是一門科學? 其實它摻雜了太多非常主觀也非常微妙的判斷揣摩。
對於現藏於大英博物館的顧愷之《女史箴圖》 唐摹本曾經採用的修復方法,很長一段時間,爭議聲始終存在。《女史箴圖》 原本以手卷的形式存在,1914年到1918年,大英博物館修畫師斯坦利·李特約翰參考日式折屏的形式,將這幅作品分割成兩長段和一小段,展平於鑲板之上,置於鏡框之下。有人指出,畫面的分割、圖像與款識的分離,都已造成不可逆轉的遺憾。有人為手卷形式的不復存在而惋惜,認為卷軸是一個生命體,生命可以隨時成長和傳遞。然而,很多人也意識到,來回折疊的手卷形式並不利於作品的保存,將其裝裱在鑲板上不去觸碰,避免了皺痕和斷裂,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幫助它們保持著最佳狀態。
但凡文物修復,“修舊如舊”似乎是一道金科玉律。在中國美術館保存修復中心副研究館員鄧峰看來,具體該如何理解“修舊如舊”,又產生了新的問題。后一個“舊”,究竟是文物創作初始的狀態,還是文物當下的狀態。目前的實際操作其實出現了三種方式,修舊如初、修就如現和隨舊做舊。“修舊是復原性修復,具體復原到哪裡,每一件作品情況都有所不同。比如清洗,到底清洗到什麼色度,是整體清洗,還是局部清洗,比如染色,是染到明代書畫的色度,還是宋代書畫的色度。”
明知一幅古書畫部分畫面有所缺失,該不該全色和接筆,尤其成為全球各大博物館的修復師們面臨的兩難選擇題。
所謂全色,指的是在畫心有破損的補紙或者補絹上使用顏料填入與畫心基本底色的色調。接筆又稱之為補筆,指的是更進一步將缺損的地方依照畫意來添加線條跟顏色。不加全色和接筆,很明顯的缺點就是對人們欣賞畫面造成了很大的干擾。加以全色和接筆,則多少掩蓋了真實性和歷史性。
西方修復中同樣存在類似的困擾。在西方,20世紀之前繪畫通常由有技巧的畫家來修復,這些畫家把修復當成副業甚至全職,會對畫作進行一些改變來取悅現存的收藏者,或者根據宗教的限制來進行修改,這種對藝術目的的漠視其實也引發了人們的探討,那就是怎樣來道德地應對視覺藝術的補綴。
在很多專家看來,任何修復均要以尊重原始的材料、真實的歷史為基礎。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首席管理員帕·努塔斯指出,補綴有前提,若有具體的文件能夠展示藏品在損失之前是什麼樣子的,補綴才能進行,否則,在道德倫理上站不住腳。他坦言最擔心的就是補綴時有過度的個人化解讀,以至於修復后的畫面可能與原來的畫面格格不入。“通常我們在使用補色的時候,一定要保証它能夠很好地粘附在紙張或者絹面的表面,而且不能夠有任何色彩上的色差或者勻染,同時不能喧賓奪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用過調色來進行補色的效果。”古物維護專家林春美甚至提出,為古書畫做替補,不僅需要與整體和諧,甚至需要與原件有所區別,這是為了避免因修復而篡改藝術性或歷史性的証據。
書畫修復師蕭依霞舉例她所在的博物館藏有一件宋代馬遠的冊頁 《鬆溪觀鹿圖》。這幅畫畫心多處破損,而且有很多前人的不當補全,與原畫相差很大,嚴重地影響到觀者觀畫的完整性。但即便面對這樣傷痕累累的古書畫,博物館也僅僅接受全色,而不接受補筆,“因為再怎麼樣的臨摹高手都不是馬遠本身,我們不能代表馬遠來添加畫意,隻能夠在這幅畫僅存的畫意上做保存,做一個折中的方法,做到不干擾觀者看畫的程度。”她認為在想不到更好的辦法之前,最好的辦法就是維持現狀,等到有更好的手段再去修復。貿然補筆,你不知道這一筆下去補的到底是不是畫家要的,不然就是你自己的臆測。
“中國的古書畫幾千年流傳下來都是我們的國寶。我們需要比醫生還要高明一點,隻能成功,不能失敗,因為一旦失敗就難以補救了。”諸品芳感嘆。在她看來,全色和補筆一定要達到高的級別才能完美。要全色,就得要全得跟整個意境的顏色一樣,看上去沒有破洞。要接筆,就得接得有一定水平,繪畫的技術很扎實。有時候,修復不妨保守一點,“如果這幅畫僅僅是有些毛病,但暫時不會危及生命,我們就不妨先給它開一點藥,如果這幅畫已經病入膏肓了,才需要立刻對它進行搶救。”
不過,在上海博物館副研究館員沈驊看來,接筆這門技術不能輕易放棄。他曾有一次修復明代的一幅花鳥圖,這幅畫中有一隻鳥頭缺了半個,但參考這位畫者的其它作品以及畫中的另外半隻頭,能夠按照已有的筆意將缺失的部分接出來。沈驊贊成的接筆也並非一概而論。他所提出的標准是“選擇性接筆”———有一些缺失是筆意的斷開,可以用接筆將其連出來﹔而對另一些較為嚴重的缺失,不如不動,因為一動便是臆造。
今天人們在博物館裡看到的古書畫,總是神採奕奕,人們不知道的卻是,為它們“提神”的修復工作耗費了修復師們多少時間與心力。歷經一次次的修復,這些古書畫才是人們今天所見的模樣。圖①②③分別為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的明代邊景昭 《竹鶴圖軸》,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的南宋梁楷 《八高僧圖卷》(局部),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的隋朝展子虔《游春圖》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