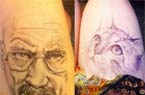也曾學先生在課桌上刻“早”字
◎魏小軍
我自小在西北農村長大,童年是在黃土高原下的一個小村庄度過的。帶著比我小兩歲的弟弟一起成長,我們有上樹掏鳥窩得手后的欣喜若狂,有追趕野兔踩空崴腳后的疼痛難忍,有到鄰村西瓜地裡偷瓜不成后的遺憾懊惱,也有初進校門強烈感受到讀書的枯燥與乏味……
然而,當我第一次在語文課本裡讀到《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時,魯迅先生寥寥數筆所勾勒出如詩如夢般的景致,頃刻間立體式呈現在我眼前,對先生筆下的百草園、三味書屋產生了無限遐想。正因為如此,我在課堂上勇敢地舉手詢問老師,百草園、三味書屋在哪裡?老師告訴我,在先生的故鄉、遙遠的江南。
從那時起,我就十分羨慕江南的石井欄、皂莢樹、桑樹,以及青山綠水,夢想有一天能親眼看看江南的樣子。這對當年身處關中腹地的一個孩童所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以至於若干年后,我毅然背起了行囊,隻身來到了魂牽夢繞的浙江紹興,走進三味書屋,一解自己的魯迅情結,終於圓了童年的那個夢。
“我家的后面有一個很大的園,相傳叫作百草園……不必說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葚……也不必說鳴蟬在樹葉裡長吟,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單是周圍短短的泥牆根一帶,就有無限趣味……”帶著書本裡的記憶,我虔誠地尋覓著魯迅先生曾經散落在家鄉的影子。置身先生故居,我似乎看到了先生早年生活起居的瑣碎場景,老屋依舊,睡床依舊,一桌一椅歷經歲月的洗禮,一磚一瓦承載時代的變遷,正散發出古色古香的無限韻味來。睹物思人,我的腦海裡驀地浮現出先生年輕時青燈相伴、苦讀到雞鳴的情景來,也時時回想起自己在先生文章的影響和激勵下,幼小立志、發奮學習的童年諧事。
我甚至認為,欲像魯迅先生一樣勤奮讀書,首先必須要有一個鮮明的態度,所以便自作主張在課桌上刻了一個“早”字。結果可想而知,除被班主任狠狠地教訓了一頓外,還罰站了一上午。心裡一直在嘀咕:為什麼魯迅能刻“早”字,我就不能?但先生“時間就像海綿裡的水,隻要願擠,總是會有的”的名言,從此深扎在我的內心,成了我的座右銘。
上世紀70年代的西北農村十分貧瘠,我們學校的教室窗戶沒有一塊玻璃,冬天都是用塑料紙蒙著。到了隆冬,這些薄薄的塑料紙真的像紙片,一吹就碎,老師剛指揮大家換上新的塑料紙,呼嘯的寒風猶如刀割一般,瞬間就破,到了最后也就懶得再折騰,所以冬天我們的教室內外溫度基本上一致。
在那個年代,我和我周圍的同學沒一個叫苦抱怨,按當下的話講,反倒幸福指數極高。這也許是因為當時的大環境所致,反正大家的心態極其快樂。不管是在泥濘的土路上,還是在刺骨的寒風裡﹔不管是在昏暗的油燈下,還是在自家的庄稼地裡,我們都會開心地背誦著魯迅先生的文章,“油蛉在這裡低唱,蟋蟀們在這裡彈琴。翻開斷磚來,有時會遇見蜈蚣﹔還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會啪的一聲,從后竅噴出一陣煙霧……”(作者生於上世紀70年代)
 |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