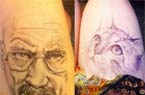“真”朋友魯迅
◎學通社東城分社、北師大二附中高二(10)班 曹雨芊
早在初中時就聽說過一個學生中廣為流傳的順口溜:中學學語文,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當時自詡語文成績出類拔萃的我,對於第三“怕”沒什麼感覺,他只是在教材裡出現得次數多了一些的作者嘛。
可以說,在高中之前,我對魯迅先生的認知僅僅是和“批判”、“戰士”這些標簽綁定在一起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以及那一張表情肅穆、凝望著中國未來的臉。
真正開始走近魯迅先生是在高一。新學期的第三個月,班裡進行了將近兩個月的魯迅專題研究。翻開課本專題導言,署名是錢理群——后來才知道這是北大教授,中國研究魯迅的大家。導言的第一句話就扑面而來一股親切感:“魯迅永遠是青年的朋友,原因就在於他是一個真的人:一方面,他敢於公開說出別人不敢說、不願說、不能說的一切真實﹔另一方面,他從不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更拒絕充當導師,他將真實的自我真誠地袒露在年輕人面前,和他們一起探討和尋路,青年可以向他傾訴一切,討論、爭論一切,也可以毫不顧忌地批評他,甚至拒絕他。”
兩個月的學習之后,我想我才真正理解這個長句。
學習魯迅先生的教材是語文組老師自己編選的。這個單元是魯迅先生的散文和雜文,選了《范愛農》、《憶韋素園君》、《記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紀念》,四篇都在講述魯迅和中國青年的故事。專題學習開始之前,平時愛以“閑扯”方式上課的老師居然特意花了整整一節課,認認真真地講解專題研究要分哪幾個部分,什麼時候要交哪些文章作業,要補充閱讀哪些書等等,還把自己列的學習任務計劃表發給我們每人一份。他說,平時講史鐵生、汪曾祺、郭沫若等扯一點沒關系,講魯迅不行,總是感覺頭頂有他老人家的靈魂。我驚訝於他說話時收起嬉笑怒罵后的一臉庄重。大概是這庄重也莫名感染了我,於是在讀魯迅每一篇文章的時候,我都要求自己視其為文學中的珍饈,就差讀書前先把雙手洗淨了。
在認真聽過幾節課之后,我開始感受到魯迅先生的人格魅力並為之深深吸引。他不只是那個以筆為槍永遠吶喊奮進的戰士,也不只是左翼文聯的領袖。在這些架子裡面填充的,是豐滿的血肉和豐盈的靈魂。在紀念他的青年朋友時,我看到他真摯而強烈的情感:欽佩、喜愛、嘆惋、悲哀。“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說的是韋素園﹔“始終微笑著的和藹的”卻在執政府門前殞身不恤的是劉和珍﹔迂得可愛的是柔石﹔“直立著”死去的是范愛農……魯迅對於這些犧牲掉的好青年的情感是復雜而深刻的,原因就在於他和他們當時處在“黑雲壓城城欲摧”的社會環境中。書上選的四篇課文裡,有許多極好的句子正是基於他這樣的情感。也正是第一次,我開始極認真地背誦魯迅先生的文字:“真正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這是我最愛反復背誦的一段。我驚嘆於先生敏銳的洞悉力和精確的文字表達功底,當然,最最重要的,是他傳遞出的感情。在最后的3000字研究論文中,我試著分析和描述他對社會、對中國的這種感情。“冷峻的熱烈”,這是我的概括。他炙熱的感情不顯膚淺和熱血,是因為他始終冷靜地凝視、思考。批判的時候有的放矢,沉郁而悲憤﹔喜愛的時候目光灼灼,溫暖而真摯。他的許多種情感交織、重疊,像一點點織成的一張大網,先生的形象也愈發立體,最終從書本上走下來,走到我身邊。
其實魯迅絕不是一個聖人般的存在,庄重之外的他,喜歡看電影、喝咖啡、和朋友聊天。讀他和許廣平的《兩地書》,你會偷偷笑他和天下男人一般模樣,在追心儀女人用些伎倆贏得好感,不過是說得冠冕堂皇罷了﹔讀他和同時代文人打筆仗,用不帶臟字的句子罵人,你甚至能看到他頗有幾分洋洋自得的神情﹔他冷峻的面孔后面,是天才的幽默細胞,隻不過那些高端冷艷的幽默都藏在看似一本正經的句子中……
魯迅先生太難用幾個詞來形容。如果一定要說,想來想去,我覺得也隻有“真”這個字還算可以概括他的情感和為人了吧。語文老師把《魯迅全集》讀過好幾遍,這是他最喜歡做的事情之一。他對我們說,青年的時候,一定要讓一位偉大的導師住進你心裡。我想,我能夠在這樣的年紀裡結識魯迅先生這樣一位“真”的朋友,實在是莫大的幸事。(作者生於上世紀90年代)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