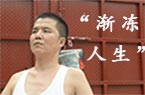廣園中路農貿市場內的記功亭,已經修葺完畢。

殘存的墓門牌坊上隱約可見墓碑。
廣州遠征軍老兵梁振奮祭戰友 願有生之年看到新一軍公墓重建
今年9月3日,是第一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再過25天,中國人也將迎來首個烈士紀念日。
5日前,國務院發出通知,公布了第一批80處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其中,山東台兒庄大戰紀念館等一批國民黨軍隊抗日遺址赫然入列。同日,民政部公布的300名抗戰英烈名錄中,國民黨軍人佔了近三分之一。
在廣州, 90歲的梁振奮是羊城唯一健在的中國遠征軍老兵。他說,除了被公布的國家級抗日遺址: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陵園,廣州還有一個不應被忘記的抗戰遺址:新一軍公墓。 他有一個心願:有生之年,看見新一軍公墓重建。
今年9月3日,生於1924年的抗戰老兵梁振奮在佛山南海舉行的一個老兵雕塑揭幕活動上,為年輕人口述那段悲壯歷史。去年的這一天,89歲的他跑到雲南鬆山,祭拜那些曾和他一同浴血奮戰並長眠那裡的中國遠征軍戰友。
一寸山河一寸血
緬北戰場痛擊日軍
更多年前的9月3日,他到過騰沖國殤烈士陵園獻花,去過雲南瑞麗河畔,靜靜地凝視河對面的緬甸山丘。
作為歷史長河的一粒細沙,在中緬印戰役后的70年,梁振奮再沒回到緬甸。但他不願悠閑待在廣州登峰街清水塘的家裡,他希望與人分享自己19歲到21歲的血色青春,一個在戰火中的廣州學生、一個中國遠征軍軍人的抗戰記憶。
時光回到1942年,高大威猛的廣州靚仔梁振奮剛好18歲。1938年日軍侵佔廣州,14歲的他就隨親戚一路逃到西南。白天梁振奮在店裡做雜工,夜晚則到基督教青年會學習。
烽火年代,逃亡路上,勤奮好學,梁振奮至今依然寫得一手好字。而強健體魄、不凡談吐,也讓梁振奮成為當時少有的文藝青年。當年9月,愛國的他最終投筆從戎,參加了新一軍38師學生隊,經考試及格后成為38師諜報隊的學生兵。
梁振奮的兵種叫“斥候”,相當於現在的偵察兵,直屬於38師師部參謀處。當時的38師師長為國民黨著名將領孫立人,后成為新一軍軍長。
1943年1月,19歲的梁振奮搭乘美軍運輸機飛越駝峰到達印度汀江,后到新一軍在印度駐地蘭姆伽接受訓練。同年11月,當時番號為中國駐印軍新一軍38師開始向緬北反攻,第2次緬甸戰役開始。
在胡康河谷。3月9日,孫立人率領的38師113團與美軍突擊隊聯手攻佔瓦魯班。號稱“叢林作戰之王”的日軍第18師團死傷過半,狼狽逃出胡康河谷。
據日軍戰史記載:“胡康河谷的中國軍隊,無論是編制、裝備,還是戰術、技術都完全改變了面貌,使我軍損失慘重,全軍不禁為之愕然。”
作為新一軍38師諜報隊隊員、少尉組長,梁振奮曾在於邦戰役前,在胡康河谷火線見過身穿普通偵察兵服裝的孫立人與美國將軍史迪威。當時,周圍隨時有敵人包圍的危險,而史迪威隻有一個黑人警衛拿著卡賓槍,孫立人周圍也隻有三四個警衛。
“在我當時看來,史迪威將軍背著卡賓槍,戴著軟邊帽,一點也不像一個高級將領,活脫脫是一個瘦削的小老頭兒。而站在他旁邊的孫立人將軍,則顯得身材高大,英氣逼人。”至今,梁振奮依然記得兩名抗戰名將的淡定從容。
為了獲得敵人信息,梁振奮曾在印緬邊境叢林裡多次單兵作戰,與日軍遭遇,幾乎是與死神擦肩。他說,回想起來,那種不為險境而恐懼退縮的精神,與新一軍將領平日的潛移默化有關。
熱血男兒返家鄉
一眼認出愛群大廈
1945年5月,中緬印戰役結束。當年夏天,21歲的少尉梁振奮隨新一軍空運回國,從雲南回到廣西南寧駐扎。
7月,新一軍收到命令:向粵西進發,反攻日軍佔領的廣州灣。廣州灣就是現在的湛江。
然而,當年8月15日晚上,梁振奮被告知剛從無線電裡聽到:日本投降了!
那一晚,梁振奮激動得睡不著覺,在通訊營給其他連隊的朋友打電話,報喜訊。而在廣州,不少市民奔走相告,“人潮浪涌,躍呼狂熱”。
隨后,新38師接到命令:派出先遣隊,代表新一軍去接收廣州。作為土生土長的廣州人,梁振奮成為先遣隊的不二人選。
1945年9月2日下午3時左右, 從14歲后就離開廣州的梁振奮終於看到了闊別多年的故鄉——在行進的軍船上,珠江口岸出現了一個地標建筑,“我一眼就認出那是愛群大廈”。
對於抗戰勝利的場景,90歲的他依然記得——在愛群大廈附近的碼頭上,老百姓和等候多時的記者把道路圍得嚴嚴實實。圍觀群眾自發鼓掌,記者忙著照相採訪。
“此情此景,讓先遣隊非常自豪,我心尤甚。我可能是光復后第一位回到家鄉的廣州籍戰士啊”。梁振奮日后自述。
八年抗戰終大捷
沙面勝利賓館由此得名
1945年9月7日,新一軍孫立人的部隊進入廣州。至今,不少廣州人都愛去沙面的勝利賓館飲茶吃飯,但很少人知道,勝利賓館得名正是八年抗爭勝利而來。在經歷了英國人起的“維多利亞大酒店”、日本人起的“東天紅飯店”后,作為新一軍軍部所在地的勝利賓館,名字延續至今69年。
進入廣州后,梁振奮回歸部隊,他隨隊先后駐扎沙面、維新路、沙河等地。他們的任務主要是觀察和監督,防止意外發生。在梁振奮印象中,接收廣州過程十分順利。包括收繳武器、集中俘虜、受降儀式等方面,都沒有出現過反抗、動亂和波折。
沙面是新一軍在廣州的駐地之一,勝利賓館則是孫立人的軍部所在地。1945年9月16日,日軍在廣州的投降儀式結束后,梁振奮接到部隊消息,開始為戰死在印緬戰場的新一軍戰士修建公墓。
據不完全統計,新一軍奉命出國參加遠征軍,抗擊日寇,至少有27000多名將士為國捐軀。
九旬老兵每年拜祭戰友
從2006年開始,每一年,梁振奮都要到紀念塔、記功亭和牌樓前祭掃、行禮,獻花。
9月初,本報記者陪同梁振奮開始了他九旬人生中的再次“會戰友”。從登峰街梁振奮的家到濂泉路,開車用不上5分鐘。90歲的梁振奮為了准備這次會面,卻用了多半個小時准備。
與水蔭路的19路軍陵園寧靜相比,經過69年的城市發展,高架橋、濂泉路、批發市場的喧鬧,已讓新一軍公墓找不回半點當年的悲壯肅穆。新一軍公墓變成了零散的三部分。
東記功亭位於菜市場內
在濂泉路28號大院門口,殘存的墓門牌坊上,蔣介石手書的“第一軍印緬陣亡將士公墓”的字跡勉強可辨。
秋日驕陽下,穿過布料市場如鯽魚的人群,梁振奮邊擦汗邊踱步到500米外的廣園中路農貿市場。在一個燒臘檔口前,他看到了記功亭。記功亭原位於墓道兩旁,有蔣介石所提的“勛留炎徼”四個大字。而目前在菜市場的為僅存的東記功亭,西記功亭已於“文革”期間被毀,題字已不存在。
看到老梁來獻花,菜檔檔主第一時間把放在記功亭門口的自行車搬走了。菜市場的保安說,每年清明和9月,總是有一些老兵來這裡祭拜。不過相比往年,讓老梁欣慰的是,從今年4月開始,天河區文廣新局已對東記功亭進行了修葺。到祭拜時,記功亭已經煥然一新。
老兵有生之年的心願
而在新一軍公墓現存最宏大的遺跡紀念塔前,梁振奮還是有些激動的哭了。
他把鮮花獻到紀念碑前,行了幾個標准的軍禮。和69年前相比,紀念塔上的銅鷹與戰士雕像早已不見蹤影。
墓碑隻剩上半部分,2001年重修前已斷成兩塊,重修后,將它安放在原處。只是原本“前帶沙河,后依雲山”的朝向,變成了背對連廣園中路高架橋,面朝部隊宿舍。
每一次來獻花,梁振奮就會想念印緬戰場的戰友,也為新一軍公墓的現狀心酸難過。
“有生之年,我隻希望能看見新一軍公墓重建。”人到暮年的他說。
當年軍官出錢修公墓
根據當年參與修墓的老兵回憶,當時孫立人乘坐軍用飛機,用印緬戰場上高空偵察的方法,三次在廣州上空盤旋為公墓選址。最后選擇了白雲山麓馬頭崗這塊風水寶地,即今天的濂泉路、廣園西路一帶。而選址原因則為“前帶沙河,后依雲山,東北為第一師陣亡將士墓園,十九路軍滬戰殉國官兵公墓在其南,其西則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及朱執信廖仲愷諸先生之兆在焉。”
1947年9月,經過日軍戰俘和建筑工人的兩年趕工,佔地8萬平方米、雄偉壯闊、全稱為“陸軍新編第一軍印緬陣亡將士公墓”的國民黨新一軍公墓落成。孫立人曾在墓園牌樓手書“頂天立地 英魂長存”。
而梁振奮記得,身為少尉的他被扣了幾個月薪水。“公墓是全軍集資修建,沒有其他的錢,當時規定士兵不用出錢,由軍官出錢,逐月扣薪水。”甚至公墓建成后,他的女友還曾帶著他的弟弟去現場,專門寫信告訴他詳情。
然而,世事滄桑。1964年,當梁振奮以紡織工人身份重新回到故鄉,曾經恢弘一時的新一軍公墓僅剩下三處遺跡:紀念塔、記功亭和墓門牌坊。 記者 王丹陽 圖/特約攝影 杜江
(來源:廣州日報)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